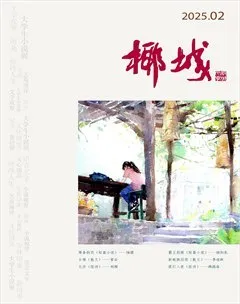旗袍招展(短篇小說)

作者簡介:余顯斌,中國作協會員,教師,《讀者》《意林》《格言》等簽約作家。寫作至今,出版文集23本,發表文章3000余篇,其中《知音》《杜牧的江南》《一輪中國月》等160多篇文章被各種考試選為考題。
不知是哪一天,穿旗袍的少婦搬到了我們院子里。那是在一個早晨,朝霞洇出一汪一汪的紅暈來,水漉漉的,如一張清嫩的臉兒。當時,我正下樓去,將摩托車從樓道里推出來,準備去學校,就在這一剎那間,我看見了她。
少婦腿長腰細,身形如鶴,穿一襲旗袍,素色的,在晨風中招展著,招展出無限的韻律和嬌媚。豐腴的腿在晨光中瓷光閃閃,耀人眼目。
當時,不知是我閃了一下眼,還是該死的摩托車油門不足。總之,我沒扶穩車子,車子倒下了。我感覺十分狼狽,很沒面子,尤其是在美女面前。于是我使勁地想扶起車子,可是越想扶越扶不起來,鬧得我更是滿臉通紅,甚至都出了汗。少婦見了,鞋聲叮叮地走過來,放下手里的小皮包,蹲下幫我。
車扶起來了,她對我一笑,露出圓圓的酒渦,說:“騎車可要小心,那可是馬虎不得的,一不小心會出事的哦。”少婦說的是普通話,不同于小鎮方言,很純真,很明亮。尤其那個“哦”字,一波三折,波光閃閃,聽在人耳里,有一種清心明目的感覺。我忙紅著臉點點頭,騎上摩托,做賊一般飛快地跑了。
上午放學回家,我就把這事對妻子說了,問以前咋就沒見過這女人,她是干什么的,從哪兒來的。妻子白了我一眼,說:“怎么?盤查戶口還是有其他的想法,別是吃著碗里的,望著鍋里的吧?”妻子什么都好,就是小心眼,說話也較為尖刻。
我笑笑,不再說話。對妻子這人,只有這種辦法。在妻子的嘴里,我才知道,少婦是最近才搬來的,就住在我們樓的對面,可能是哪個老板的妻子吧。
其時,高速公路剛修到小鎮。小鎮正處于兩省的交界點上,頓時熱鬧起來:工人、司機、包工程的老板,一群一群來到小鎮,大車小車,日夜不停。小鎮人口一時暴增,房租也隨之大漲。像少婦那樣旗袍招展、高跟鞋叮叮的,租住著一套單元房,一定是個有錢人。說實話,那種裝扮,在小鎮人眼中看來,也實在是不俗的。
妻子說,那女人還是一個蠻善良的人呢。
原來,一天早晨妻子去上班,路過街上時,看到一個民工被汽車撞了,血流一地,倒在地上呻吟著,看樣子傷勢很重。肇事車輛早已逃逸了。街道上人來人往,沒有一個人理睬。就在這時,一輛面的停下,潔白如鶴的少婦從車中走下來,來到那個工人身邊,細細地察看工人的傷勢,想把他扶起來。可她那么纖弱的身子,又怎么扶得起一個壯漢呢?無法,她只好請旁邊看熱鬧的人幫忙。可看到那人滿身是血的樣子,周圍沒有一個人愿意搭手。
妻子恰好就在旁邊,看不過去,出于好心勸她:“別人躲都躲不過來,你怎么還往身上招啊?”
少婦鼻尖上微微地沁著汗,臉色紅暈,很焦急地說:“總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一條人命在眼前消失吧?大姐,來幫個忙吧。”最終,還是妻子和她一塊兒把受傷的人抬上了車。然后,少婦掏出一沓錢,遞給司機,說:“你把病人趕快送醫院,我還有事,過一會兒就來。”
路上,妻子大為不解,問那傷員是不是她的熟人,她搖頭;又問是不是她的親戚,她也說不是。
“那她怎么說?”我問。
妻子對我說:“你猜她怎么說?說是同情,嘖嘖,同情!無親無故啊。”妻子說著,既佩服,又有些不相信的樣子。
但幾天后發生的另一件事,徹底改變了妻子的看法。那天,妻子抱著小貓一邊親著,一邊走出院子門,那少婦恰好從外面回來,懷里抱著一個臟兮兮的孩子。孩子哭得鼻涕眼淚直流,糊了少婦一身。少婦一邊哄著,一邊掏出手紙給她擦鼻涕,并拿出糖果,往孩子嘴里塞。
妻子見了,很高興,問:“大妹子,到底把孩子帶來了。”
少婦氣喘吁吁地說:“哪里,剛經過街道,遇見個孩子,找不見媽媽了,在那兒哭。我想,要是被哪個人販子遇上了,怎么得了?所以就帶著她到處找她的媽媽,可沒想到就是找不著。這不,我只好把她帶回來了。”
妻子不信,可看她一臉正經的樣子,就半信半疑地把小貓放下,伸手接過孩子,幫她抱回了家。
少婦一進家門,就忙著給當地派出所打電話,請人幫忙調查,看是哪一家的孩子走失了。之后,她又打來一盆熱水,用手試了試,開始給孩子洗澡。洗完澡,她又帶著孩子到商場去買了一套衣服。再抱回來時,一個灰灰土土的孩子,竟變成了一朵鮮艷的花骨朵。滿院子的人都像妻子一樣,認為那是她的孩子。她再怎么解釋,大家也不信,說不是自己的孩子,怎么會那么心疼。少婦只是笑,抱著孩子哄著、親著。還是妻子代為解釋,才解了圍。
第二天,派出所民警帶著一個民工的妻子進了院子,那個女孩看見自己的媽媽,一頭撲過去,大喊“媽媽”,這時大家才相信少婦的話。妻子也從半信半疑中徹底解脫出來,連連說:“真少見,真是少見。”
孩子的媽媽見了少婦,一下子跪了下來。少婦忙忙拉起她,還送了孩子一套衣服和很多食物。那位母親抱著小孩,走得很遠了,少婦還望著。一直到人影都不見了,她才回過身。
院中的女人們笑著說:“怎么,舍不得?”
少婦笑笑,說:“帶了一天一夜,突然走了,心里空落落的。”說著,她的眼圈紅了,長長的睫毛一眨一眨地,可怎么也沒夾住,幾顆眼淚落了下來,在潔白的衣服上洇出幾朵梅花。
妻子勸她,說:“如果想孩子了,就把自己的孩子帶來吧。”少婦笑笑,沒說什么,拉著妻子的手,兩個女人在一塊兒,嘰嘰喳喳地,頭對著頭談心了。也不知她們談了些什么,回來后妻子告訴我,原來少婦還沒有孩子呢。
少婦和妻子像親姐妹一樣,對院子里的其他人也從不生分,一見就熟,不停地點頭。遇見女人了,總要拉著人家的手,談談菜價,說說衣服的好壞,滿眼笑意蕩漾,讓人見了,心里軟軟的,特舒服。
有時少婦回來,看見院中的女人們玩牌,或者說閑話,就加入進去。一群女人嘰嘰喳喳地,間或一陣大笑,清亮的聲音像水一樣流淌。不久,院中的女人們竟辦了一個自樂班,吹拉彈唱,歌聲嘹亮,再也沒有了打麻將和玩牌的現象了,一個個仿佛都成了藝術家。尤其是妻子,在家里哼進哼出,仿佛又回到了初戀時的模樣。我笑著戲謔,說:“你那唱的也叫歌,純粹是破西瓜滾下了山崖。”
妻子很得意地一笑,瞥我一眼,驕傲地說:“妒嫉。連人家宛如都說我的歌唱得像王菲的一樣好聽。”說完,她哼著歌下廚房去了。砧板聲和歌聲一起飛揚,很有一種甜膩膩的味道,聽聽,還真是那么個味兒。
宛如,就是少婦的名字,至于姓什么,妻子沒說,我也沒有好意思問。自樂班是她組織起來的,妻子是其中的積極分子。
然而有一天,我回到家時,發現妻子卻坐在那兒發呆。我問她怎么了,她不說話。過了一會兒,她才側過身子,頗為神秘地告訴我:“看樣子,宛如不像是什么老板的妻子。有人問她丈夫時,她笑笑,說在家呢。你聽聽,一個女人,孤身一人來到小鎮,一身袒腿露胸的衣服,陪著一群男人進進出出、早出晚歸的,據院中一些婦女推測,一定不是干正經事的。”
我一時云里霧里,摸不著頭腦地問:“怎樣叫不干正經事啊?”
妻子說:“就是那樣不干正經事啊。”她囑咐我,以后見了宛如,打招呼時不要笑嘻嘻的,也不要望著那蛇似的身子發呆。
我說:“過分了吧,難道望一下就把我吃了?”
妻子似笑非笑、似諷非諷地說:“算了吧,你那也叫望?眼光像狗舌頭,叫舔。你要是敢不聽,到時候我也到大街上,用你那種眼光,滿大街瞅男人。”
妻子一句話把我嚇了一大跳,我登時一句話也不敢說了。妻子說完,就坐在那兒發呆,過了很久才嘆了一口氣,說:“那樣好的一個女人,怎么會是那樣一個人呢?不會是那樣一個人吧?”
從那以后,再見到那少婦,我也只是很嚴肅地點點頭,算作打招呼,再也不敢說笑話了。我知道,在我身后一定有眼睛看著,一不小心我就會落得一身泥水,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那少婦呢,卻絲毫沒有感覺出來,進了院子,依然像過去一樣和院中的女人們打招呼。可院中的女人們一個個臉上表情淡漠,或點一下頭,或應一聲。
少婦走過了,就有女人說:“呵,看那旗袍,水光閃閃的,裹著那綿軟軟的身子,撩人。”
接著,有更刻薄的人接話:“不然咋能吸住男人的眼睛,生意咋會紅火?”
話音剛落,一院子的女人都捂著嘴,吃吃地笑了。
少婦不知道這些事,仍然早出晚歸,跟過去一樣。一日,她從外面回來,吃力地搬著一盆花,細細的腰肢扭著,白白的臉上漾出粉粉的紅,鼻尖上也滲出細細的汗。有男人憐香惜玉去幫忙,沒走幾步,身后傳來咳嗽聲,知道自己的妻子在警告自己,只好匆忙放下花盆,溜了。
慢慢地,連我也有些懷疑少婦的身份了。院子里本來沒有自來水,大家合力打了一口井,共同飲用,然而人多水就顯得不足,為了水,鄰里經常吵架,甚至打得頭破血出,很傷和氣。少婦來后,經常問,怎么不拉自來水啊。大家紅著臉,不好意思回答。原來,當初自來水公司來拉水時,小院人各算各的一本賬,你也認為吃虧,我也認為吃虧,都決定不拉。到了后來,全鎮都拉了自來水后,獨留下小院人,想拉又不好意思開口,就這樣一直拖延著,拖到現在。
在小院人再一次為水爭吵后沒幾天,院里就來了一群工人,拉管道的拉管道,焊水管的焊水管。三天后,我從縣里開會回來,剛進家門,妻子就興沖沖地喊我到衛生間去。我一走進去,妻子一擰水龍頭,清亮亮的水嘩嘩地流淌著,一種清涼的氣息溢滿房間。
“知道嗎?是宛如給拉的。”妻子說,仿佛是自己做的一樣光榮。
“呵,這宛如,可真能來事。”我衷心地夸獎。妻子也喜滋滋的,說要請宛如來家里吃頓飯,她可給我們辦了大事了。
但還沒有等我們請宛如吃飯,院子里的議論就又升級了。大概的意思是,一個院子的人沒水吃,沒人管,那女人一張嘴,工人就來了,而且免費給拉水,怎么可能有那種好事呢?一定是那女人和鎮上領導有一腿,鎮領導憐香惜玉。而且更有甚者,說曾經看到少婦從鎮長的車上下來,鎮長一副笑瞇瞇的色樣。
這些流言一傳出來,我們真的徹底對少婦望而卻步了,至于請來吃頓飯,更是提也別提。我和妻子都不想讓別人在背后指指點點,那樣的滋味,就如腳板心粘了一塊濕泥巴,特別不好受。有時,出門的時候,看見少婦旗袍張揚的樣子,在街道上走著,一個小包,一雙高跟鞋,一個綿軟的身子,還有一張鳥語花香的臉兒,我就從心里感覺到遺憾,至于遺憾什么,一時連自己也說不清。
在少婦來到院子一年左右的時候,有一天,少婦被鎮政府叫走了。一院子的女人們見了,就扎成堆,嘰嘰喳喳地議論著,說一準是因為掃黃打非,這樣的女人,就應當拉去治治。
也有人狠狠地說,應當讓派出所關兩天。那咬牙切齒的模樣,好像與少婦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還有更狠的建議,說應該將少婦逐出院子,免得壞了院內的名氣,也免得院內的爺們兒個個像饞嘴貓似的。
大家都贊同這個建議,而且準備等少婦一回來,就馬上實施。妻子剛好抱著小貓出去玩,聽到這些,心里很反感,就替少婦辯解了兩句,說:“宛如到這個院子,給我們辦了那么多的好事,又是那么善良的一個人,你們怎么就容不下她?”話還沒有說完,就受到大家一致的責備,說妻子立場不堅定,胳膊肘子竟然向外彎。妻子很不高興,懷著一肚子委屈回到了家,把不快全部發泄到我身上,嚇得我不敢應聲,遠遠躲開了事。
大家呢,就嗑著瓜子,說著少婦的事情,坐等少婦回來。可沒想到一等沒見少婦回來,再等沒見少婦回來,到了第三天,一輛車開來,裝上少婦的東西,拉了就走。
院里有人趁機打聽,少婦是不是干那個的,要被趕出鎮子。
裝東西的人聽蒙了,一臉的驚詫,問道:“什么干那個的啊?”
“就是——就是那個啊。”有女人說,其余的女人都吃吃地笑著。
裝東西的人敲敲頭,迅即醒悟過來,笑了,說:“你們想哪兒去了,人家是工程師,到這兒是勘測和規劃路段。現在,這兒工作結束了,要到別處去勘測路段,走的時候,她還說舍不得你們,請我代她向你們道謝呢。”
“那自來水是怎么回事啊?”女人們還有些不信,問道。
“那是人家自己掏腰包給小院拉的,說小院人用水難。”裝東西的人說完,上了車,汽車一聲哼,走了,扔下一個院子的人,愣愣地站在那兒發呆。然后,一個個灰頭土臉地回去了,沒有一個吱聲。
穿旗袍的少婦已經離開了好長一段時間,可茶余飯后,院里的人們還是總會談起她,談起她那一身素淡的旗袍,談起她的典雅和她的善良,當然,還有她的文靜。尤其是妻子,一直稱呼她為“我們宛如”,一說起“我們宛如”就兩眼放光,嘖嘖稱嘆,說她高貴,說她含蓄,說她隨和。
不久,小鎮女人們也興起了旗袍熱。而最先興起的就是我們院子,第一個就是我的妻子。而且,我發現,自那以后妻子的性格也大為改變,變得文靜、隨和、善解人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