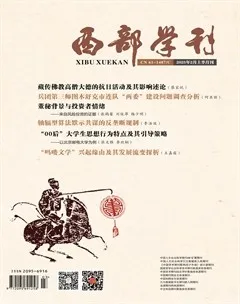馬克思關于歷史現象學闡釋研究
摘要:《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經典之作,其中反映出馬克思運用歷史現象學的原理,剔除一切形而上學的假設,回到歷史本身描述歷史,并將歷史還原到人的對象性活動中去。以還原歷史本身為出發點,通過對《德意志意識形態》進行闡釋與分析,從該文本中所反映出的歷史現象學的來源、基質和革命內涵,即“脫離超驗歷史哲學,復歸現實的個人本身”“揭穿純粹思辨的‘形而上’面具,轉向直接現實的歷史”“走出解釋歷史的迷霧,邁向創造歷史的康莊大道”三個部分進行分析,以期通過重讀文本的方式,挖掘、釋讀經典,體悟馬克思關于歷史現象學的闡釋研究。
關鍵詞:馬克思;歷史現象學;《德意志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A8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5)03-0050-04
A Study of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logy
— Taking The German Ideology as an Example
Li Yua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Abstract: The German Ideology is a classic work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this work, Marx applies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phenomenology, eliminates all metaphysical assumptions, returns to history itself to describe it, and restores history to the objective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Starting from the restoration of history itself,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German Ide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substance, and revolutionary connotations of historical phenomenology reflected in the text. These aspects are analyzed in three parts: “breaking away from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returning to the real individuals themselves”, “unmasking the ‘metaphysical’ guise of pure speculation and turning to the history of direct reality”, and “stepping out of the fog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moving towards the broad road of creating history”. The purpose is to excavate and interpret the classics by re-reading the text, and to understand Marx’s hermeneutical research on historical phenomenology.
Keywords: Marx; historical phenomenology; The German Ideology
首次出版于1832年、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創立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是馬克思、恩格斯體系化論述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文本,通過對西方歷史哲學體系的批判,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實現了批判與重構、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揭示了歷史本質為現實人的生產和實踐活動。我們回到原文,能夠體悟其中一以貫之的歷史現象學精神,剖析馬克思廓清唯心主義理論局限性的邏輯理路。
一、脫離超驗歷史哲學,復歸現實的個人本身
在西方歷史哲學建構中,柏拉圖、黑格爾、孔德、叔本華等哲學家都局限在頭腦中,向內解釋現實世界,無一例外地“同現實的影子作哲學斗爭”[1]510,此種線性歷史思維的做法,掩蓋了歷史真相,使一切人的活動失活。馬克思反對先驗建構理想世界,以歷史性思維從現實個人出發,用實踐方式認識動態發展的人類歷史,借歷史現象學的方法構筑起一個新世界。
(一)“形而下”自我意識中蘊含著現實的個人的自由精神
馬克思對“現實的個人”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采用哲學與歷史互感互化為基礎的構境論歷史思維,不斷地靠近歷史本身。
1.自我意識的主體性和自由:馬克思對觀念哲學與現實世界聯結的思考
馬克思的“自我意識”思考承繼于青年黑格爾派,因此他偏重對歷史哲學中的革命思維和哲學意蘊的思考,希望以此來對抗宗教神學對人精神的統治,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這一點在馬克思受布魯諾·鮑威爾指導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得以體現,他在序言中指出:哲學存在的價值旨歸即是將世界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正如普羅米修斯所說“總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2]12。
2.打破神諭命運的桎梏:馬克思對唯心主義歷史觀的批判
馬克思沒有像先前的哲學家一樣沉溺于解釋世界不可自拔,而是轉向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來改變世界。這反映在他對神意歷史觀和青年黑格爾派的批判中,馬克思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他希望人民掙脫思想鉗制,獲得個人精神和行動的自由。他同樣批判黑格爾左派賦予一切事物,包括歷史,以純粹概念化和抽象的含義,深陷于錯誤的歷史觀中。“哪怕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家和理論家們滿口喊的都是所謂‘征服世界’的語詞,但他們卻是最徹底的保守主義。”[1]516馬克思駁斥哲學家們沉溺于純粹理性的精神世界,認為現實的個人才是成就歷史的前提。
(二)現實的個人存在于歷史的發展過程中
青年黑格爾派僅在思辨層面將神意歷史觀還原到了哲學歷史觀中,然而其“自我意識”思辨的、臆造的歷史觀仍沒有觸及歷史的本質。馬克思意在將歷史還原為現實的個人,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馬克思拋棄抽象的人,對費爾巴哈抽象思維進行批判。費爾巴哈否定了使得世界烏煙瘴氣的一切思辨的形而上學,使哲學轉向到感性的范疇。然而,與黑格爾將歷史看作是絕對精神的運動相比,費爾巴哈雖批判思辨哲學的非歷史思維,但卻從人的類本質出發,固定了人的歷史屬性,這樣孤立、片面、抽象的人違背了人的歷史屬性和自然屬性相結合的原則。馬克思廓清了哲學對歷史主體的誤讀,他認為哲學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意識是屬人的意識[1]525。馬克思將歷史看作是現實的人的對象性活動所形成的動態的、不斷發展的人類史。
“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及其產生狀況來描述歷史,一切難解的問題都可以非常輕易地還原為某種經驗的事實。”[1]528馬克思痛斥一切錯誤的歷史觀,排除了之前的哲學家所定義的絕對精神、自我意思以及永恒不變的“人”,歷史當然也不是施蒂納認為的利己、離群的“唯一者”,而是現實的人所創造的實踐活動產物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的總和。并且,現實的個人總在變化的歷史中自我改變并改造周圍的物質世界,個人存在于這種“生存論”中,馬克思通過把握歷史現象學的原理,把歷史描述為人通過實踐自我創生的過程。
(三)現實歷史發展決定自我意識
抽象的哲學飄漂浮于現實世界的上空,虛浮于人的頭腦世界之中,并且哲學家們并不想轉換研究軌道,轉而解決現實問題,改變現狀。在歷史問題上,哲學家們置意識于世界之外,那么意識怎樣切中“此”岸、把握“彼”岸世界?也即胡塞爾認為的“認識怎樣才能認定自身與自在之物齊同,怎樣才能‘切入’這些事物?”[3]馬克思認識到理性并非認識歷史的充分條件,他顛倒了思辨哲學的歷史前提,摧毀了形而上學的底層建制——意識的內在性。那么如何突破意識的內在性這一底層建制?海德格爾提出,哲學以我思為源頭便再無法切中對象[4]。可見,只要意識的內在性不拋棄,對歷史做出預設的思維方式就難以廢除。
施蒂納用“唯一者”攻擊費爾巴哈,卻比費爾巴哈更快地陷入了意識的內在性建制中。馬克思批判其“幽靈現象學”,指出現實的人不斷創造歷史。因此,只有保持意識的獨立性外觀,才能突破思辨歷史邏輯的無限循環。意識具有社會歷史性,這是馬克思對意識內在性的直接反駁。馬克思在《形態》中寫道:沒有被意識到的存在不是意識[1]525。由此可見,馬克思認為意識和人的實踐活動交織在一起,并且意識是個人感性活動的表達,本身就是在外的,而不是在內的。并且,馬克思將語言與意識等同,強調了意識的外在性,認為語言和意識一樣,產生并服務于人類實踐[1]533。馬克思終止了無休無止的思辨,還原出了意識的社會歷史性,完成了對形而上學歷史觀批判的第一步。
二、揭穿純粹思辨的“形而上”面具,轉向直接現實的歷史
阿爾都塞提出:“在哲學革命能夠獲得一個清晰且確定的架構之前,總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理論積累和自我調整的歷史過程。”[5]馬克思利用歷史現象學的方法建構起的新唯物主義批判繼承黑格爾、施蒂納等歷史形式主義理論,以現實人的物質生產為基礎,從生產力與交往方式辯證關系鋪敘歷史發展過程。
(一)社會現實的岔路口:馬克思與黑格爾
馬克思與黑格爾在針對作為歷史本質的社會現實的理解上產生了偏差。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提到:“現實是本質與實存或內與外所直接形成的統一。”[6]現實和理想交織糅合,“切合理性即現實,反之亦然”[7],黑格爾將理性作為衡量的尺子,丈量現實。他把歷史的社會現實性設置在客觀思想,即絕對精神上,使得現實的歷史本身變成了思辨的歷史,是“神學的已死的精神”。黑格爾的歷史原理有局限性,即困于思辨邏輯而無法脫離形而上學怪圈,同時局限于唯靈論,未從人的感性活動出發建構歷史,二人最終于“社會現實”的十字路口分道揚鑣。
(二)黑格爾思想的“異在”:施蒂納
馬克思對施蒂納的批判貫穿于《形態》中,馬克思認為施蒂納表面上是在反對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實際上是利用黑格爾唯心主義歷史觀而已。施蒂納主觀臆斷地把握歷史,將歷史分為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并分別對應三種利己主義者,此三階段的歷史主義觀無不對應著黑格爾思辨歷史哲學的“正—反—合”三段式,這種拋開特定歷史階段特點,直接套用黑格爾哲學的三段論推導社會發展規律的做法遭到了馬克思的反駁:“抽象的意識支配了歷史,因此歷史也就淪為了單純的哲學史”[8]149。對此,馬克思認為正確的歷史觀一定是立足于人的實踐活動的,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透視歷史的演進法則,他批判施蒂納主觀臆斷式的歷史觀,認為這只是一種思維的把戲而已。
(三)物質生產活動:歷史于現實世界的復歸
在思想論戰中,施蒂納對馬克思繼承費爾巴哈關于人的最高本質的價值懸設提出了批判,使馬克思意識到了人本主義的威脅所在,引發了他哲學立場的改變。施蒂納對馬克思擺脫費爾巴哈哲學影響的作用有二:第一是馬克思關于人本主義的反省,第二是馬克思關于物質生產的思考。比如在對改變物質世界的認識上,施蒂納所提出的“我們應該改變環境,要徹底地改變它,使偶然性變得不起作用”[9]158,與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十一條的“改變世界”均聚焦于改變現狀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再比如,施蒂納說:“固定的觀念被當作‘準則、原則、立場’等…塵世的活動被居高臨下地俯察并遭到蔑視”[9]68。他們對這種觀念高高在上,而生產實踐活動處于俯視的下位的現象有相同的認識,并且認同實踐長久以來被忽視與低估了。
馬克思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的“理想化勞動”替換為“一段歷史條件下的社會生產活動”,對歷史的思考從社會關系深入到了物質生產。施蒂納提出了費爾巴哈哲學認識的不足之處,為馬克思摒棄意識層面的困擾,最終走向歷史唯物主義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馬克思在《形態》中對唯物史觀作了簡要概述:從現實的物質生產為起點解釋生產過程,將不同時期的物質生產關系總括為歷史的基礎[1]544。他轉向人類實踐,從生產力演進以及社會交往變化的角度看待歷史,透視現象看本質,找尋人類社會向前推進的動力源泉,進而把握歷史主動。
三、走出解釋歷史的迷霧,邁向創造歷史的康莊大道
傳統西方歷史哲學用先驗原則解釋世界,脫離現實生活,使實踐失去價值。馬克思運用歷史現象學原理,終止抽象思辨,轉向生成論歷史觀。“說句真話,我痛恨所有的神靈。”[2]36他認為歷史由現實的個人創造,是生成性、未來性的。馬克思摒棄了一切探尋世界本源的錯誤認識,轉而把握主動,改變世界,作為共產主義者第一次回答了歷史的本質。
(一)詮釋與改造的統一:歷史現象學闡釋
之前的哲學家無一不局限于意識,追尋終極真理,他們具有以下的共同特點。從先驗原則出發推理人類歷史,這樣推演概念、演繹推導,非常容易“使得讓歷史變成了為了實現預設理想而努力的天命論、前定論和預成論”。這些預設的原則不隨時間和空間轉移,而從一個固定不變的預設前提出發,意味著未發生的歷史結果業已窮盡,歷史成為虛無。抽象的哲學致力于邏輯推導,忽視事物以及事物之間聯系的直接現實性,自說自話地從假設的源頭推理現實事物的未來,甚至人的命運。這種概念的運動是宿命論的,人能動的創造性都被思辨的邏輯所遮蔽,哲學家們拿起“斧頭”,想要以普適的結論定義歷史走向。
馬克思認識到世界本無邏輯構建出的終點,一切在于創造。他從生產實踐的角度揭示社會更迭、歷史變換,將人、世界置于現實的歷史中考察,吸取歷史上哲學家之長,結合改造世界的愿景,強調詮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辯證統一。馬克思利用歷史現象學的原理,既辯證地思考歷史“從何而來”,也科學地規劃歷史“到何處去”,在把握歷史規律的基礎上創造人類美好的未來。
(二)“劇作者”與“劇中人”的統一:歷史科學
馬克思站在現實歷史角度創建的歷史科學,他提出,終于思辨起于現實中,科學誕生了[1]545。馬克思使用歷史現象學的方法,在《形態》中構建了一門朝向歷史本身的科學:“唯一的科學是歷史科學”[1]516。這種歷史科學要朝向歷史本身,聚焦生產實踐活動的演進,通曉歷史規律而創造未來。這里的“歷史”指的不僅僅是文獻中記載的人類社會過去發生的事件和活動,而主要指代的是當下人們正在發生的感性的對象性活動。這里所指的對象性活動是歷史科學的原點,并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自我意識不應超脫于主體本身,它并不是抽象的,而是集“劇作者”的作品和“劇中人”的實踐于一體的。
(三)共產主義對歷史之謎的回答
追求人的解放是馬克思畢生的志向和終極的目標。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不是空想的,而是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對歷史之謎的真正解答”[1]539。共產主義的實現并非來自于自我意識的空轉,而是來自于人類現實的勞動實踐所創造的物質世界之上。共產主義的實現與把握歷史規律基礎上所達成的現實活動基礎密不可分,二者的關系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共產主義興盛的先決條件是高度繁榮的生產力基礎和深厚的經濟財富。馬克思說:“若無這種發展,則只會有極度窮苦的廣泛化,而在極度窮苦的狀況下,一切腐朽污濁的東西又將死灰復燃。”[1]538也就是說,沒有充足豐厚的物質基礎,何談自發自愿的人類活動。第二,共產主義政黨需要緊握用來改造物質世界的根本條件。馬克思親眼看到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在泥沼中掙扎前行,而他們正是最適合實現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具備革命的激情。第三,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制和強制性分工。分工具有二重性,雖然能夠推動生產力發展,但異化強制的勞動分工必然造成人與人分離對抗,摧殘人的肉體與精神,因此必須消滅造成人片面性發展的強制性分工。第四,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是宏大的歷史革命愿景,建立起歷史的、科學的方法論是必要條件。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是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得以實現的先決條件[1]534。只有運用辯證的、革命的歷史主義方法論指導實踐活動,才能走向共產主義。
四、結語
人們這樣評價《形態》:這部著作閃爍著新世界觀的天才光輝,是闡釋歷史唯物主義最全面、最系統、最完善的馬克思哲學經典著作,是馬克思哲學革命成果的集中體現。用歷史現象學方法解讀馬克思文本,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深入新時代現實生活,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活動。進而撥開歷史虛無主義障蔽,為新時代建設實踐提供科學方法論支持。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
[3]埃德蒙德·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M].倪良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7.
[4]F.費迪耶,丁耘.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J].哲學譯叢,2001(3):52-59.
[5]復旦大學哲學系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207-208.
[6]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295.
[7]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1.
[8]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49.
[9]麥克斯·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作者簡介:李媛(1999—),女,漢族,甘肅慶陽人,單位為西安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責任編輯:馮小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