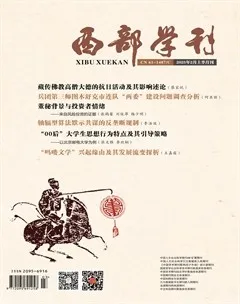互惠共生視角下“和美鄉村”互助養老服務提升路徑研究
摘要:提升養老服務水平是和美鄉村建設的應有之義,就地互助養老模式為農村老年人提供了新選擇。利用互惠共生理論分析框架探討和美鄉村互助養老共同體的構建,強調互助養老模式應整合資源、轉變養老服務供給方式,并運用該理論拓寬研究視野。選取浙西X鎮為例,實證分析了農村互助養老服務互惠共生模式的成功實踐,指出當前和美鄉村互助養老服務面臨意識淡薄、體制機制缺位和多主體參與度不高等問題,據此提出了轉變觀念、完善機制、加強引導等方面的建議,旨在打造多主體參與、資源整合的互助養老服務體系,推動和美鄉村建設與互助養老服務的互惠共生發展。
關鍵詞:互惠共生;和美鄉村;互助養老服務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C913.6;F323.8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5)03-0163-06
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istic Symbiosis
— Taking X Town in Western Zhejiang as an Example
Ye Han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Longyou County Committee, Zhejiang Province, Quzhou 324400)
Abstrac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and the local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model provides a new choice for rural elderly people. By us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tualistic symbiosis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community in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has been explored, emphasizing that the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model should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transform the supply mod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use the mutualistic symbiosis theory to broaden research perspectives. Taking X Town in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mutualistic symbiosis model of rural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services has been empirically analyz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currently, the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are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weak awareness, lack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low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Based on this, suggestions in aspects like changing concepts, improving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guidance have been put forward, aiming to create a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services system with 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to promote the mutualistic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as well as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services.
Keywords: mutualistic symbiotic; beautiful and harmonious countryside; mutual aid elderly care services community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統籌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布局,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1]。建設和美鄉村不僅需要人居環境優美、產業興旺,同時也需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共生。作為農村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升養老服務水平是和美鄉村建設的應有之義。傳統的養老模式以家庭自主養老及國家自上而下推動的養老院、社區養老等方式為主,政府、社區、家庭、企業等多元主體都參與其中。隨著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升,大批農村青年人到大城市謀生,傳統農村家庭養老功能日趨弱化,加之農村老年人經濟承受能力有限,機構養老在農村的普及度不高,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互助養老模式方興未艾。互助養老行為的一方是低齡有勞動力的老年群體,仍能創造一定的經濟價值,另一方是高齡、生活自理困難甚至失能、半失能的高齡老年人,亟須生活照料。基于農村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由低齡老年人照顧高齡老年人的互助養老模式成為可能,能夠實現低齡老年人價值實現和高齡老年人獲得照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提出要“構建農村互助式養老服務網絡”[2]。互助養老模式為和美鄉村建設過程中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提供了新選擇,也為應對“未富先老”的現實狀況紓解了壓力。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一)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農村互助養老研究已形成一些較有價值的觀點。在農村互助養老主體研究方面,劉妮娜[3]建議通過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推動各類互助組織共同構建鄉村互助養老體系;王立劍等[4]把老人參與互助養老供給模式分為情感型、低管理型和高參與型等5種模式。在農村互助養老提升路徑研究方面,張繼元[5]發現農村互助養老可通過聚集態結構、自組織化等形式降低成本,提升互助養老效率;楊康等[6]建議通過培育社會信任、完善社會網絡等路徑培植農村互助養老的社會資本;劉曉梅等[7]認為農村互助養老應兼顧需求者和供給者的雙重需求,進行社會資源的調配;米恩廣等[8]提倡通過優化政策、創新服務方式、完善服務機制等路徑實現農村互助養老服務供給效能的整體性提升。在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研究方面,孫文中[9]提出通過整合婦女志愿者力量、運用“82兌換模式”等激發“時間銀行”互助養老發展動力;齊鵬[10]提出以多主體共治的方式推進農村幸福院機構化、社區化運作;朱火云等[11]建議要構建以政府為主導、以民主協商為基礎的縱向、橫向協調治理機制來加強農村幸福院的建設和運營。
國內外學界對農村互助養老的研究范圍涵蓋概念界定、內涵機理、模式體系、實踐探索、發展建議等多維度,盡管實證和案例研究中發現實踐過程中存在管理不規范、政府投入不足、社會資本參與不夠等共性問題,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議,但是大多數研究集中于對老年人或是政府、資金等單一養老要素的分析,對村莊治理共同體的系統研究較少,對農村互助養老行為背后的文化動因探討不多。因此,本文從互惠共生的視角對和美鄉村建設中的互助養老模式提供建議,挖掘傳統孝道文化與和美文化在互助養老過程中的深厚底蘊,更具有時代性和針對性,以期彌補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過程中對鄉村老年人關懷研究相對欠缺的不足。
(二)問題的提出
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背景下,作為和美鄉村公共服務的重要一環,農村養老值得關注,目前需要回答三個問題:一是在大城市虹吸效應和縣域城鎮化的影響下,大量人口流向城市,農村留守老人數量增加,養老服務主體減少,如何引導和鼓勵家庭、政府、互助組織、志愿者等多主體參與養老服務,激發其參與互助養老服務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二是隨著機構養老、社區養老、搭伴養老等新型養老模式的出現,如何實現互助養老與傳統家庭養老服務模式相結合,讓老年人安度晚年,同時滿足其生活服務及精神文化需求;三是作為農村公共服務的一部分,農村互助養老如何嵌入基層治理,通過打造互助養老服務共同體弘揚和美文化、助力和美鄉村建設。鑒于此,本文基于互惠共生的研究視角,從打造基層治理共同體、和美文化共同體、產業振興共同體、醫養融合共同體、數字服務共同體等方面嘗試回答以上問題。
二、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
(一)互惠共生理論
共生理論最早在生物學領域被提出,德國生物學家德貝里運用此理論來分析不同環境狀態下各類生物共同生存、相互依賴的關系,后來共生理論被引用到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多領域[12]。共生模式是共生環境中各單元相互作用的形式,國內學者袁純清[13]將共生行為分為寄生、對稱互惠共生等四種模式,其中互惠共生是經濟社會生態系統演變的最終方向。互惠共生是共生單元在一定的環境下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適用于研究不同共生單元間的相互關系,為探究和美鄉村互助養老模式提供了理論借鑒。
(二)分析框架
1.和美鄉村互助養老共同體構建。互助養老克服了傳統家庭養老模式中每個家庭老年人相對“孤立”以及養老服務資源碎片化的問題,整合鄉村熟人社會的村集體、家庭、鄰里照料資源,實現從自上而下的政府養老服務供給模式到地緣聯結、扁平式的互助模式轉變,構建鄉村鄰里互助的和諧場景,契合和美鄉村建設理念。運用共生理論有利于拓寬農村互助養老主體間單一互助關系的二元對立研究思路,探尋互助共同體的關系、充分發揮多方優勢的路徑。筆者將共生環境劃分為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內部環境主要包括村莊社會環境和老年人家庭環境,外部環境包括政策環境、市場環境、發展環境等。共生單元是互助養老的各行為主體,主要包括政府、村集體、社會組織、家庭成員、低齡老年人、青年人等,各主體間存在相互作用、互惠共生的關系形態,可將互助養老歸類為青老互助共生、老老互助共生、社老互助共生等類型,共生單元間的共生模式可歸類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收入提升、補貼家用、傳統技藝傳承等方面。互助養老共同體依托多樣共生單元、整合多種共生模式,推動互助參與和互助合作保障行為,實現由老年人個體的生存目標向鄉村建設利益共同體的構建目標轉變。
2.互惠共生動力機制。和美鄉村建設涵蓋鄉村振興、宜創宜業、和諧善治等方面的內容,作為共生環境中的共生單元,老年人與養老主體間的信任與互惠是構建鄉村互助養老共同體的基礎,一方面,老年人尋求自上而下的政府及養老政策支持、扁平化的市場主體、社會組織服務、耦合式的村集體與青年人互助行為和嵌入式的家庭和鄰里幫助;另一方面,互助養老服務過程中各服務主體產生了超越親緣和地緣的利益聯結,互助參與和合作不斷增強,互助養老共同體由此構建,助力村級治理與村莊發展、和美文化建設。老年人在整個互惠共生機制中始終處于核心位置,低齡老年人處于互助養老服務鏈條中的供給端,高齡老年人處于需求端,政府、村集體、家庭成員、鄰里等都在互助養老服務共同體中各自發揮作用,以提供多樣化養老服務為載體,構建出基層治理、醫養融合、產業振興、和美文化等方面的共同體,有助于和美鄉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領域的建設,如圖1所示。
三、案例分析:浙西X鎮“一鎮帶三鄉”抱團發展片區農村互助養老服務互惠共生模式
為進一步呈現農村互助養老服務共同體打造的可行路徑,選取浙西X鎮為案例,探析互助養老服務互惠共生模式的形成機制。X鎮是全國重點鎮、省級中心鎮,生活相對比較便利,臨近地區有M鄉、D鄉、M鄉,四個地區地域相鄰,歷史文化一脈相承,“三鄉”群眾常到X集鎮求學、就醫、購物等,由此打造了“一鎮帶三鄉”抱團發展片區。得益于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政策紅利,在多主體的共同努力下,X鎮老年人的互助養老服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自上而下與數字賦能:智慧互助養老
X鎮未來鄉村原為黃鐵礦宿舍區,老年人較為集中,在政府的行政主導下,通過數字賦能打造15分鐘“養老服務圈”。依托智慧養老云平臺,為未來鄉村獨居老人家中安裝智能監控、SOS報警器,同步配備智能手環,通過系統后臺的煙感報警、心率報警、血壓報警等實現老年人的動態健康監測。工作人員通過遠程看護系統隨時關注老人的動向,一旦發現緊急情況,實現第一時間上門、第一時間幫扶、第一時間救助。X鎮政府注重數字化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在未來鄉村中安裝了智能感應路燈、智能讀書(聽書)房等便利老年人日常生活的設施。82歲的老年人H表示:“我是黃鐵礦工人退休,子女都在外地,幾年前就讓我跟他們住,我去他們身邊又幫不上什么忙,還給子女造成負擔。而且住在這里幾十年,習慣了,也不想離開這里,現在生活很方便,都是上門服務,出去逛逛環境也好,連垃圾桶都是自動的。”這種由政府主導、志愿者參與、數字賦能的自上而下式互助養老模式為老年人創造了便捷、安心的生活環境,受到未來鄉村老年人的歡迎。
(二)自發與耦合:D鄉“6090”銀發互助聯盟
D鄉成立“6090”銀發互助聯盟,全鄉60周歲以上的低齡健康老年人與高齡老人、獨居老人、低收入老人、殘疾老人等結對,自發提供互助養老服務,主要包括生活服務、居家照料服務以及精神文化服務等。目前以F村為試點,成立一支有101人的“6090”銀發互助聯盟,其中“60”成員15名。整合居家養老服務照料中心、老年大學、新時代文明實踐站等組織力量和資源,銀發志愿者為老年人分類提供送餐、精神慰藉、居家照料、化解矛盾等服務。目前D鄉的“6090”互助養老均以自發和自愿行為為主,低齡老年人在此過程中實現“老有所為”,日常生活更加充實,在農村聲望更高。如71歲的Y是F村人,曾經當了50多年的鄉村醫生,現在他成了F村“6090”銀發互助聯盟盟長,經常為村里老人提供上門醫療衛生服務。他表示,“家附近的7戶老人都由我結對聯系,大家都是鄰居,相互照顧做點力所能及的瑣事及一聲問候是應該的”。在D鄉X村,銀發互助聯盟中的老人們經常在一起進行文藝表演,不僅讓參與其中的老年人感受到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更讓觀看的老年人體會到集體的關愛。獨居老人Z說:“兒子媳婦都在外打工,我平常都一個人在家,現在各個節日能和這么多人一起過,也不覺得孤單了。”通過文化活動,低齡老年人與高齡老年人推進了日常生活的供需耦合。
(三)扁平化治理與互利:居家養老服務中心
X片區與第三方服務機構合作,打造“公社食堂”,為老年人提供三餐,老年人可以享受每餐10元的特色餐,葷素搭配、營養均衡,也可以為黃泥山小區80歲以上的老人送餐,每餐收費2元。對于行動不便的老年人,食堂工作人員會提前備餐,并由志愿者為老年人送餐,以保障高齡以及半失能、失能老年人的用餐需求。M鄉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為老人提供堂食,為行動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門送餐服務,通過市場化運作的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和文體娛樂等服務,引進有資質、懂老人、會經營、責任心強的市場主體,政府對經營主體進行監督,老年人對市場主體進行評價,在市場主體獲利的同時老年人享受服務,形成扁平化、全周期的互助養老管理體系。
(四)嵌入與反哺:老年人助力青年創客聯盟產業發展
X鎮“一鎮帶三鄉”片區擴大青年就業創業和民生服務保障的覆蓋面,吸引了原鄉青年歸鄉、外鄉青年來創業,一方面部分老年人在家就能為身邊子女照顧孩子,解決青年就業創業的后顧之憂,青年人也能通過日常照料反哺老年人;另一方面具有勞動能力的老年人積極參與青年創客聯盟,通過傳統技藝傳承助力鄉村產業發展,目前溪口有40余名老年人參與“一盒故鄉”傳統工藝品制作,上百名老年人通過制作小吃(裹粽子等)實現創收。X鎮的老年人W原先在家里做來料加工,一個月收入1 200元左右,現在參與到裹粽子、蒸發糕等“一盒故鄉”的發展計劃中,每個月能有3 000多元的收入。她說:“現在既能在家干活照顧家庭,又能和其他老人一起邊聊天邊干活,每天都很充實,收入還能補貼兒女,我對此感到十分滿意。”老年人在增收的同時嵌入到鄉村的發展過程中,改變了以往局限于家庭、“脫嵌”于社會的狀況,真正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樂,形成了產業振興共同體。
在多個共生單元主體互惠互助的過程中,老年人與村集體、青年人等逐漸形成了不可分割、連續共生的共同體,互助養老服務內涵范圍逐步拓寬,智慧互助養老服務助力打造醫養融合共同體和數字服務共同體,“6090”銀發互助聯盟運行過程中蘊含的孝道文化、互助文化以及矛盾化解等行為都能協助打造基層治理共同體、和美文化共同體,老年人參與青年創客聯盟助力發展產業振興共同體,多種互助養老模式超越了單一的二元互助關系,形成了多主體共生互惠的共同體。
四、和美鄉村互助養老服務存在的問題
作為一種新型的農村養老模式,互助養老經濟成本低、不脫離農村熟人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目前農村老齡化問題,適用于和美鄉村建設,盡管互助養老模式已經在很多地區進行摸索實踐,但在具體的實踐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一)互助養老意識淡薄
受到傳統養老觀念的束縛,一些老年人參與互助養老的意識不強,“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大多都傾向于家庭養老,還可為子女創造價值,如照料小孩、補貼家用等。家庭條件較好、家人無暇照顧的老年人會去養老院或養老服務中心,目前真正參與互助養老服務的老年人數量還不多,主動服務意識不足,專業性不強,互助養老服務以村里的黨員定期走訪慰問為主,以鄰居偶爾幫忙做家務為補充,依靠多年的“交情”維持互助養老的狀態。部分老年人尚未轉變觀念,有的認為幫助年齡較大的老年人擦洗身體、換洗衣服等是“臟活”,寧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意到人家里照料老人;還有部分年齡較大的老年人,擔心自己的隱私被人“窺探”,不愿意由家人之外的其他人承擔日常照料的工作,互助養老模式還沒有推廣開來。
(二)相關體制機制缺位
近年來,隨著精準扶貧政策的實施,國家加大農村養老方面的資金投入,但與實際養老需求仍不匹配,尤其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盡管配備了一些居家智慧養老設施,但是在整個鄉村領域適老化、數字化設備投入不足,如養老助餐管理系統、民政養老監管系統、可視化智慧醫療平臺等都還未接入,對老年人跨越數字鴻溝的培訓宣傳較少。養老服務的監管和評價機制不完善,第三方機構入駐后,對市場化運營過程中的養老服務監管不足,除了日常的老年人口頭評價外,缺乏正式的反饋、退出機制,政府在購買社會化服務時缺乏統一的標準,導致互助養老服務管理質量不高。雖然部分地區借鑒“時間銀行”的模式推出“愛心卡”等服務,但在補貼發放、家政服務、醫療護理等方面服務質量的跟蹤測評還不夠,形式大于服務內容的情況依然存在。
(三)多主體參與度不高
引導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參與農村互助養老的激勵制度不完善,涉及安全隱患和矛盾糾紛沒有明晰權責,降低了多主體進入農村互助養老領域的主動性。以青年為例,如今隨著城鄉要素流動加快,農村地區年輕人更向往去就近的大城市發展,勞動力轉移,在大城市打拼生活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大多數都是以老年人幫襯為主,少數有孝心的青年能顧上家里老人,互助養老主動性不強。村集體也是一樣,村“兩委”只能階段性地關心老年人,不能常態化地照顧,對真正有養老需求的老年人多是通過低保低邊補助進行幫扶。志愿者數量有限,且互助養老服務是主觀性較強的工作,主要遵從服務主體的意愿,無法對其服務行為進行硬性規定及考核,導致服務質量良莠不齊。
五、對提升互惠共生視角下和美鄉村互助養老服務的質量建議
作為一個新生事物,農村互助養老服務正在普及,需要汲取各地區互助養老服務的先進經驗,如桐鄉市石門鎮墅豐村“時間銀行”鄉村互助養老模式、湖州市安吉縣的“愛滿空巢”為老服務項目等,同時結合每個地區的發展實際,積極探索提升路徑。
(一)轉變觀念,增強參與意識,打造基層治理共同體、和美文化共同體
農村互助養老服務質量提升的前提是老年人樂于提供并接受養老服務,以現在的服務他人來換取今后所需時他人的幫助,要從理念上進行宣傳勸導。通過推廣“時間銀行”等互助養老模式,幫助村民認識到當前所從事的養老服務行為能夠換取積分,積分可以兌換實物或是兌換今后青年人對自己進行的養老服務,幫助村民更加具象化地認識到互助養老服務的長遠性和互利性。樹立互助養老典型,利用新聞媒體、社交平臺等進行推廣,積極宣傳互助養老的作用,引導廣大村民投身互助養老,讓村民意識到養老問題并非個人或是家庭的事情,而是村集體和大家的事情,增強村民的集體意識和責任意識,營造尊老養老助老的文化氛圍,弘揚孝道文化,打造基層治理共同體、和美文化共同體。
(二)完善機制,提高服務質量,打造數字服務共同體
建議政府出臺互助養老的實施指導方案,建設互助養老配套設施,普及養老知識,培訓養老護理專業人員,為提高養老服務水平奠定基礎。建立互助養老服務市場化運營評價考核機制,通過政府考評、老年人評價、服務質量評估等多個維度對第三方機構的養老服務進行評價,考核結果與后續的準入及運營緊密掛鉤,明晰各部門的權責,引導互助養老市場主體規范化運作。指導各村建立互助養老組織,培育一批助老志愿者,形成獨具村級特色的互助養老品牌。以需求為牽引打造數字化、智慧化的養老服務平臺,根據老年人的實際需求,在智慧化養老服務平臺上對服務內容進行更新,借助數字化手段真正讓老年人獲得在線問診、健康監測、生活服務等便捷的養老服務,形成數字服務共同體。
(三)加強引導,整合服務資源,打造產業振興共同體、醫養融合共同體
農村互助養老服務需要多主體共同參與,政府應多措并舉引導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等參與互助養老,引入“時間銀行”與“互助養老儲蓄銀行”等創新互助養老形式,提升互助養老的參與積極性。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為有勞動力的老年人進行產業匹配,以傳統技能進行再就業創收,為農村經濟發展創造價值;盤活農村的閑置勞動力資源,組織志愿者服務隊伍,加強互助養老隊伍技能培訓。村集體可將部分閑置資產改建為互助養老服務中心,通過開展保健活動、戲劇表演、下棋比賽等多種形式的文體活動滿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鼓勵醫院、護理院下沉,搭建村級衛生室和互助養老服務點,為老年人提供醫養服務,打造產業振興共同體和醫養融合共同體。
六、結語
作為農村公共服務的一部分,農村互助養老服務嵌入農村社會發展,吸引多主體參與,助力打造基層治理共同體、和美文化共同體、產業振興共同體、醫養融合共同體、數字服務共同體等,對弘揚和美文化、和美鄉村建設發揮著積極作用。今后要提升和美鄉村互助養老服務水平,完善政策和制度,優化村級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群眾支持等社會保障機制,營造孝老敬老的文化氛圍,形成互助養老與和美鄉村發展互惠共生的良性循環,推動農村養老服務水平穩步提升。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2022-10-25).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新華社.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EB/OL].(2022-02-21).
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1/content_5674877.htm.
[3]劉妮娜.中國農村互助型社會養老的定位、模式與進路[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3):133-141.
[4]王立劍,楊柳.老年人參與農村互助養老服務供給的模式特征及其影響因素[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151-162.
[5]張繼元.互助養老的福利自生產機制:互惠的連鎖效應與結構效應[J].山東社會科學,2021(10):116-123.
[6]楊康,李放.社會資本視角下農村互助養老發展的現實路徑[J].長白學刊,2022(3):130-139.
[7]劉曉梅,劉冰冰.社會交換理論下農村互助養老內在行為邏輯與實踐路徑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21(9):80-89.
[8]米恩廣,李若青.從“碎片化運行”到“協同性供給”:農村互助養老服務有效供給之進路[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86-93.
[9]孫文中.“時間銀行”農村互助養老服務的賦權機制[J].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1):64-72.
[10]齊鵬.農村幸福院互助養老困境與轉型[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2):105-116.
[11]朱火云,丁煜.農村互助養老的合作生產困境與路徑優化:以X市幸福院為例[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62-72.
[12]LEWIN R A.Symbiosis and Parasitism: Definitions and Evaluations[J].Bioscience,1982(4):254-260.
[13]袁純清.共生理論及其對小型經濟的應用研究(上)[J].改革,1998(2):101-105.
作者簡介:葉菡(1988—),女,漢族,浙江衢州人,中共浙江省龍游縣委黨校講師,研究方向為社會學。
(責任編輯: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