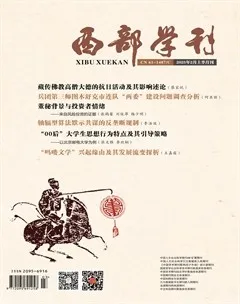“嗎嘍文學”興起緣由及其發展流變探析
摘要:“嗎嘍文學”是一種具有廣泛傳播性和互動性特點,富有冷幽默語用風格的網絡語言表達形態,成為“Z世代”網絡青年群體表達意見、宣泄情緒、映射焦慮、書寫困境的媒介之一。在個人情緒的媒介映射、“喪文化”的衍生、語言模因的強勢復制、精神退行下的本質回歸等背景之下,“Z世代”青年群體通過適度、有分寸的“嗎嘍文學”,在互聯網平臺實現個人的情感抒發、身份共鳴、群體認同與社會歸屬,借此緩解現實生活中的苦悶與壓力。“嗎嘍文學”蘊含著網絡文化、大眾文化、媒介文化等多種影響因素,反映出網絡流行語對青年心理和社會發展的文化影響與傳播意義。
關鍵詞:“嗎嘍文學”;溯源;表現形式;心理機制;傳播邏輯
中圖分類號:G206;H1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5)03-0088-05
An Analysi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alou Literature”
Wang Jialu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Abstract: “Malou literature” is a kind of network language expression for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dissemination and interactivity, rich in cold humorous pragmatic style,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edia for the “Generation Z” network youth group to express opinions, vent emotions, mapping anxiety and writing dilemm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edia mapping of personal emotions, the derivation of the “demotivation culture”, the strong reproduction of language memes, and the essential return of spiritual regression, the young people of “Generation Z” achieve personal emotion expression, identity resonance,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belonging on the Internet platform through moderate and proportional “Malou literature”, so as to alleviate the depression and pressure in real life. “Malou literature” contains many influential factors such as network culture, mass culture and media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cultural influence and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ce of network buzzwords on young people’s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Malou literature”; trace to the source; the form of express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propagation logic
“嗎嘍文學”是一種擁有廣泛傳播性、簡易二創性的幽默語言表達形態,是當代互聯網青年群體消解精神壓力、抒發現實苦悶的大眾文化產物之一。本文從“嗎嘍文學”產生緣由入手,嘗試探繹其興起的表現形式、社會心理機制和深層傳播邏輯。
一、“嗎嘍文學”溯源
“嗎嘍”成為網絡熱詞,出現在2022年春節前的“砂糖橘狂熱”。互聯網青年群體對于廣西砂糖橘囤貨行為產生出極大的熱切,紛紛催促砂糖橘盡快上市。不堪重負的廣西商家發圖調侃“嗎嘍的命也是命”,這一圖文雙構的表情包成為“嗎嘍文學”興起的淵藪,很快造就了席卷互聯網的第一波高浪。隨后出現的“嗎嘍文學”大多采取“文字+表情包”的創作形式,以“‘嗎嘍’形象+詼諧文字”為主體構成要素進行創作。比如,“嗎嘍有淚不輕彈”“你醒啦,你已經變成嗎嘍了”等。“嗎嘍文學”在社交媒體平臺橫空出世,與“凡爾賽文學”“廢話文學”等網絡流行語并肩,成為“Z世代”青年群體手中最火熱、最保值、適用性最廣的私人虛擬不動產之一。
“嗎嘍”本字為“馬騮”,是兩廣地區稱呼“猴子”的方言語態。王小盾從語言學角度考察漢藏語猴祖神話譜系,認為作為猴祖的“猱”,從“矛”得聲,中古泥母豪韻(nau),上古音讀如“mlu”,因此現代廣州話中“馬騮”一詞實際上就是古音“mlu”的遺留[1]。“嗎嘍”就是猴子,作為在生理、遺傳進化等方面均與人類存在諸多形似的靈長目動物,擁有與人高度相似的生理形態結構,面部表情靈活生動,動作舉止同樣擁有“類人”特征。“嗎嘍”形象配合文字制作而成的表情包一經出現,便在社交平臺產生了不可小覷的病毒式傳播能力。“嗎嘍”普遍具有神情低落、舉止頹喪等特征,不同于前一階段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發瘋文學”,“嗎嘍文學”并不激進。與高度夸張、情緒激烈、邏輯蠻橫、語言無序的“發瘋文學”相比[2],“嗎嘍文學”更偏重于“喪”與“嘲”,它以一種溫和的“軟著陸”姿態,接手了網絡青年群體在猛烈發泄情緒之后產生的空虛、混沌、頹喪與無力。
“嗎嘍文學”承載著互聯網時代青年群體無處宣泄的“喪”氣,以自嘲與戲謔的方式將現實生活中的苦悶與暗面剖于燈下,將心中壓抑的頹喪與不滿展于人前,為社會高速發展背景下的青年心理健康提供了一種舒緩途徑和修護手段,以勢不可擋的姿態席卷網絡。“累死‘嘍’”“硬撐‘嘍’”“活著就是打工‘嘍’”,網民用風趣自嘲的語言調侃在工作和學習的高壓下不堪重負、無處傾訴苦悶的無奈與苦楚。無力擺脫,那就只能承受,秉持“有人看樂子,有人照鏡子”的虛擬世界交往原則,無數青年群體在隱匿真實身份的互聯網上找到了“同伴”,穿著松垮西服的“社畜嗎嘍”們得以會面。人們通過網絡流行語在虛擬網絡廣場中得到群體歸屬感,在同樣焦慮、同樣疲憊、同樣頹喪的群體戲謔中獲得身份共鳴和集體認同。網絡青年們在“嗎嘍文學”的大被下相擁而眠、抱團取暖,在短暫的“喪”中會心一笑,逐漸消解現實生活中的負面情緒,緩解緊繃已久的壓力,實現精神壓力的無負擔代償。自此,“嗎嘍文學”成為一種新興的互聯網交往手段與話語方式。
二、“嗎嘍文學”的表現形式
“嗎嘍文學”作為新興的青年亞文化衍生物,經由網絡廣場延伸化和擴展化的推動得以跨界傳播,在社交媒體平臺經過多用戶、多用途、多年齡層的二次創造,實現了大規模、廣范圍的使用與傳播,隨之誕生了多種表現形式。
(一)文段語料
文段語料即單純的文本結構,僅靠文字組合表達豐富情感,依靠使用雙方的語言思維和文字思維營造特有交流氛圍,主要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1.自我勉勵型
嗎嘍雖然只是嗎嘍,但也不是因為一點什么有的沒的就會要死要活的嗎嘍。嗎嘍只是比較笨,但是嗎嘍很善良,這就夠了。每日默念:嗎嘍的命也是命。
2.崩潰發泄型
學習關我什么事我可是只嗎嘍(浪蕩在樹林之間)(不經意地順走路人的香蕉)(纏著樹藤從左蕩到右)(落在高山上高原長嘯)(啊嗚嗚)(手拍嘴)(啊嗚嗚嗚)(手撓身上)(猖狂地笑)(再搶走一個香蕉)。
(二)表情包
新媒介時代,或者說,視覺文化時代的到來,讓語言和圖像這兩種表意符號得到更深層次的結合使用,文字表達的戲謔化使得表情包成為一種全新的交流手段和會意方式。借由“嗎嘍”表情包,人們可以無負擔地排解負面情緒,并在一定程度上從中獲取與其自身的社會經驗和生活體驗相關聯的特定快感[3]。“嗎嘍文學”的表情包圖像可以歸納為以下兩種表達形式:
1.純圖像型。無文字說明,單純使用“嗎嘍”的動物形象表達情感態度。如以身穿西服、手拎公文包的“嗎嘍”暗喻上班時的打工人,宣泄心中的郁悶與疲憊。
2.圖文雙構型。使用量最大,使用范圍最廣,含義最豐富,網絡熱度最高。如以“嗎嘍”身背巨大書包,一臉沮喪低頭扣手的形象,配上“嗎嘍不想讀書”的文字說明,幽默可愛,廣泛應用于學生群體之中。
(三)主題短視頻
短視頻作為我國互聯網文化的新生強力增長點,是指以移動智能終端為傳播載體,依托于移動社交平臺及社交鏈條,播放時長在數秒到數分鐘之間的視頻內容產品。短視頻創作者通過迅速模仿熱點話題或流行敘事,使作品在極短時間內迅速進入公共文化議程[4],是網絡流行語得到進一步傳播、接受和二次創作的互聯網媒介方式之一。
自“嗎嘍文學”流行以來,短視頻軟件出現大量“嗎嘍”換臉特效,短視頻制作者將不同“嗎嘍”圖像的雙眼和嘴巴替換為本人,進行事件敘述或才藝表演,依靠眼神和口型營造喜劇效果,多用于吐槽視頻和幽默搞笑視頻,增強了“嗎嘍文學”在實際應用層面的實用性、流暢性和代入感,對于情感宣泄和壓力代償具有顯著效果。
短視頻形式的“嗎嘍文學”相比于前兩種表現形式,創作成本和創作門檻都有所提升,但是短視頻擁有更強的情緒感染力和傳播力。通過“嗎嘍”短視頻臉部特效,創造者達成“異化面具下的前臺表演”[5],借助“面具”實現自由度更高、暴露風險更低的內在表達和情感抒發,為重塑自我媒介形象提供了規避負面評價風險的可能[6],進一步增強了“嗎嘍文學”的傳播力度,擴展了傳播范圍。
三、“嗎嘍文學”興起的社會心理機制
“嗎嘍文學”作為新興時代潮流和社會背景下的語用產物,是大眾文化對網絡信息進行有意識和無意識雙線并行篩選的結果。這一文化現象與青年群體心理健康、社會大眾思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一)個人焦慮的媒介映射與群體歸屬
伴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的普及,網絡空間已然成為“一種大型對話的開放性結構”,網絡憑借其特有的虛擬性建構了有別于現實世界的“第二空間”[7]。虛擬空間為個人提供了宣泄情緒、映射焦慮、書寫困境的媒介,近年來以“佛系躺平”“發瘋文學”“嗎嘍文學”為代表的網絡流行語,被認定為是觀測和審視當代青年社會心態和思想動態的重要窗口[8]。
學歷焦慮、就業焦慮、工資焦慮、健康焦慮……身處于社會全面發展時期背景下的青年群體焦慮層層疊加,越來越快的生活節奏與社會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人們不敢停歇的壓迫感與向后滑落的恐懼感[9]。
“嗎嘍形容我真是太形象了/既不像貓狗那樣可以靠外表混飯吃/又不像老鼠那樣真正的低三下四卑微活著/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幻想著自己也是齊天大圣那樣有通天的本領/就連佝僂的腰也能挺直三分。”
人們在壓抑與焦慮中繃緊神經,“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發瘋文學”和“嗎嘍文學”等網絡流行語應運而生,為心中郁憤急需疏解發泄的人們提供發泄通道和出口。不甘郁郁久居人下,但跨越階層、平步青云的困難程度在當今時代背景下遠勝于前,如何在有限的生存空間中爭取到足夠自身充實發展的社會資源,是當下青年群體不得不面臨的困境與難題。
作為當代青年群體以網絡平臺為媒介進行交流互動的重要手段之一,網絡流行語是青年群體滿足社交需求、獲取群體歸屬感的重要手段。石立春將網絡平臺空間內部的流行語大眾狂歡分為四個類別:弘揚主流價值觀的正能量狂歡、聚焦社會流行現象的個性張揚狂歡、注重緩解社會重壓的戲謔表達狂歡和聚焦于網絡公共事件的對抗敘事狂歡[8]。“嗎嘍文學”正是網絡空間聚焦于緩解社會壓力和精神重擔的戲謔式流行語表達的代表之一。
“生活,給嗎嘍整笑了”“出了社會,乾坤已定,你我皆是嗎嘍”,親切、幽默、易懂、口語化的文字表情包為“Z世代”青年搭建出一片屬于“小群體”的交流范圍,以趣緣為聯結紐帶構建成的群體以互聯網為媒介,強化圈層內部的共同信念[10],在庇護所中建立安全感。青年們經由“嗎嘍文學”聚集在一起,個人經過社會類化融入社會群體,實現自我的情感抒發、群體認同與社會歸屬。
(二)青年亞文化與“喪文化”的衍生物
《近三十年中國網絡青年亞文化變遷研究》[11]一文認為,網絡媒介文化反映主流社會正統思想觀念的文化潮流,而網絡亞文化則更多是以不同年齡、個性、職業、思想觀念、興趣愛好而聚集形成的群體文化,具有新潮性和獨特性。
“喪文化”是青年亞文化的一種全新形式,其以互聯網社交平臺為依托,主要在青年群體中流行傳播,以頹廢無力、壓力分享、間斷抵抗為特征,通過自嘲娛樂化的方式表達對現實壓力的不滿與無奈[12]。一度在互聯網平臺上短暫流行的“咸魚梗”“葛優躺”,包括“發瘋文學”和“嗎嘍文學”,都可以認定為“喪文化”的衍生物。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青年亞文化和“喪文化”常被認定為是青年的“自我污名”和“精神矮化”,其存在對社會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負面影響,部分被濫用歪曲的“喪文化”甚至存在偏離主流意識形態的風險。然而伴隨著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媒介對社會文化生態的全方位滲透,如今社會的整體文化向著開放、民主和多元的方向轉變,同時整體文化的存在形態也在朝著“數字化生存”轉向[13]。經過信息技術革命、傳媒手段的多元擴展、網絡文化的長期發展和網絡青年亞文化的規范治理,“喪文化”實現了從相對封閉的“小眾團體”向整體青年社會開放的“普泛化”轉向[13],其“被認定”的觀念核心從“徹底躺平時的情緒宣泄”轉變為“短暫休息時的自娛自樂”,“喪文化”的生產傳播目的逐漸轉向“變崇高為低俗,變莊嚴為幽默,從而達到釋放自我內心被壓抑的情緒”[14]。
從“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到如今的“嗎嘍文學”,唯一不變的內核是紓解苦悶緩解壓力,改變的卻是紓解苦悶過后的處世態度。盡管“嗎嘍”仍然不能變成齊天大圣,但“嗎嘍”依舊可以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努力堅持下去。“不可能只當一輩子嗎嘍,總有一天,我要站在花果山最高處。”新媒介的興盛為青年亞文化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新機遇,青年亞文化得以與主流意識形態接壤對話。“嗎嘍文學”作為青年亞文化的衍生和創新,將模仿并追隨主流文化的發展路徑,對青年群體心理健康和社會風潮產生積極的影響。
(三)精神退行下的本質回歸與自我安慰
弗洛伊德提出“退行”心理防御機制專業術語,即“復雜的觀念活動倒退為記憶痕跡的原始材料”[15],在經歷挫折、面臨緊急狀態、即將精神應激時,少部分人群將會短暫放棄已獲得的較為成熟的處世技巧和行為方式,退行到早期生活階段,使用更為原始、遠遠低于當前行動水平的方法來應對,以此對現實環境進行自我防御和主動逃避[16]。“嗎嘍文學”就是一種以網絡社交平臺為媒介、用于減輕自我焦慮、防范精神應激的心理防御機制。退行的過程僅僅體現在精神層面,時間短暫且具有可恢復性,并不會對個體在現實世界的行動產生消極影響。
相較于五官幼態、毛發旺盛的貓狗萌寵,“嗎嘍”并沒有那么引人憐惜,但是“嗎嘍”憑借人們對自我本質的探尋和精神回歸在動物表情包中占據一席之地。擁有與人高度相似生理形態結構的“嗎嘍”,或許就是全人類最原初的模樣,面對困難和壓力,它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不”,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平”,以風趣幽默的方式發泄頹喪與不滿,在話語狂歡中得到自我安慰和積極心理暗示,在心靈自洽中重拾前進的動力和勇氣,借助“嗎嘍”達成自我和解。
四、“嗎嘍文學”傳播邏輯
伴隨網絡社交平臺和亞文化圈層群組的發展壯大,互聯網作為“媒介”的功能逐漸得到挖掘和激發。
(一)語言模因(meme)的強勢復制與流行
模仿是青年群體通向社會化的重要途徑,而對網絡流行語的模仿與傳播即可視作當下青年主動融入社會語境的社會化嘗試[17]。模因(meme)一詞最初由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提出,“meme”(模因)由“gene”(基因)而來,是基因的文化對等物,是存儲于人腦中的信息單位和文化傳播單位,可以通過廣義上的模仿過程被復制、創新創造和傳播,“任何一種信息,只要能通過廣義性質的模仿過程被‘復制’,就是模因”[18]。
變動型強勢語言模因包括社會上某一特定時期流行的熱詞勁語,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流行的歌詞、廣告語、電影電視對白以及某一特定時期流行的話語篇章[19]。我們常說的網絡流行詞,大部分都是變動型強勢語言模因的一種。“嗎嘍文學”即屬于變動型強勢語言模因,其快速傳播和走紅,離不開語言模因的塑造和推動。“嗎嘍文學”在使用與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強勢的語言模因,以網絡平臺為復制傳播媒介,以文字、圖像、視頻為基本復制元素,得到規模更大且更加豐富的表現形式和話語模式。
(二)“二次詮釋”和語言收編
網絡語言的“二次詮釋”遵循語言符號意義的二度性原則,語言的淺層含義以表層符號為傳播依托,在使用過程中以字面意義得到顯示,這一過程可以被稱為“一次聯系”;但其深層含義需要在傳播過程中通過“二次聯系”獲得,字面意義從“此物”中抽離,指向抽象的“彼物”,“二次聯系”是對“一次聯系”之后獲得的意義的再一次延伸,是語言符號意義的二度符號化[20]。“嗎嘍”一詞的含義從字面上的“猴子”抽離,轉向泛指“疲憊社畜”的深層意義,同時被賦予復雜的情感色彩和精神力量,正是語言進行“二次詮釋”的結果。
網絡流行語的傳播途徑大致可以概括為“網絡空間—網民效仿—網絡語言收編”三個環節[20],即可以理解為互聯網平臺的內部傳播—語言模因的復制傳播—網絡流行語的降格收留或改編的過程。“嗎嘍文學”的發展傳播路徑則選擇“改編”方向,表情包、文段語料、短視頻等多種表現形式的出現,維持了“嗎嘍文學”在網絡流行語中的熱度,形成了大眾文化社會化的擴散和傳播。“嗎嘍文學”體現的“出現→效仿→復制→二次詮釋→語言改編”傳播機制,正是大部分網絡語言得以廣泛傳播和流行的路徑范本,具有深刻的觀察價值和研究意義。
五、結語
“嗎嘍文學”是大眾文化在當前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產物。經由個人情緒的媒介映射、語言模因的強勢復制和網絡平臺內部的話語狂歡,“Z世代”青年群體通過適度、有分寸的“嗎嘍文學”,在互聯網內部實現個人的情感抒發和群體認同,緩解現實生活中的負面情緒,實現自我安慰和能量積蓄。普通平凡的“嗎嘍”勇于自嘲、樂于自嘲,在戲謔幽默中進行積極的心理暗示、精神自洽和天性釋放。“嗎嘍文學”作為青年亞文化的衍生和追隨主流文化的創新品,對于青年群體適應現代生活有著積極的文化意義與傳播價值。與此同時,“嗎嘍文學”作為青年亞文化的衍生物之一,將在廣泛的傳播使用中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消極、反叛的“脫軌”文化傾向,因此需要對其文化內涵進行批判性反思和理性分析,對其存在價值、傳播邏輯、流行因素和方向把控作進一步深層探究和思考。
參考文獻:
[1]王小盾.漢藏語猴祖神話的譜系[J].中國社會科學,1997(6):146-167.
[2]沈天健.“發瘋文學”的文化批判[J].新媒體研究,2023(3):107-111.
[3]鄭滿寧.網絡表情包的流行與話語空間的轉向[J].編輯之友,2016(8):42-46.
[4]常江,田浩.迷因理論視域下的短視頻文化:基于抖音的個案研究[J].新聞與寫作,2018(12):32-39.
[5]胡一葦.網絡自嘲文化下青年群體的自我呈現:以B站“檸檬頭”系列視頻為例[J].聲屏世界,2022(19):99-101.
[6]李冬琪.迷因理論視域下抖音臉部特效短視頻的傳播研究[J].西部廣播電視,2023(15):63-65.
[7]王薇.狂歡理論視域下的網絡表情包研究[D].廣州:暨南大學,2017.
[8]石立春.流行語呈現的青年網絡狂歡及潛藏的思想動向研究:基于《咬文嚼字》雜志十大流行語(2009—2018年)的內容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19(12):54-59.
[9]吳寧,孔靜漪.社會加速背景下青年的生存焦慮與消解路徑:基于羅薩的社會加速理論[J].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24(1):39-45.
[10]劉美憶.Z世代媒介使用的自我表達與群體認同:以B站為例[J].青年記者,2021(17):57-58.
[11]陳賽金.近三十年中國網絡青年亞文化變遷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23(3):83-89,99.
[12]龐雨晨.亞文化視角下90后“喪文化”的風格及其意義:基于社會學的調查與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18.
[13]馬中紅.新媒介與青年亞文化轉向[J].文藝研究,2010(12):104-112.
[14]蕭子揚,葉錦濤,馬恩澤.我國網絡青年“喪文化”的研究進展:一個文獻綜述[J].北京青年研究,2019(1):53-60.
[15]弗洛伊德.夢的解析[M].劉連景,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272.
[16]張建梅,李宏翰.大學生的角色退行與心理健康[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6(2):235-237.
[17]韓敏,盧松巖.回到中國文化的對抗認同:網絡流行語“躺平”的話語脫逸與共識反哺[J].當代青年研究,2023(5):22-33.
[18]張國燕.語言模因論視域下網絡流行語的傳播機制研究[J].品位·經典,2022(21):31-33.
[19]何自然.流行語流行的模因論解讀[J].山東外語教學,2014(2):8-13.
[20]黃碧云.網絡流行語傳播機制研究[D].廣州:暨南大學,2011.
作者簡介:王嘉露(2004—),女,漢族,陜西西安人,單位為西北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網絡文學與大眾文化。
(責任編輯: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