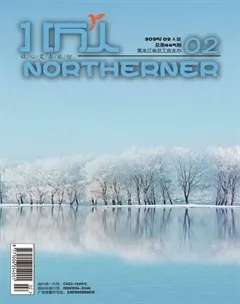用戶需要改變嗎

那天,我去北京出差,晚上在酒店里見到了一些創(chuàng)業(yè)者朋友,聊了聊大家遇到的困難。2024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困難很多,但其中的兩個問題讓我印象深刻。
第一位朋友說,今天的電商實在是太發(fā)達(dá)了,擠占了太多實體經(jīng)濟的空間。潤總,你能不能呼吁大家克制克制,減少網(wǎng)購,讓實體經(jīng)濟喘口氣。另一位媒體朋友說,很多企業(yè)遇到經(jīng)濟困難,首先砍掉的就是廣告預(yù)算。潤總,你能不能呼吁呼吁大家,就算面對困難,也還是要保住品牌預(yù)算。
我特別理解他們的處境,因為我們今年也遭遇到了類似的問題。但這兩個愿望,我真的做不到,它們只是美好的“愿望”。
在技術(shù)變革時降低交易成本,在環(huán)境變化時追求短期效果,這都是人性的、商業(yè)的邏輯。前兩天,也有一位企業(yè)家這樣總結(jié)自己企業(yè)面臨的問題:因為行業(yè)內(nèi)卷,所以我們的利潤下滑嚴(yán)重。我說,如果你把利潤下滑歸因于“行業(yè)內(nèi)卷”,那你永遠(yuǎn)都不可能改變,因為這是外部因素,而你不可能控制外部因素,難道你能去呼吁大家,停一停,不要內(nèi)卷了嗎?
什么是向內(nèi)歸因?因為我們的產(chǎn)品沒有壁壘,在激烈的競爭下不再稀缺,所以利潤下滑嚴(yán)重。只有這樣,你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思路:要么建立壁壘,要么創(chuàng)造稀缺。所以,永遠(yuǎn)不要去“呼吁”什么,而要理解什么是大勢所趨,改變自己。
類似的邏輯,還發(fā)生在另一個我們經(jīng)常聽到的詞身上——用戶教育。去年5月,我來到廣州參加一個心理學(xué)論壇,和許多心理學(xué)專家一起討論,收獲非常大。那一天,我似乎突然對“用戶教育”這個詞有了新的理解。用戶教育這件事存在嗎?或許存在。但假如你多年如一日,向消費者反復(fù)宣傳,他們卻還是不需要,你的想法會怎樣?如果你依舊認(rèn)為,我不服,我要繼續(xù)教育你,終有一天你會需要。那就不是努力了,而是一廂情愿。
但凡一個產(chǎn)品需要“教育市場”,那就說明用戶并不需要。就拿心理咨詢舉個例子,這個行業(yè)在國內(nèi)的發(fā)展一直有很大阻礙。心理咨詢的基本形式是一個封閉的房間,一個心理咨詢師坐在椅子上,然后客人坐在他的對面,兩個人對聊。很多中國人對這種形式非常抗拒。有人說,這是因為這個行業(yè)還不成熟,需要市場教育。為什么中國人這么難以接受呢?其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這種形式太像“看病”,很多人會給自己一種強烈的暗示:我又沒有問題,為什么要去看病?他甚至?xí)谶M(jìn)門前用口罩和墨鏡把自己包裹得嚴(yán)嚴(yán)實實,就是怕被別人認(rèn)為“心理有病”。
雖然心理咨詢這個行業(yè)做了大量的用戶教育工作,但如果一個行業(yè)要讓用戶在進(jìn)門時承擔(dān)如此大的心理負(fù)擔(dān),我覺得這無論如何都是難以推進(jìn)的。
但為什么這種模式在歐美就沒有阻礙呢?我在論壇上看到一個觀點,說因為歐美本就是基督教文化圈,大家從小就有去教堂對著神父懺悔的習(xí)慣,這種模式天然就是兩個人在小房間里對聊,整個過程非常自然。而起源于歐美的心理咨詢,本質(zhì)就是在這種心靈對聊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但中國人根本沒有這個習(xí)俗,非常難接受在一個小房間里對陌生人傾訴。這是不同的文化導(dǎo)致的,你非要教育他另一個文化的習(xí)俗,那就是在逆人性而為。聽到這個邏輯的那一刻,我真的是醍醐灌頂。
那該怎么辦呢?我作為心理學(xué)外行,當(dāng)然沒法提出什么具體的思路,但隨便瞎說幾句的話,或許解決方案也在“形式”。有沒有可能,帶你的客人去吃頓火鍋、吃頓小龍蝦,邊吃邊聊呢?如果兩個人都是女生,有沒有可能像閨密逛街一樣,邊逛邊聊呢?你看,聊的內(nèi)容完全可以建立在科學(xué)的心理學(xué)理論上,只不過聊的形式換成了中國人更容易接受的形式。當(dāng)然,我得再次強調(diào),作為外行,我這完全是天馬行空,沒有參考價值。
我只是想說,如果你發(fā)現(xiàn)你的產(chǎn)品一直需要大量的“用戶教育”,那一定不是用戶的問題,而是你的問題。
(摘自微信公眾號“劉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