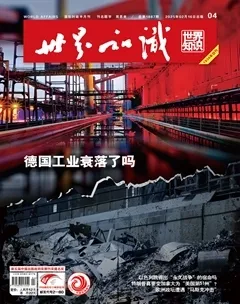推動中日成為新時代的經貿合作伙伴

2024年11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利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見日本首相石破茂。12月25日,日本外相巖屋毅應邀訪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與其舉行外長會談并共同出席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中日關系出現改善勢頭,在近期的中日高層互動中,中日經貿合作的話題正在得到更多關注和新的期待。
經貿合作是否還是壓艙石
近幾年,中日經貿關系出現了三點變化。一是雙邊貿易額下降。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43.85萬億元,同比增長5%,中國與東盟、歐盟、美國、韓國等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額均實現增長,而中日貿易額為2.2萬億元,同比下滑2%,被中韓貿易額反超。二是日本對華投資收窄。2019~2023年,中國累積實際使用日資在累積實際使用外資中的占比從5.1%下降至4.6%,日本被新加坡超越,排名降至第四。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4年度《海外日資企業實況調查》顯示,未來一至兩年希望擴大在華投資規模的日企比例為21.7%,繼2023年首次跌破30%后,2024年數據為2007年可對比以來的最低。三是經貿合作結構隱現松動。長期以來,日本對華投資偏重制造業,但近五年呈下降趨勢,制造業投資占比從2019年的65.4%降至2023年的63%。非制造業投資持續增長,占比從2019年的34.6%增至2023年的37%,日企批發零售業對華直接投資占比更是從2018年的8%提高至2023年的22%。
但是,中日經貿合作的基本面沒有被撼動。貿易方面,2024年日本滑落為中國第五大貿易伙伴,但與第四大貿易伙伴韓國的貿易額2.33萬億元相比,僅差0.13萬億元。中國不僅自2007年以來保持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地位,還是日本的最大進口來源國,根據日本2024年版《通商白皮書》,日本進口的1406個品類商品中,超一半進口額來自中國。投資方面,雖然日企增資中國的意愿有所下降,但大多數在華日企具有投資黏性,有意愿撤出中國的日企比例極低。此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中日兩國構建了一個高水平的自貿合作機制,RCEP的關稅減免、通關簡化等政策紅利降低了企業的進口成本,為中日經貿合作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
事出有因,動因復雜
一方面,通過上述三點變化可以看出,中日經貿合作的推進遭遇一些挑戰,面臨著逆水行舟的風險。這些變化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有非經濟因素和外部環境的影響。
第一,制造業向產業鏈上游攀升,中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顯著增強。這一變化使得包括日企在內的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營和銷售面臨更激烈的競爭。特別是日本傳統優勢產業——汽車產業在新能源轉型中表現不佳,競爭力逐漸下降,這成為中日貿易額下滑以及日本對華投資減緩的重要誘因之一。第二,兩國經貿關系受非經濟因素干擾。近年來,日本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經濟安保法”)及相關政策,搞“經濟政治化”“經濟安全化”,實施出口管制措施,人為筑起技術壁壘,嚴重阻礙中日經貿伙伴關系的提質升級,也導致日本企業在華投資意愿下降。例如,中國對日本的半導體制造設備和材料有較大需求,但在日本目前的政策法治環境下,中日間該領域合作開展無法深化和擴大。第三,美國推進“印太戰略”,構建多圈層“小圈子”,試圖在多個領域對中國進行戰略遏制。日本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被美國視為對華競爭“力量倍增器”,美日同盟的強化以及得到美國支持的日本國家安全戰略調整不利于中日關系改善,也對中日經貿合作推進帶來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兩國做出改善關系的表態和推進合作的動作,來自基本面的支撐和窗口期的加持。第一,中日經濟利益和產業鏈供應鏈已深度交融。中日在傳統制造業領域合作基礎好、互嵌深入,電子、金融、物流等領域不斷拓展。日本在高端機械制造和技術研發、企業投產比管理等方面仍將具有優勢,而中國生產的消費品具有競爭力,同時在應用場景和商業模式創新方面表現出色,中日經貿伙伴關系具有內生動力。第二,石破茂對華態度相對務實。自2024年底以來,他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希望盡早訪華的意愿,強調中日關系的穩定對兩國和地區的重要性,認為中日經濟合作潛力巨大。此外,特朗普一直秉持“美國優先”原則,奉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其再次執政可能給全球經濟和美國盟伴關系帶來沖擊,這促使日本政府傾向于與中國加強溝通,希望通過改善對華關系、加強與中國溝通合作來對沖風險,并為自身經濟復蘇營造更大空間。
中日應攜手“五新”
基于對“面”和“變”的分析可見,中日經貿合作“大干快上”難度不小,但也不會“脫鉤斷鏈”,這將成為一種新常態。中日經貿合作正在步入發展機遇期,而石破茂內閣穩不穩、特朗普怎么“出牌”,都會對機遇期產生影響。既然中日兩國都認為經貿合作符合自身利益,那么就更需要抓住機遇期、塑造機遇期、相向而行。
一是找準新坐標定位。認識到時空和國際方位的變化,覺察到中國是自變量而非因變量,找準中日在“東”“西”“南” “北”國際格局中的位置和分量,探索契合新時代的不同意識形態兩強鄰國間相處新模式。二是明確新思路相處。優勢互補共同培育新質生產力、開拓新市場。在第三方市場合作中盡量降低干擾,率先多開展中小企業間合作和“中日+”多領域合作。三是開辟新領域共贏。主動塑造中日投資伙伴關系,保持制造業合作同時,挖掘金融、康養、新零售和綠色、藍色等產業增長潛力。四是涵養新動能蓄力。在中日關系改善發展的關鍵時期著力涵養合作根基,抓緊落實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達成的十項重要共識,并推動科技合作盡可能向更廣泛、更深入、更前沿領域延伸。五是樹立新范本彰顯。以中日契合新時代要求的經貿合作伙伴關系來釋放穩定預期,彰顯兩強如何平衡發展與安全,實現和平共處、互利共贏。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涉外法治與安全研究所〈原海洋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