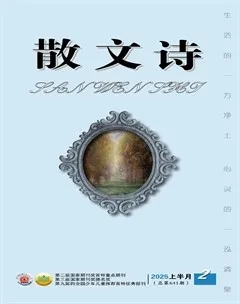“凝視”之道
一 “千萬要凝視”——為散文詩一辯
在散文詩集《凝視》的開篇自序中,周慶榮申言:“千萬要凝視。”(《凝視》)隨后,“凝視”——不只作為一種元素,更作為一種結構——貫穿了整部作品。顯然,“凝視”并不只是為了呼應特定主題,更是為了表明一種寫作方法,甚至,是為了展露一種辯護的勇氣和雄心。
散文詩的合法性和美學性問題歷來備受疑慮。詩人西渡曾從詩和散文作為兩種思維方式的區別出發,指出“詩以感性、直覺的方式感受、領悟世界,散文則以知性的方式觀察、思考和認識世界”;進一步地,他以散文作為參照系指出詩具有“未來性”和“完全性”。所謂“未來性”,即是指詩所處理的世界是未成的、可能的,詩創造世界;至于“完全性”,即是指詩以直覺、隱喻、象征的方式領悟世界的本質和整體,一首詩因而自成一個宇宙。基于如上理論辨析,西渡結論道:散文詩從性質規定上說是詩的,而不是散文的;它是詩的內容和散文形式的結合,而不是散文的內容和詩的形式的結合。周慶榮無疑會贊同西渡的論述,于他而言,散文詩絕非具有詩性的散文,而是以散文形式呈現的詩;鑒乎此,周慶榮才坦言,自己的寫作是為了詩意地呈現事物之“本質”,并發揮散文詩的“預言性”優勢。
統觀整部《凝視》,其中充滿了博觀與精微、體悟與思辨,既有對世界萬象的統攝,也有對主體身份的觀照。在“凝視”行動中,寫作者自由穿梭于物象之間,拽拉語詞的引線,拔除意識的界樁,拆解世界的封印,這很容易讓人想起一百年前郭沫若的主張:“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專挹詩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客觀而言,周慶榮所謂的“凝視”不再是一個被規定的詩歌動作,而是一連串相互激勵的詩學動機;正是在“破除”的自由意志與“自然”的決定論之間,“凝視”才作為一種“欲望”呈現出了強悍的命名活力和指認效力。
當周慶榮開篇寫下“千萬要凝視”時,他已然暗中許下了為散文詩一辯的承諾。“千萬要凝視”既是敦請,也是告誡,它以主體宣言的形式對散文詩做出了性質判斷。顯然,散文詩并非詩的稀釋或降格,而恰好是詩的波動和擴張——歸根結底,散文詩是詩之“自由”的擴大化;這里的“自由”既關乎主題和風格,更牽涉主體精神。正是在這里,我們方能看到“詩”這一活動無盡的生產性,也才能以“同情之理解”(一個決定性的顛倒)重思施蟄存不無驚人的論斷:“從《現代》以來的中國新詩,可以認為都是散文詩。”
是的,關鍵在于如何回溯散文詩的發生并體諒其在現代性寫作罅隙中的曲折。在此意義上,周慶榮的寫作既是對散文詩傳統的接續,亦是對散文詩傳統的改造。依周慶榮之見,散文詩是“更加復雜和隱秘的詩”,勉附以“散文”之飾者,不過是轉喻之鋪陳、思想之媒介——恰好是在此一關卡,散文詩涵攝著世界并召喚著自身,一切皆可成詩,一切尚未成詩。
二 “大地上每一處細節”——凝視與凝思
人類天然處在過去和未來兩種永恒之間,這一特殊處境迫使人類反復探求自身的位置和方向。周慶榮所提供的探求之路既非先知或哲學家式的,也非信仰或科學家式的,而是經驗和文學家式的—— 一種力圖從“此在”出發獨自通達世界的詩寫方案。大致看來,這一方案總是起始于一種笛卡爾式的懷疑,并收束于一種禪宗般的醒悟。
先看懷疑——
“太陽向下和它正在升起,這是否是最本質的區別?”(《黃昏路》)
“是否只要高風亮節就可以不介意自屬之物?”(《自屬之物》)
“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思考純潔所需要的條件?”(《與污泥說》)
“叢林的法則是否可以無效?”(《與叢林說》)
顯然,這里的懷疑超出了美學經驗主義的范疇,它既指向自我道德律令也指向他者審美觀念,它既關乎叢林法則也關乎天文規律;它是一種讓萬物陌生化的懷疑,一種將全世界都視作異鄉才可能帶來的懷疑。正是懷疑帶來了認知的根本性轉捩——“不再簡單地把自己看到的稱為外部世界。……看清楚大地上每一處細節。”(《目光》)
再看醒悟——
“破土而出的覺醒,我們沒有辦法拒絕。”(《沉睡中的一根刺》)
“這蒼茫的人世,你一定不能以為只有自己醒著”(《對話錄》)
“星星睡著了,民生醒著。”(《雪夜》)
“這沉睡的靜物,也會是醒者的對比和參照。”(《靜物》)
“是根,率先覺醒。”(《根》)
“醒來,發覺是夢。”(《搖櫓,夢里出海》)
“出世是入夢,入世是夢醒。”(《錯覺現象》)
“我會從戲中醒來。”(《古戲》)
就美學效果而言,這些句子儼然以論斷性的方式呈示著一種東方式的新知,它們蘊含著一種致力于“發現”而非“發明”的求新意志;不妨說,支撐周慶榮散文詩的內在精神就是一種禪宗式的醒悟。問題在于,懷疑這一動力機制與醒悟這一美學精神之間存在天塹鴻溝,周慶榮是如何完成這驚險一躍的呢?答案是:凝視與凝思。
周慶榮對萬物的“凝視”行動并非全景式監獄控制者那般雄性的、不對稱的、無形的監視,而是涉世嬰童那般中性的、平等的、有情的關切;他不是冰冷地觀察世界,而是經由語詞與萬物親密地推搡、親切地交談,以求贏獲超出意外的思辨。在詩寫層面,這種凝視和凝思體現為一系列具體而微的格物過程——
“我目睹了兩塊云在天空追尾。/稍后傳來的聲音由尖銳到沉悶。”(《目睹》)
“從生長的方式看待生命,最慢的速度也好于坐以待斃。”(《蝸牛》)
“明天,在時間之外。”(《時間里》)
“苔痕仿佛一種古典,人們期待著一次鮮活的鋒利。”(《陳舊》)
請注意:觀“云”過程中的視聽聯動,經由“蝸牛”被勾連的快慢辯證,以“明天”為契機對時間所進行的指認,以“苔痕”為緣起對新生所進行的思考,無一不是為了入乎其內并出乎其外。顯然,凝視和凝思的方法不再停留于描述事物的表面,而是沉浸于事物并探測其中隱藏的辯證機制和寓言意味;一方面,凝視過程不停地為凝思積蓄著力量,另一方面,凝思過程也不斷地向凝視釋放著活力。
正因于此,我們才一面看到周慶榮的筆觸隨性指點著萬千物象,如“羊”“馬”“牦牛”“燕子”“蜜蜂”“彩蝶”“蝸牛”“鷹”等動物,“銀杏”“松樹”“蘑菇”“櫻桃樹”“油菜花”等植物,“風”“云”“雪”“星”“河床”“土地”“海水”等自然物,乃至于“篝火”“隧道”“風箏”等人造物,另一面又不得不跟隨他重新經驗一遍世界,譬如,他言“隧道”卻及“愛”,談“風箏”又及“理想主義”,觀“河床”則逼視“生命”,看“海水”則領悟“堅硬”……比興旁通之術,不一而足。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言:“如今我們更需要與世界、宇宙、事物、森林、田野、山脈、海洋重新建立聯系,就像我們與所愛的人和藝術作品更需要重新建立聯系一樣。”無疑,這種與萬物重新建立聯系的過程對周慶榮而言,便是世界的可能性被重新打開的過程,也是語詞被重新擦亮的過程。
三 “我要驅逐的是我自己”——從“格物”到“誠意”
在代后記中,周慶榮以“格物、及物和化物”來總結自己的散文詩觀——
所謂格物,是指我們如何從所接觸到的事物中獲得自己所需要,同時也對他者有意義的啟示;及物,要求我們的寫作必須在場,必須食人間煙火,必須能夠讓我們的寫作去喚醒更多沉睡的經驗;化物,要始終清醒寫作主體本身的情感和知性的轉換貫通,不拘泥于典和任何已有的出處。
這種以物觀“我”、以“我”化物的格物過程不僅推動了修辭策略的展開,更標記著主體認同的生成。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凝視者的“我”,總能在對他者的觀察中將“我”打撈出來——“當田野之外的明星們在社會中熱鬧的時候,我做一根獨立的骨頭。”(《追星者》)不僅如此,這種凝視還會推動自我反思的發生,并生成自我驅離的自覺——“我要驅逐的是我自己?”(《驅逐》)事實上,“他者”被納入考察視域,恰好是因為“自我”面臨“匱乏”,主體的匱乏要求主體以自我否決為形式來實現自我填充。
如前所述,周慶榮踐行的“凝視”方案是一種平等的、有情的關切活動,而非等級化的、無形的監視行為;這意味著,“凝視”的背后是主體的省思性活動而非介入性意志。“凝視”的非支配性伴隨著“凝思”的反身性,這導致了主體位面的兩層變化:首先,“凝視”行動被扭轉成了一種“自我凝視”(self-gaze),正是在自我觀察與審視中,“我”與萬物之間達成了“互為主體性”(mutual subjectivity)的共構共生狀態;其次,“凝視”有待于從格物活動躍升為一種誠意行為。
在程朱理學的格物傳統中,存在一個以“致知”為目標的普遍性誤區,這一誤區的致命之處便在于它遺忘了“格物”的根本目的在于“誠意”,“致知”只不過是一個橋梁。正所謂“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禮記·大學》),唯有以“誠意”為終極目標的格物行動才不會止步于“致知”;或許正是明見于此,王陽明才會繞過程朱理學的“致知”傳統,另辟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蹊徑。所謂“誠意”,也便是“良知”,便是因良知而來的關切行動。這一點同樣見諸周慶榮的散文詩——
“我要擁抱黎明,去熱愛我能夠看得清楚的——/人間萬物。”(《啟明星》)
“我思考著如何合格地做好一名觀眾。耐心和讓人疼痛地對另外生命的尊重,以及永遠不能覺得眼前的事情都與自己無關,它們是觀眾須知?”(《觀眾》)
如果“凝視”對應著格物,那么“凝思”便意味著“誠意”。“‘理’如果發揮作用,書里的文字,是精神的光,更是夜空中的群星。”(《“理”的作用》)對周慶榮而言,“理”并非只在于“致知”,更關乎“誠意”;所謂“誠意”,并非見到外在的光,而是見到內在的光。唯有見到自己內部的光,才會致良知,才會奉獻,才會重生——
“每當生活中需要光,我就自燃。”(《燭語》)
“我以向下的方式繼續活著,如果再次向上,我會從一株幼苗重新活過。”(《樹樁獨語》)
這樣的主體性無疑是一個“嘈雜的”主體形象,他凝視他者以填充自身,他驅逐自身以關切他者;仿佛“我”與世界處于無盡的相互干擾過程之中。然而并非如此。透視法教給我們這樣一個常識:對象物的所有水平線如果向空間中無限延伸,就會在某一消失點上會合。我想強調的是,周慶榮這里呈現的并非美術上的透視法,而是精神上的透視法;與其說,這意味著,一切所見、所聽、所聞、所嘗、所感、所思皆匯集于“我”這一點——神奇之處在于,“我”這一點位總是一個傾向于消失的點位,它只在對象之物的統合匯集過程中浮現;毋寧說,“我”以自身的消失和重生為前提,促成了世界的對象化。
根本上來看,正是因為“格物、及物與化物”的方法論背后有一個明晰的欲望主體,它才會意識到“唯美、抒情和密集修辭”本身便是一種語詞戀物癖的露出,進而強調散文詩寫作中的“思想性”。與此同時,“針砭、悲憫、熱愛與希望”作為“思想性”的要件,不僅提示著欲望的生成過程,也標記著欲望消弭的過程;這種辯證性的認同之所以能夠生成,并非只憑靠主體的主觀內省,也援恃于悠悠天地這一中國式的文化背景。就此而言,周慶榮的散文詩儼然是一種從西方現代性視域中回望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的寫作者才能提供的原創性書寫方案——這里的原創性是一種思維方式上的原創性而非技法風格上的原創性,是一種土壤般的原創性而非種子式的原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