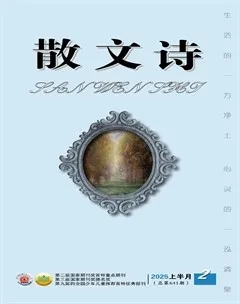北疆長河
落日下的新開河
我是從它掌心里出走的孩子。
小村的燈火,順著土路追隨背影趟河而過。
母親的割草聲與流水唱和:孩子,你看那落日,依舊從下游升起,去上游歸巢。
孩子,什么樣的路啊這么長,走了這么久還沒有走回去。
孩子啊,什么樣的流水這么長,流淌了這么多年,眼眸中的波浪未曾干涸。
與駿馬對話——打馬而過的獵手,把自己的余生闖進牧場,偶爾闖入村莊的煙火中,舀走一夜新開河的故事,可入藥,亦可入茶。
我至今也叫不出他的名字。
只覺得他像一枚落葉,順著河水緩緩流走。
與鏵片對話——天南地北的行者,關里關外的豪客,逃荒的、落草的、退隱江湖的,用老河的一行淚痕洗去風塵,安身于鏵片的撫慰,于荒原上耕種煙火。
有傷,就讓新開河的水聲洗一洗。有淚,就讓塞北的風吹干。
與網對話——九叔打過的魚,比他講過的妖魔鬼怪還要鮮活,至今還在記憶里蹦來跳去,跳入茫茫月色里,消失不見。
我曾像他們那樣在河邊小坐。
落日落得很慢,慢得你以為它不會落下。
空河道
以另一個身世變回自己。
它累了,只是拐了個彎,就睡在草原和大漠的懷抱中。
埋伏于漩渦曾埋伏的地方,黑夜在它的注視下慢慢褪去。
等一場大雪返鄉,像一張臉龐回到天空,照耀所有漂泊的空曠,默默等待空空的河道漲潮。
曾親眼目睹遠行者,它們的音訊我絕口不提:要么隱姓埋名,要么遠走他鄉,留下來的都成了彼此的兄弟。你能守住這必經之路嗎?與它長相廝守,對峙中走完一生的跋涉。
老馬懷念的水流,將鞭影的忐忑拖走:越是接近人間煙火,越是覺得厭倦了烽火和號角聲。
再窄的河道,也能跑開它未完成的野性。當年的水也才沒過小腿,恍惚間淹沒了時空,不知要把故事的源頭拖向哪里。
你要相信兩棵草之間,一定藏著奔騰的秘密。
你要相信多么空的河道之上,都有一滴水的身世緩緩流淌。
現在,空空的河道橫在面前,像一個手勢攔住去路:開過刃的裂痕,等很久了,你踏過的堤岸又矮了許多。
舍不得放棄,它把自己騰空。
想象過無數次歸來時刻,臥于背風處猜測結局。
那幾只蹄印子,化作魚兒逃走了嗎?
——都關在一滴水的眼眶里,不信,你就喊一聲它們的小名。
水被水拖走,馬蹄子摁不住漂泊的天空。
燃燒的河
那么多英雄或草民的風骨,緊緊抓住西遼河的諾言,也抓住故人的音訊。
弦月壓彎河水,也壓彎船影和背影,講述一把生銹的鎖,怎樣完成它的遼闊。
小心翼翼,跌落塵埃的可能是飛翔。
流水在它的手掌中,翻閱斑駁的傳說,誰家的女兒出嫁,誰家的小子把心上人娶回了家。
你的心動時刻,為他們的所愛筑巢。
他們的恩怨,為你打開心頭枷鎖。
而它只是遙望這些人間煙火,眼眶中流出眷戀的晨光和暮色。
回一回頭,失蹤已久的部落撲面而來:磨刀打獵,生火做飯,他們與你偶遇的瞬間欲言又止。
水落水漲。一條河流丈量春秋的寂寞,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習慣煙火中的光陰丈量喜悅和哭泣:拈起一片月色,蘸著人間風塵,所有心事都能不治而愈。
以聚落為界,鎮守前世的諾言和來世的約定,哪怕斷骨泛白,只要貼近泥土就不害怕。
而今世,我縫縫補補的面容依然在山水間等你。
等你拖著千山萬水的音訊,等你背負半生的明月和天涯來與我對視。
那個瞬間,就像把聽過的曲子再聽一次,前世的身影,再擁入懷中。將一切雜念都聚攏在大地的腹部,羊皮鼓響起,它就隨之燃燒。
英雄之獵
燃起。
開過刃的石頭是老不死的。
一個個神話,才會在火焰中涅槃。一座座江山,才會在火焰中重生。
你心頭之火,必然會點燃更多的報國心,千年,再千年,直到化作大河東去,刀劍笑,美人吟。
畫卷上,山河大美,自然是一曲聽罷,再彈一曲。
這么大的河山,必然要用我轉世的年華行走,大地上,聚落會告訴你斗轉星移,親手種下不老的夢,我要用三千次輪回與你遇見。
火一樣的親情,就是等待相認的。
一粒粒沙子替你死守疼痛的記憶。從出生的那一刻,就成了史書上的一顆丹心。
鐵甲也好。
羅裳也罷!
無非都是你在同一闋辭中掙扎的方式。刀光劍影,誰懂我的心呢?
邊關之月,老夫做夢。
誰知我來人間行走一回,要講述的是誰的前生:“某一天,我們都走不動了,就靠在自己的墓碑上,臨摹彼此的來生。”
走不動了,就像一曲流水彈不動了,優雅地在一塊石頭上老去,你必然還會念念不忘我的絕世容顏,在一闋詞中不老。
你必然不會猜中,我早已躲進說書人的袖子里,替他掐算一座又一座江山的風骨。
取火的人,鎮守河山的人,耕種的人,讀書的人,征戰沙場的人,都是英雄。他們都在這片大地上按下手印——
我們用同樣的動詞,來做科爾沁的韻腳。
被火燒過的石頭,曾是某人遲緩的告白。
石頭里的江山
一塊塊石頭被刀斧或鑿子喚醒,只有它們,才能讀懂一顆石頭心。
向山體追問時空,什么人在崖下義結金蘭,什么人在沙場上同生共死,什么人在馬放南山后,歸隱到石頭中去。
你還記得它的宿命嗎?
一幅幅巖畫會告訴你。
曾是英雄手中利刃,曾是戰馬的一記嘶鳴,曾是一條河流的千載胎記,也曾是鎮守山巒的一塊傲骨。
現在,它苦守靈魂深處的余溫:快來我的身上雕刻平仄,雕刻出不一樣的時光,喚醒紅塵的飄逸,古道的雄壯。
開一朵花吧!
聽一塊石頭的哭或者笑,聽一個手藝人和一塊一塊石頭推杯換盞。
醉了。石頭的臉龐會說話。
醉了。石頭的裂痕會唱歌。
它的辭典里有三千弱水,卻只取一瓢飲下,飲下五千年金戈鐵馬,飲下幾生幾世輪回繁華:哥哥,我還在一塊石頭上等你啊,等你輕喚我的小名,等你為我弄斷琵琶。
你說春暖花開了,你就來看我,看我轉世為一小塊石頭上的一曲小令,輕輕地彈啊,輕輕地唱。
石頭稱王。
它們在大地上書寫手諭,彈指間竟已過了千年。
一幅長卷,雕出人間大美。一寸河山,包羅萬種答案。
你就一刀一刀,刻出花開正好;你就一刀一刀,刻出光陰苦寒。
請記住那些失蹤者,習慣于置身事外,對你身處的局,看破而不會說破。
哈民的根系
就從一條河流說起。
它有著鋒刃般的光芒,也有蒼狼的野性。
它的光芒,鋒利無比,切割亙古深邃的歌謠。
水和流動的沙,發生了好多故事,思念把它們一一拖上堤岸:那是一個個古村的胎記啊,印在一滴滴水的顫音里。
一個聚落,就是一滴筆墨:我寫下的文章,只等一個人來讀,我讀過的磚石,只等一個人來愛。
每一個胸懷天下的人,最后都會向這片江山交出自己。
遺址上,鑿刻著羸弱的靈魂,可就是這斷斷續續的樂章,彈奏的都是他們或怒發沖冠,或擊壤而歌,或在一部史書里終老的千古絕唱。
沙子下面漲潮,終會重見天日。
誦讀他們的風骨。
是西江月,是水調歌頭,是大江東去,也是牧羊女在河邊垂釣心頭的夢境。
千年一嘆,知我者,一片山水的濃濃鄉音;等我者,是幾世輪回,誰的背影。
碑文上,雕刻著千年的厚重與輝煌。
遺址上,承載著千年的風雨和滄桑。
你聽,枯木獨坐,它指一指蒼天,試圖喚醒云朵——
那是如瓷器開片般疼痛的名字,輕輕一嘆,便又有一夜故鄉,杳無音信。
鐘聲,一槌一槌落淚,心疼每一個地名的輪回和脫胎換骨。
如果一個老僧的坐化,能換回一個鮮活的名字,那么,就讓我去他的經文中剃度吧。
每一粒種子,都喂養著哈民遺址里的蛙鳴和月亮那么大的饑餓。直到聽見它“哇”地一聲,喊出迷失在夜空的乳名,我們才能在這部書簡上一粒一粒找回自己。
它們都是被摁在泥土里的種子,一筆寫出一槌鐘聲。
我們老了,骨殖不老。
一筆寫出一個名字,我們曾在天涯錯過,也在這里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