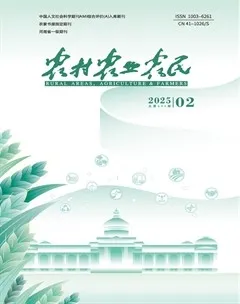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權利主體權力界定和權利關系研究



摘 要:以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權利主體權力界定和權利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回顧了中國土地經(jīng)營制度變遷的若干階段,分析了農村土地的權力結構,揭示了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的權利關系及配置缺陷。需要明確集體經(jīng)濟組織在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中的核心主導地位,合理劃定集體所有權與農戶承包權的財產性收益比例,明晰土地流轉中各經(jīng)營主體的權利和義務,規(guī)范集體經(jīng)濟組織經(jīng)營權的行使方式,并著手完善其土地經(jīng)營收益的分配機制,以確保各方利益得到公正、合理的體現(xiàn),從而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的順利進行,實現(xiàn)土地經(jīng)營效益的最優(yōu)化,促進農村經(jīng)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
關鍵詞:土地流轉;農戶;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新型經(jīng)營主體;權利關系和界定
中圖分類號:F321.1" " 文獻標志碼:A
農村土地流轉是在農村土地雙層經(jīng)營體制下,將土地使用權臨時或長期轉交給其他農戶或組織進行耕作和管理的過程,旨在實現(xiàn)土地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和農業(yè)生產的規(guī)模化、集約化。為了規(guī)范農村土地流轉行為,國家層面正式提出對農村土地進行“三權分置”,鼓勵在實際操作中以合法合規(guī)的方法,讓農民集體能夠有效管理土地,監(jiān)督承包者和經(jīng)營者合理使用土地,也提倡在理論上深入探討農民集體與承包農戶之間以及承包農戶與土地經(jīng)營者之間的權益界定和相互關系。通過這些實踐和理論研究,不斷完善厘清土地的集體所有權、承包權和經(jīng)營權之間的關系,為“三權分置”政策的實施提供堅實有力的理論支持和實踐支撐。然而,幾年過去了,不僅在實際操作中,農民集體依法行使所有權、監(jiān)督土地利用的具體方式仍不多見,而且在理論研究上,關于土地流轉中的權利邊界和相互關系的問題也缺乏深入的成果。由此導致如下現(xiàn)象:雖然“三權分置”為我國農地產權改革提供了制度依據(jù),但是現(xiàn)有的法律、法規(guī)、政策等在農地流轉管理中出現(xiàn)了一些空白或者處理不夠明確的問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還存在諸多爭論與障礙。因此,按照國家層面要求,深入研究并明確集體、承包戶和經(jīng)營主體在土地承包和流轉過程中的權利界限及權益關系,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為了更加深刻地分析和研究,可嘗試將“權利”一詞分解為“權力”和“權利”。本研究所指的“權力”,是指在農村土地經(jīng)營及流轉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可以按照國家有關法律的規(guī)定影響和改變個人或團體行為的能力;本研究所指的“權利”,是指權力人在相應的權力關系中通過合法行使權力應當?shù)玫降膬r值回報。
一、國內外關于農村土地產權的研究
(一)關于農村土地經(jīng)營的權利主體研究
國外的研究認為,農村土地的權利主體包括小農戶、合作組織、農場主、農民集體及政府等。馬克思認為,土地的權利主體包括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使用者即農場主、土地的耕作者即農民,主張國家為土地的終極所有者。恩格斯認為,要把小農戶的生產和物質占有的私有化轉化為以合作社為主的合作生產,并以示范和協(xié)作的方式對小農戶進行福利援助。可見其把小農戶和合作組織視為了權利主體。列寧繼承和發(fā)展了馬克思關于農業(yè)合作的理論,認為:“小農不僅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土地上的工人,而且是無產階級的堅定的同盟者,不能剝奪他們的權利,只有通過合作,才能把他們帶到社會主義發(fā)展的道路上來”。
國外學者普遍認為政府負責制定和執(zhí)行土地政策,為確保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通過調節(jié)土地供應和需求,維護土地市場的穩(wěn)定和公平。政府在進行土地征收、土地使用許可和土地開發(fā)時,需要考慮公共利益,提供土地登記、測量、評估等土地服務,為土地交易和使用提供便利。這些服務有助于減少土地糾紛,提高土地交易的透明度和效率。美國的現(xiàn)代農業(yè)管理制度包括了家庭農場與農業(yè)組織,主要是大型農場[1]。法國近代農業(yè)管理體制的建立,主要是以實行集中的土地制度為前提,以擴大農業(yè)規(guī)模和推行農業(yè)社會化服務為手段。在日本農業(yè)體制的發(fā)展進程中,農業(yè)管理得到了迅速發(fā)展,并且其服務職能也日益凸顯。根據(jù)日本農業(yè)歷史上的數(shù)次變革,可以發(fā)現(xiàn)日本近代農業(yè)管理體制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家族規(guī)模日益縮減、公司規(guī)模日益增加等特點。
Ichio SASAKI[2]認為德國以家庭農場為主體,以農業(yè)社會化服務系統(tǒng)為核心,德國的農業(yè)生產系統(tǒng)以家庭農場為主。Bitsch[3]認為韓國的農業(yè)生產體制是由家庭農場、農業(yè)企業(yè)和農業(yè)合作組織3個部分構成,其特征是由國家通過農協(xié)進行農業(yè)經(jīng)營,而農協(xié)則負責農業(yè)發(fā)展政策的落實。Kim Jeong Seop[4]認為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歐美發(fā)達國家中的英、美、法等國,都是以保護耕地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為目標,以法律手段對其進行規(guī)制,以“有償獲得”“以公為得”等方式,賦予“國家”與“土地所有人”相結合的“權利”。
國內研究表明,土地經(jīng)營過程中的權利主體就是土地經(jīng)營的利益相關者。在土地產權發(fā)展過程中,權利的主體主要有政府、集體、農戶家庭、新型經(jīng)營主體。政府具有國家公權力,對集體土地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和監(jiān)管職能。申惠文[5]認為,應當在恰當?shù)臅r機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便在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使得國家與集體、集體與集體之間可以依法進行土地所有權的買賣或轉讓。目前的農村土地管理體系中,“集體”與“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界限模糊,實際上將后者視作前者的代理人,這可能導致集體主體地位的不明確。農村集體土地的初始分配權在集體手中,農民作為集體成員,通過承包獲得土地的使用權、收益權等,但并不直接擁有土地的產權,通常是以承包經(jīng)營戶的身份來行使這些權利。新型經(jīng)營者往往是職業(yè)化的農民,他們在法律上應得到保護,確保他們對集體土地的承包權益穩(wěn)定,并通過合同確保這種關系長期有效。
(二)關于農村土地權利及其結構的研究
在分析土地產權問題時,馬克思認為土地產權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和支配權,其中土地所有權是核心,它允許占有者獨占土地并進行使用、收益和處置。在土地經(jīng)營上,馬克思提出了小土地經(jīng)營即小型經(jīng)營必然會被規(guī)模經(jīng)營所取代的觀點。科斯[6]提出產權可拆分為獨立的部分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等權能,分別由不同的主體擁有和行使。科斯深入分析了產權明晰界定對于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認為產權的可轉讓性是實現(xiàn)資源有效配置的關鍵。
國內關于農村土地權利的研究,主要依托于馬克思和科斯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更適合中國發(fā)展的路徑。土地權利就是土地生產資料的所有、占有和使用,實際上在中國的落實過程主要體現(xiàn)在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jīng)營權,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民通過承包取得土地的耕作權和收益。在農村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承包權經(jīng)歷了從“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的演變。黃祖輝等[7]認為,經(jīng)營權作為新興權利,在“三權分置”政策下得到明確,進一步促進了土地資源的流轉和高效利用。
(三)關于農村土地經(jīng)營主體的權力內容研究
賈后明等[8]從農地產權的視角對其進行了分析,認為農地的確權工作不能僅僅是要弄清楚農地的現(xiàn)狀和占有、管理狀況,還需要明確農村土地資源在市場化過程中的所有權、承包權、經(jīng)營權、流轉權、抵押權、轉讓權和收益權等。推動農地由模糊的產權到明晰的權利行使。王慧青等[9]認為,目前我國農地流轉面臨著土地用途變更、有效需求不足、流轉周期過長等諸多問題,而破解之道在于,必須按照法律法規(guī),積極開拓土地流轉市場。吳冠岑等[10]采用文獻綜述、歸納分析、比較分析等方法,對我國農地流轉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土地流轉的產權問題影響比較大。農地流轉過程中新型農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培育也日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而對村級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研究則相對匱乏。肖衛(wèi)東等[11]對村集體的權利進行了界定,對“三權分置”的內涵及權利關系作了細致的討論,認為“三權分置”旨在落實權利主體的權力過程,落實集體所有權是前提,穩(wěn)定農戶承包權是基礎,放活土地經(jīng)營權是核心。
總之,國內外學者已就農戶、集體及新型經(jīng)營主體的權益實現(xiàn)及農地流轉等問題開展了較多的研究,但對落實農村土地經(jīng)營權利主體的權利的研究存在不足,在權利關系的構建中忽略了權力界定和權利關系的比較,存在著權利主體界定不清、權利無法實現(xiàn)的研究空白。
二、中國農村土地經(jīng)營制度的變遷
生產力的發(fā)展引起生產關系的轉變,土地權力演變的過程伴隨著土地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早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其土地產權制度歷經(jīng)了漫長而復雜的演變過程。從早期的“井田制”到商鞅變法,再到明代“一條鞭法”和清代“攤丁入畝”的稅賦制度,逐步形成了與土地私有制相適應的土地產權制度。這一制度的形成,使得國家能夠較好地調整農民與地主、國家與地主之間的關系。然而,一次又一次的農民起義以及由此帶來中國封建社會朝代更替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前,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呈現(xiàn)封建特征,土地權利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地主和富農掌握著絕大部分土地資源,而貧農、中農、佃農等則僅擁有少部分。
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制度,逐步建立了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真正實現(xiàn)了耕者有其田。
1950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2]開始實施,廢除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確立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允許他們買賣和租賃土地,但受到一定限制。據(jù)統(tǒng)計,到1953年春,除了某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中國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超過3億的貧苦農民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他們能夠獨立耕作并享有全部產出,大大激發(fā)了他們的生產熱情。然而,土地的農民私人所有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土地向少數(shù)人手中集中的可能及趨勢。
隨著農業(yè)生產的恢復和發(fā)展,為了克服生產中的困難,農戶間通過共同勞動、人工或畜力互換等方式,自發(fā)組織互助組。后來,在互助組的基礎上,在初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中,農民將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入股,交給合作社統(tǒng)一管理和使用,但依然保留對土地的所有權。年終時,農民依據(jù)土地股份參與分紅。這標志著農民開始從個體經(jīng)營向合作經(jīng)營轉變,是農業(yè)集體化的早期形式。
隨著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開展,土地的產權結構開始發(fā)生變化。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中,一些決策者認為擴大農業(yè)合作化規(guī)模和提高公有制水平能夠更快地促進生產力發(fā)展,因此推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1961年6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通過《農村人民公社條例》[13],實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等由集體統(tǒng)一管理和分配使用,農民參與集體勞動,共享集體收益。這樣的經(jīng)營方式提高了土地規(guī)模化、農民組織化、生產合作化程度,但“政社合一”的體制機制,將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和集體經(jīng)濟組織合為一體,將農村的行政管理和經(jīng)濟活動混淆不分,忽視了客觀經(jīng)濟規(guī)律,導致農業(yè)生產經(jīng)營活動受到過多行政干預,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挫傷。
1978年后,農村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確立了農村集體統(tǒng)一經(jīng)營和農戶家庭分散經(jīng)營相結合的雙層經(jīng)營體制。農戶成為基本的經(jīng)營主體,其生產積極性得到極大激發(fā),農業(yè)生產效率顯著提高。然而,這種體制也帶來了土地的碎片化,導致農業(yè)生產規(guī)模化、集約化經(jīng)營水平降低,農業(yè)生產的相對成本逐漸增加,限制了農業(yè)技術的推廣應用,影響了農民的進一步增收和農業(yè)現(xiàn)代化進程。適應農民進城務工和土地代耕及流轉的需要,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為土地經(jīng)營權的轉讓和流轉提供了明確的指導和支持,允許農民在保留土地承包權的同時,將土地的經(jīng)營權讓渡給他人。在此制度下,農村集體依然能夠通過已有的承包合同獲得經(jīng)營收益,實現(xiàn)了集體和農戶的共同經(jīng)營,所有者權益和承包經(jīng)營者權益同時得到保障。
2006年,國家取消農業(yè)稅,這一改革具有歷史性的深遠影響,它不僅為農民減輕了經(jīng)濟負擔,還標志著在中國沿襲了超過2600年的農業(yè)稅收體系的終結,成為農村稅費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取消農業(yè)稅后,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和支持農民發(fā)展多種形式的合作經(jīng)濟組織,支持農民將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給種糧大戶、農民專業(yè)合作社等新型農業(yè)經(jīng)營主體,以實現(xiàn)規(guī)模化經(jīng)營,但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在土地流轉過程中一般沒有實質性參與。從那時起,原有的體現(xiàn)農村集體統(tǒng)一經(jīng)營和土地所有權收益,用于村一級維持或擴大再生產、興辦公益事業(yè)和日常管理開支的集體收入的“村提留”也隨之取消,造成了農村集體的土地經(jīng)營收益隨之歸零,農戶家庭基本完全擁有了農村土地的自主經(jīng)營權,所有權與承包權及經(jīng)營權開始分離,農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權益被嚴重虛置。
黨的十八大以后,為加快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國家于2013年提出了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jīng)營權三權分置的基本構想,在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里得到確認,明確提出要始終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根本地位,嚴格保護農戶承包權,推動土地經(jīng)營權的規(guī)范流轉,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jīng)營權被“并重”提出。201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布《關于穩(wěn)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14],確立了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維護了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確保他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權益不受侵害,推動了農村產權的規(guī)范流轉和交易,切實維護農村集體在土地流轉中的權益被重新提及,區(qū)別于農民專業(yè)合作社等經(jīng)營性的農村集體股份經(jīng)濟合作社應運而生,農村的土地經(jīng)營邁入以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主導的集體所有、合作經(jīng)營的新階段。
綜上所述,從新中國成立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土地改革再到農民合作社,新中國廢除封建土地制度,經(jīng)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從經(jīng)濟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從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到新型合作經(jīng)營,中國農村的土地經(jīng)營制度經(jīng)歷了不斷適應農業(yè)農村生產力需要的變化過程。這些變化反映了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變革歷程,也體現(xiàn)了國家對農村土地經(jīng)營制度的不斷探索和調整。
三、“三權分置”制度框架下的農村土地權力結構分析
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是新的歷史條件下農村基本經(jīng)營制度的自我完善、適應農村生產力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要求、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著力推進農業(yè)農村現(xiàn)代化的重要舉措。由圖1可見,在“三權分置”的制度框架下,明確“三權”的具體內容、權力邊界和權力保障,合理平衡“三權”利益,對于創(chuàng)新農業(yè)經(jīng)營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土地生產效率,以及激發(fā)農村基本經(jīng)營制度活力、推進農業(yè)農村現(xiàn)代化極為關鍵。
(一)農村土地權力的構成分析
馬克思和西方新制度經(jīng)濟學者認為,產權是圍繞著所有權展開的一系列權利,包括占有、使用和控制等,這些權利界定了人們與財產相關的合法行為和社會關系。運用這些產權理論并結合當前的產權制度基礎,中國將農地權利明確為所有權、承包權和經(jīng)營權,其中村集體保有所有權,農戶獲得承包權,而經(jīng)營者則獲得經(jīng)營權。
所有權是農村土地權力行使并通過統(tǒng)一經(jīng)營獲得利益的前提和根本,決定了土地的歸屬;承包權保障農戶對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構成農村經(jīng)營體系的基石;經(jīng)營權則允許經(jīng)過流轉的土地在約定時間內被經(jīng)營,以提升農業(yè)生產的靈活性和效率。這種分置旨在平衡集體、農戶和經(jīng)營者的利益,保護各方權益。
為了更加深刻地揭示問題的本質,本研究將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分解為農村集體對土地的歸屬權及其由此延伸出來的經(jīng)營權、使用權、發(fā)包權;將農戶家庭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分解為承包權、經(jīng)營權和經(jīng)營權流轉權;將土地經(jīng)營者的經(jīng)營權分解為經(jīng)營承接權和經(jīng)營權。
(二)農村土地權力的界限確定
2021年7月2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15]明確指出,除特定情況下法律規(guī)定為國家所有的土地外,農村及城郊的土地歸屬農民集體,包括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在內的土地也歸集體所有。國家通過制定土地利用的總體規(guī)劃來監(jiān)督管理這些土地的使用,特別是對耕地給予特別的保護,并嚴格控制將農業(yè)用地改變?yōu)榻ㄔO用途,以確保土地資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護。
2020年5月28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16]規(guī)定,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的方案、土地發(fā)包給集體外的組織或個人、承包地的調整以及土地補償費等費用的使用和分配,都必須依照法定程序,經(jīng)過本集體成員的共同決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農戶。這意味著,對于土地承包相關的重大事項,需要通過集體成員的民主決策,確保每位成員的權益得到充分考慮和保護。
2020年2月17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17]規(guī)定,農民作為承包方,對其所承包的土地擁有合法的使用權,能夠自主地進行農業(yè)生產的組織和經(jīng)營活動,并且有權自行決定如何處理農產品。承包方也有權自主決定是否將其承包土地的經(jīng)營權通過合法的方式轉讓給他人。在進行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時,承包方需向土地的發(fā)包方進行備案,以確保流轉過程的合法性和透明度。同時,土地經(jīng)營權的受讓方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也擁有對農村土地的占有權,并能夠獨立進行農業(yè)生產和經(jīng)營活動。
可見,圍繞著完善農村土地基本經(jīng)營制度,為了規(guī)范農村土地管理和經(jīng)營行為,國家有關法規(guī)對農村土地的國家管控權、集體所有權、農戶家庭承包權、經(jīng)營權和經(jīng)營權流轉權、新型經(jīng)營主體的經(jīng)營承接權和經(jīng)營權都作了較為明確的規(guī)定,但唯獨缺少關于農村集體對土地使用權和經(jīng)營權的明確規(guī)定,需要對相關法律法規(guī)作出相應修改予以補充和完善。
(三)農村土地權力的行使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guī)定,法律明確禁止任何單位或個人非法占用、買賣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轉移土地,允許土地使用權的依法轉讓。為了公共利益,國家可以依法征收或征用土地,并對受影響的個人或單位給予適當?shù)难a償。國務院自然資源主管部門負責全國土地的統(tǒng)一管理和監(jiān)督。如果出現(xiàn)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爭議,應首先通過協(xié)商解決;如果協(xié)商無效,則由人民政府介入處理。這些規(guī)定確保了國家的土地管理權的行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guī)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以及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如果屬于村級農民集體所有,那么由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依法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如果這些資源屬于村內多個農民集體所有,那么每個集體經(jīng)濟組織或村民小組分別依法代表各自的集體行使所有權。對于鄉(xiāng)鎮(zhèn)級別的集體所有資源,則由鄉(xiāng)鎮(zhèn)集體經(jīng)濟組織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這樣的規(guī)定確保了集體資源的合法管理和使用,同時也保障了集體成員的權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guī)定,農民集體依法擁有的土地,由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發(fā)包,并對承包方進行監(jiān)督和約束。發(fā)包土地不得改變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承包期內,發(fā)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調整承包地。土地承包者擁有對承包土地的自主經(jīng)營權利,并且在向土地發(fā)包方進行備案的情況下,可以決定是否將經(jīng)營權以出租、轉包、入股或其他合法方式進行流轉。土地經(jīng)營權持有者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有權占有土地并自主開展農業(yè)生產活動,同時獲得相應的收益。這些規(guī)定旨在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益,同時促進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和農業(yè)現(xiàn)代化發(fā)展。
可見,為規(guī)范農村土地的經(jīng)營、管理及使用,國家有關法規(guī)對于國家對農村土地的管控權、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農戶家庭的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新型經(jīng)營主體的經(jīng)營權的行使都作了較為明確的規(guī)定,但缺乏對農村集體土地經(jīng)營權即收益權的規(guī)定,農村集體的土地經(jīng)營權被體現(xiàn)在發(fā)包權上。這需要對相關法律法規(guī)作出相應修改予以補充和完善,對農村集體組織如何行使包括發(fā)包權在內的經(jīng)營權作出更加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
四、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的權利關系及配置缺陷
統(tǒng)計資料表明,截至2021年年底,家庭承包經(jīng)營的耕地面積約15. 75億畝,流轉面積5. 57億畝,流轉面積所占比例達35. 37%;承包經(jīng)營的總戶數(shù)22 087. 34萬戶,流轉出農戶7 586. 56萬戶,參與流轉的農戶所占比例達34. 35%。從2015年開始,比例不再大幅度增加,流轉面積和參與流轉的農戶基本維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見表1)。
產權理論認為,權力的界定和行使旨在維護和保障利益相關者的權利。在以上論述的基礎上,對土地流轉過程中的利益關系進行分析,找出現(xiàn)有制度中存在的權利配置缺陷,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從鞏固和完善統(tǒng)分結合的雙層經(jīng)營體制的邏輯起點出發(fā),審視農村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過程中權利關系及其配置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現(xiàn)行的制度設計存在如下缺陷。
(一)確保了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但缺乏土地所有權的權益體現(xiàn)
起始于改革開放初期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經(jīng)營責任制,是由村集體的統(tǒng)一經(jīng)營和農戶的分散經(jīng)營所形成的雙層經(jīng)營構成的。村集體的經(jīng)營收益即所有者權力收益是通過“聯(lián)產”的村提留而實現(xiàn)的,農戶的承包經(jīng)營權收益則是由在繳納農業(yè)稅和村提留后的剩余收入實現(xiàn)的。即便后來承包地的經(jīng)營權在農戶之間形成了自發(fā)流轉,國家的農業(yè)稅收和村集體所有權的權益收入并沒有受到影響(見圖2)。
但是,2006年取消農業(yè)稅后,村提留也被不經(jīng)意間取消,農村集體對土地的經(jīng)營只有相應的權責,卻沒有了相應的利益,所有者權益被實質虛置。直到2014年11月20日國家發(fā)布《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jīng)營權有序流轉發(fā)展農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意見》[18],提出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行“三權分置”、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jīng)營制度,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者權益問題才被重新關注。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國家出臺的政策性文件還是相關法律法規(guī),依然難以看到對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過程中如何保障農村集體所有者權益的明確規(guī)定。
(二)穩(wěn)定了農戶的承包權,但忽略了成員集體的合法經(jīng)營權
在以往規(guī)范農村土地流轉工作的一系列法規(guī)文件中,無論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禁止“返租倒包”“資源變資產”,還是“承包方可以自主決定依法采取出租(轉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轉土地經(jīng)營權,并向發(fā)包方備案”等方面的規(guī)定,重點都是為了充分尊重土地承包戶自身的意愿,對維護農戶家庭的土地承包權利、增強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穩(wěn)定性具有積極作用。
但是,這樣的政策規(guī)定卻不經(jīng)意間限制了農村集體統(tǒng)一經(jīng)營權的行使,導致新增的集體成員不僅不能及時獲得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而且也無法從集體的土地經(jīng)營中間接獲得相應收益。同時,該制度限制了農村集體的土地經(jīng)營權,使得農村土地流轉一定程度上處于無組織的失范甚至混亂狀態(tài),家庭承包戶的應得權益也常被侵害,從而影響了流轉的積極性和經(jīng)營的穩(wěn)定性,違背了政策的初衷。
(三)放活了土地的經(jīng)營權,但難以實現(xiàn)土地經(jīng)營效益的最優(yōu)化
促進農村土地經(jīng)營權的流轉,旨在適應當前農業(yè)生產力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要,提高農村土地經(jīng)營的規(guī)模化和集約化程度,促進現(xiàn)代農業(yè)生產技術的推廣運用。但是調研表明,盡管農村土地經(jīng)營權在農戶和新型經(jīng)營主體之間實現(xiàn)了自由流轉,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土地的規(guī)模化經(jīng)營,但由于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缺少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有效參與,農戶自愿進行土地流轉的積極性也因市場博弈能力偏弱而受挫,土地的碎片化依然存在,撂荒現(xiàn)象也有發(fā)生,導致旨在提高土地產出效益的高標準農田建設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不僅工程建設質量難以得到確切保證,先進的生產管理技術難以推廣,而且現(xiàn)代化的農田基礎設施的管理維護存在責權不清的問題,大力提高土地經(jīng)營效率的目標也沒有真正實現(xiàn)。
五、進一步優(yōu)化農村土地流轉經(jīng)營主體權利配置的對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針對當前政策法規(guī)中存在的制度缺陷,進一步優(yōu)化農村土地流轉經(jīng)營主體的權利配置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明確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在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中的主導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法》明確規(guī)定,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是發(fā)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jīng)濟、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主體,它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優(yōu)化農村土地流轉經(jīng)營主體的權利配置,需要充分尊重其作為特殊法人的主要地位,發(fā)揮其在農村土地經(jīng)營及土地流轉過程中的獨特作用,在穩(wěn)定農村土地家庭承包關系、鞏固農村基本經(jīng)營制度的基礎上,將農村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的主導權賦予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落實其農村土地經(jīng)營的組織領導責任。為此,應當將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合同主體由“農戶和經(jīng)營者”兩方變?yōu)椤按寮w、農戶和經(jīng)營者”三方。
(二)明確農村集體所有權和農戶承包權的財產性收益比重
農村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收益(俗稱地租),是包括所有權和承包經(jīng)營權在內的權利收益,是農戶和集體共同擁有的一種財產性收益。農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和農戶家庭承包經(jīng)營權均可認定為財產權。在確保農戶家庭承包經(jīng)營權收益不受損的前提下,在組織土地流轉過程中,應當允許村集體要求經(jīng)營權承接者在經(jīng)營收益中按照一定比例支付農村集體所有權的權利收益,從而調動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積極性,引導農民將閑置土地流轉給有經(jīng)營能力的集體、大戶、企業(yè)或新型合作經(jīng)濟組織,實現(xiàn)土地資源的高效利用,增強農戶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的組織化程度和市場博弈能力。這意味著農戶家庭在流轉土地時,不僅有權獲得土地流轉的租金收益,還有權參與土地流轉后的集體所有權權益收入的分配。這不僅能夠充分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還能激勵他們積極參與土地流轉,推動農業(yè)生產的規(guī)模化和現(xiàn)代化。為此,可將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居間服務費”分解為“居間服務收入”和“所有者權益收入”。
(三)進一步明確土地流轉相關經(jīng)營主體的權利和義務
優(yōu)化農村土地流轉經(jīng)營主體的權利配置,需要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應當以進一步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為重點,在農村集體的土地承包方式及流轉方式的選擇、發(fā)包方和承包方的權利和義務、土地經(jīng)營及經(jīng)營權流轉等方面,增加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主導經(jīng)營條款、農戶家庭的自愿選擇條款和新型經(jīng)營主體的經(jīng)營機制建構等相關條款,進一步明確相關經(jīng)營主體的權利、責任和義務,使土地承包經(jīng)營及土地經(jīng)營權流轉的程序、方法更加符合實際,使土地承包及土地流轉合同更加規(guī)范、科學和合理。
(四)規(guī)范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土地經(jīng)營權利的行使
對于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來講,落實土地集體所有權及其衍生的使用權和經(jīng)營權,是優(yōu)化農村土地流轉經(jīng)營主體的權利配置的重點。但是,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要嚴格防止集體所有權“異化”為村組干部所有權;要堅決防止走上“政經(jīng)不分”的老路,避免將農村基層黨組織和村民委員會與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混為一談。要以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和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成員的認定成果為基礎,明晰并固化村民集體及其財產的邊界;要在農村集體土地經(jīng)營管理中,建立村民集體的民主議事制度,依法保證他們完全享有集體土地使用、經(jīng)營、發(fā)包、轉讓、流轉、處分和收益等的知情權、決策權。
(五)完善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土地經(jīng)營收益的分配辦法
優(yōu)化農村土地流轉經(jīng)營主體的權利配置,最終要落實到農村土地經(jīng)營收益的分配上。在確保集體的所有者權益收入、農戶家庭承包權權益收入和經(jīng)營者經(jīng)營收入等在制度上均有相應體現(xiàn)的基礎上,對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土地所有權權益收入和其他形式的經(jīng)營收入進行分配使用,是優(yōu)化農村土地流轉經(jīng)營主體的權利配置的根本體現(xiàn)。要通過規(guī)定的民主程序制定相應的集體土地經(jīng)營收入分配使用辦法,正確處理發(fā)展和福利之間的關系,把保障包括承包農戶家庭成員在內的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成員的福利放在首位。
參考文獻:
[1]Meike WeltinIngo Zasada,Christian Franke,Annette Piorr,MeriRaggi,Davide Viaggi. Analysing behavioural differences of farm house holds:an example of incom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European farm survey datal[J]. Land Use Policy,2017. 62.
[2]Ichio SASAKI,Modem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Japan[J],Obihir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and Veterinary Medicine,2012,41(4).
[3]Bitsch. Veral Borucinska. Marta MMair,Stefan Schettler,Christiane A. Introduction of a Nation wide Minimum Wage:challenges to agribusinesses in Germany[J]. Economiaaero-alimentare,2017,19(1).
[4]Kim Jeong Seop . Trends of cooperatives establishment in rural Korea and lmprovemen of legislation[J]. Jourmal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mp; Community Development,2014,21(1).
[5]申惠文. 《民法典》集體土地權利主體規(guī)范的法政治學解讀[J]. 河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6(4):49-56.
[6]科斯. 企業(yè)、市場與法則[M]. 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0:123,90.
[7]黃祖輝,王朋. 農村土地流轉:現(xiàn)狀、問題及對策:兼論土地流轉對現(xiàn)代農業(yè)發(fā)展的影響[J].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2):38-47.
[8]賈后明,黃程程. 論農村土地確權中土地權利界定與行使[J]. 河北經(jīng)貿大學學報,2016(2):85-90.
[9]王慧青,尹少華. 農村土地流轉的問題及對策[J]. 特區(qū)經(jīng)濟,2011(5):187-188.
[10]吳冠岑,牛星,許恒周. 鄉(xiāng)村旅游發(fā)展與土地流轉問題的文獻綜述[J]. 經(jīng)濟問題探索,2013(1):145-151.
[11]肖衛(wèi)東,梁春梅. 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內涵、基本要義及權利關系[J]. 中國農村經(jīng)濟,2016(11):17-29.
[12]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EB/OL](1950-06-28)[2024-09-18]http://www. zmdsjw. gov. cn/sitesources/zmdjw/page_pc/ztzl/dsxxjyzl/dswx/articlef521a67ddc494a04bbd18b8556d2b960. html.
[13]中央工作會議上修訂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EB/OL](1961-06-15)[2024-09-18]https://illss. gdufs. edu. cn/info/1121/6075.
[14]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wěn)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N]. 人民日報,2016-12-30(001).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743號關于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EB/OL](2021-07-21)[2024-09-18]https://www. gov. 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 31813. htm.
[16]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EB/OL](2020-05-28)[2024-09-18]http://legal. people. com. cn/n1/2020/0602/c42510-31731656.
[17]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EB/OL](2020-02-17)[2024-09-18]http://www. zfs. moa. gov. cn/flfg/202002/t20200217_6337175. htm.
[18]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jīng)營權有序流轉發(fā)展農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意見》[EB/OL](2014-11-20)[2024-09-18]https://www. gov. cn/xinwen/2014-11/20/content_2781544.
[責任編輯:李偉杰]
收稿日期:2024-12-23
基金項目:河南省高校哲社應用研究重大項目(2023-YYZD-11);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決策咨詢項目(2024JC058);河南農業(yè)大學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應用類研究項目(FRZS2024B16);信陽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2024JJ041)
作者簡介:張錕(1962—),男,河南鹿邑人,正高級經(jīng)濟師,主要從事城鄉(xiāng)發(fā)展與鄉(xiāng)村振興、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李溫馨(1999—),女,河南南陽人,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