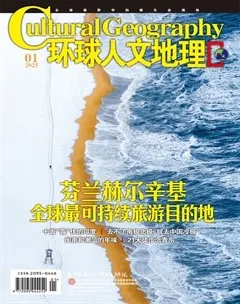從民間文獻看傳統時代深渡的水陸交通
深渡是安徽歙縣南鄉新安江畔的重要水運碼頭,據說原是因村前深潭渡口而得名。北宋初年,樂史在《太平寰宇記》中記載:深渡在歙縣東一百一十里,與睦州分界,“從新安江上,崇山峻流,爽秀尤異。欲到州界,峰巒掩映,狀若云屏,實百城之襟帶”。在清代,此地另有“深溪”和“深川”之雅稱。
作為交通要沖,在明代以來的商編路程圖記中,就屢屢出現“深渡”這一地名。例如,明末清初休寧人汪淇所編的《天下路程圖引》中,就有“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程”,其中提及由本府梁下(歙縣漁梁壩)搭船,十里至浦口,七里至梅口,然后經狼源口、瀹潭、薛坑口、莊潭、綿潭、蓬寨和九里潭,再五里至深渡……而經折本《杭州上水路程歌》亦載:“大川境口蓼花橙,白石磷磷傍岸行,深渡碧渡無可數,寒潭九里午風清。”及至同治十二年,在上海經商的婺源理坑人余岱雯,經由新安江輾轉回到老家,寫下了《徽浙水程詩》二十首,對沿途地名做了詳細的描述,其中一句作:“深渡清波魚可數。”
深渡依山傍水,街市及周遭村落民居鱗次櫛比,當地與歙縣的另一水運碼
頭漁梁一樣,以姚姓最占多數,故有“十里姚”之稱。傳說姚姓祖先始遷自成都西北武擔山,故名“武擔姚”,他們于宋代遷居于此,及至明清時代成為該處首屈一指的大姓。十數年前,筆者曾至深渡實地考察,見到當時尚存的姚氏宗祠,雖然其前半部分已完全毀損,但從殘存的部分來看,仍可得見昔日雄偉的氣勢。關于深渡姚氏,現存的《姚氏宗譜》中有《十世祖廷用公詩》,其中除《漁梁結屋》《鳳池書隱樓》之外,還有《深溪結屋》,載:“武擔山人老東麓,偶向深溪結茅屋,溪縈水面幾千尋,路轉山腰三百曲。”這里也明確指出當地的姚姓源自“武擔姚”。另一首《深溪鳳池巖結屋》則載:“茅屋初成三兩間,半溪流水半依山,江空歲晚誰為友,松竹梅花伴老閑。”從中可見,深渡姚氏中的一些人亦頗慕悅風雅。
明代以還,因轉輸貿易的興盛,深渡一帶店鋪林立。及至清代民國時期,當地船行眾多,這些船行主要都是姚姓所開。據調查,歙縣全縣共計有過載行(又名船行,即舊式之運貨公司)14家,主要分布于漁梁和深渡兩處,其中,漁梁計有8家,深渡計有5家,即姚日新、姚寶和、姚寶信、姚泰和與姚景和。所以在歙縣,一向就有“郡(按:指徽州府)中埠頭在梁下,南鄉埠頭在深渡”的說法。從現存的徽州文書來看,這些過載行的歷史顯然至少可以上溯至清代。
作為歙南重要的水運碼頭,深渡與縣內外各地商埠都有著廣泛的聯系。清咸豐十一年,太平軍攻占徽州,在各交通要隘設置哨卡,民眾往返,皆須持統一發放的“路憑”為證。1985年,在深渡一處姚姓宅屋內發現的一份《太平天國告示》載:“天福大人有令,績溪官兵齊聽,本爵恭奉王次兄金諭駐扎深渡安民,設關征收課稅,以便商賈通行。該處爾等正月搬糧過起,已有一月有零,又兼大隊過境,目下民不聊生,子民百般寒苦至今,何日安寧?所有績溪兄弟明早即行歸城,倘再任意駐扎,查出軍令施行。為其辦公至此,須呈路票為憑。急宜凜之慎之,勿怪本爵無情。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囗月囗日。”同時發現的還有木板印刷之太平天國路憑,其主要內容涉及深渡鄉民姚社有前往街口一帶買貨貿易。此路憑于1998年經國家文物鑒定組鑒定為一級文物,其最重要價值顯然在于反映出深渡是徽州人外出經商的交通要沖,即使是在咸同兵燹期間亦不例外。
除了起始或終到的貨物流通以外,深渡還是過往商品之集散地,1937年后的一張《民運車船通行證》就記載:“屯溪怡怡茶號,雇民船一只裝運茶葉,經過朱家村、深渡到達杭州。這份由呈,經本部核準,特許通行。”該份落款署名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和顧祝同的通行證,下令“凡本區以內各部隊不得攔阻扣留,妨礙運輸”,顯然是抗戰時期簽發給徽州茶商的特別通行證,其中亦提及經由深渡。此外,20世紀40年代由深渡商會開具的《證明書》,也反映了深渡與新安江流域各地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