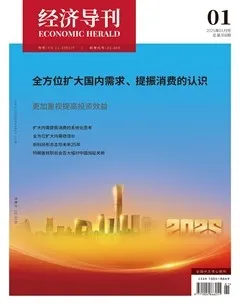特朗普就職后會否大幅對中國加征關稅
競選期間,特朗普揚言要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加征60%的關稅。他當選后,又威脅要對中國全部商品先征10%的關稅(獨立于其他關稅)。目前,特朗普贏得大選即將上任。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人們都非常關心,特朗普的新政府會不會立即對中國大幅加征關稅?
目前,美國國內輿論有大量針對特朗普對中國大幅加征全面關稅(60%)的聲音,但一直以來也有很多反對聲音,因為這意味著提高關稅稅率,并且將會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這是對供應鏈的擾亂,并可能帶來美國國內物價上漲。

反對聲音和不同意見
下面集中分析對中國進口產品大幅加征關稅的反對聲音及不同意見,以及特朗普自己的考慮。
反對加征關稅派
美國許多企業和機構從商業利益角度,反對美國以各種形式對中國進一步加征關稅。這些企業和機構有大有小,分屬不同行業,與中國的經貿聯系有不同方式:
(1)有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直接從事生產,部分產成品銷往美國市場(典型企業如通用、福特、特斯拉等車企;耐克、寶潔等消費品公司;杜邦和陶氏等化工企業)。這些企業是當年推動“離岸化”(offshoring),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方式將美國制造帶到中國的企業。他們代表的是資本的利益,希望獲取最大化收入和利潤回饋股東,當然不愿意主動放棄在中國的投資企業和中國市場。
(2)有些美國企業高度依賴中國供應商/供應鏈,例如需要采購中國的原材料或零部件(從礦產資源到電池),有的在中國依靠代工模式生產(例如蘋果手機)。這些企業在中國供應鏈的質量、效率、規模、在特定領域的技術含量、稀缺性等,都是其他海外市場短時間內無法取代的。這些企業當然不希望看到供應鏈被切割破壞。
(3)有的企業主要從事貿易,將中國供應商/品牌的產成品銷往美國零售市場,例如亞馬遜、沃爾瑪、Temu以及無數細分領域大大小小的零售企業,美國大幅加征對華關稅則意味著他們銷往終端消費者的產品價格會提高,短期又沒有平價替代品,結果導致銷售額下降。
(4)一些企業和中國有緊密的業務聯系,雖然未必和中國進口商品直接相關,例如Meta,雖然其旗下的社交媒體不在中國運行,但有大量中國供應商在Meta的平臺上投放廣告,其在中國業務收入占Meta全球總收入的10%左右。貿易戰將會減少中國供應商在北美投放廣告的意愿,進而減少Meta的收入;其他(包括大量科技公司)的重要甚至主要收入來源也在中國。如果美中經貿戰升級,很可能導致他們減少與中國客戶的業務往來,意味著這些公司營收利潤減少。
(5)金融資本投資可能受到中美經貿關系波動較大的影響,其中有的是一級或二級市場投資人;有可能投資在中國本土,也有可能投資在美國本土;投資有可能落在資產和實業上,也有可能落在金融/資本市場上(股票、債券);有可能投資于中國企業,也有可能投資于美國企業。只要他們的投資可能因為美中貿易戰進一步升級而受損,他們自然就會成為反對力量。前面舉的例子,蘋果、Meta、亞馬遜、PDD……沒有哪個投資人會樂見貿易戰升級。實業企業的投資、商業模式、業務布局、供應鏈體系都是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的,這類企業會更愿意通過游說的方式影響政府決策,但資本是流動的、自由的,可以立即用腳投票,“死給你看”,當即就反映在股票市場上,給決策者形成巨大壓力。盡管有一些美國本土制造企業可以從加征對華關稅中受益,但畢竟是少數。或者說,在這些企業背后,還有更多因為對華加征關稅而利益受損的跨國企業和金融資本——他們已經適應了2018年貿易戰以來的格局(包括拜登政府的有限升級),不希望特朗普再進一步大幅加征關稅,也不希望國會采取行動廢除給予中國的“PNTR”(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

此外,這些企業,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可能反對所有加征關稅的行為,包括但不限于:
把中國商品拿到第三國生產、改換生產國的商品也統統按中國商品加征關稅;
把帶有中國原材料和組件的最終產成品統統按中國商品加征關稅;
由于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反而加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失衡和沖突,導致更多國家對中國加征關稅(對于把供應鏈構建在中國、面向全球市場的跨國企業來說,將是災難);
所有可能進一步擾亂供應鏈,或給全球市場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的舉措。
請注意,以上只代表資本的邏輯,資本是“無國界”的,只希望(在可承受的風險內)最大化回報。如果由資本按照自己的利益去選擇的話,他們當然不希望看到貿易戰普遍升級。
“漸進派”
一些人意識到,在過去十年,重振美國本土產業已經成為美國的政治共識——老百姓擁護、兩黨政客支持,獲得了充分的政治授權,成為國家的政治選擇和歷史選擇。而如果美國要重振本土產業的話,可能確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用關稅手段(雖然關稅不是重振本土產業的充分手段,但可能是必要手段)。所以,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可能是一個企業需要看清、接受并適應的“政治現實”。
很多人長期不看好中美關系,認為中美地緣政治博弈實質上已經成為“新冷戰”,長期將發展為漸行漸遠的態勢,成為多極世界里的兩極。“在商言商”,在不摻入任何意識形態、政治判斷、價值判斷的情況下,企業只是出于規避風險、最大化收益的目的,認為有必要在供應鏈上做一定的布局。具體總結為三條,一是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不是清零,而是減少);二是增加對“友岸”的布局;三是參與產業回流美國(在政治上也能加點分)。至于關稅,如果特朗普政府已經認定對中國加征關稅是必需的,重點就將放在落地方式、步驟上,例如如何加征,以什么節奏,什么范圍,什么方式等技術問題。

“漸進派”認為,短期大幅加征關稅是供應鏈不能承受的,也會給美國本土的物價帶來較大沖擊。更加“現實”的方式,是在一個更長的時間段里逐步加征關稅。其中要具備幾個因素:第一是明確的目標(60%就是一個目標);第二是給出明確的時間期限(多少時間內完成);第三是時間充裕,但也不能太松弛。將“以時間換空間”,在漸進方案下,制定加征關稅的周期里,使企業對關稅做出反應,逐步在中國以外構建供應鏈。
像馬斯克(企業家+幕僚)、貝森特(提名財政部部長、企業家、金融家、幕僚)、托馬斯·弗里德曼(有一定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都以直接或委婉的方式提出了漸進方案。關稅(包括全面關稅)增加是有必要的,但要慎用,要用好。
“漸進派”其實也可能是“拖字訣”。特朗普畢竟只有四年執政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只要不一蹴而就加征關稅,后面就都有機會,因為政治變化要比構建產業鏈快得多、容易得多,他們也寄希望于中國國內經濟政策和環境的變化,例如,如果中國的內需將要大幅有效提升,或者找到了替代的海外市場,得以消耗產能,減少美中雙邊貿易不平衡,也有可能減少加碼美中貿易戰的政治壓力。但所有人都明白,美國這個產業邏輯,最終要的是產業回流。無論是中國本土消費,還是“友岸外包”,都不能解決美國本土的產業問題。漸進派提出了看似可行的方案(例如,“三年加征到60%”),特朗普就更難下決心依此大幅加征關稅。
“精準打擊派”
“漸進派”關注的是加征關稅的時間、節奏等問題;“精準打擊派”關心的則是關稅的范圍。核心在于,他們認為不應該不分品類地對所有商品加征關稅,只需要對有戰略重要性(產業戰略或安全考慮)的資源、產業、產品(包括組件)加征關稅就可以了。例如,中國出口大量低附加值的產品比例仍然較高,例如在Temu和亞馬遜上售賣的各種小玩意兒——從紡織品、玩具到各種日用品。這些商品有中國品牌,也有美國品牌和國際品牌,并沒有戰略重要性和產業重要性。按美國的現實情況,不可能將所有產業都回流本土。所以,加征全面關稅唯一可以確定的結果是,顯著提高老百姓日常購買商品的價格。也許中國供應商和跨國公司還可以慢慢尋找替代市場(包括擴大中國內需市場需求)、調整全球供應鏈,逐漸改善經營狀況,但美國老百姓面對的價格提升卻是即將發生、實實在在的。
因此,“精準打擊派”主張對特定產業和產品加征關稅。這其實是貿易官員一直以來更喜歡的做法,例如拜登政府推動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并且禁止中國生產的汽車互聯網硬件及軟件進入美國。這就是對有一定戰略價值的產業定點打擊。還有一個拜登政府和特朗普過渡政府都討論過的,就是對中國征收“芯片組件關稅”,即不論終端產品是哪國生產,只要包含中國制造的芯片,就要加征關稅,其目的也是打擊和限制中國的戰略產業(科技戰略、安全戰略)。
“精準打擊”的要義是避免全面關稅所導致的不必要的經濟成本。只要存在這種聲音,能向特朗普證明其價值,并能夠對美國公眾宣傳,取得一定的輿論認可和政治加分,也是特朗普大幅加征全面關稅后的替代政策。
主張精準打擊的,有企業和機構,也有貿易問題專家(可能是前官員、智庫學者,或學院學者)。

反通脹
能源價格帶動一攬子物價下調。哈里斯輸掉大選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過去三年多美國的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盡管通貨膨脹率已經得到控制,但物價的絕對水平很難再壓下去。特朗普當選后已公開承認這一點,將寄希望于通過全面開放油氣行業,把能源價格壓下去,并帶動整個物價指數下調。問題是,到底能以多快的速度調整能源價格,而價格調整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傳導到食品雜貨和房屋價格,這是有很大不確定性的,經濟學家之間也有很大分歧;但加征關稅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卻是“立竿見影”的。帶來的問題:是否應該先把能源價格壓下來,減輕物價方面的壓力,再伺機推動關稅政策;或者上來就加征關稅,寄希望于通過能源同步解決物價問題?更安全的辦法似乎是前者。
美國基層民眾無法承擔更多的通脹。民眾既希望看到產業回歸本土,期待更多的高質量就業機會,但同時又沒有能力承擔物價的進一步上漲。問題在于,產業回歸是一個“慢活兒”,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見效;而物價上漲是“立竿見影”,很快就能發生效果的。如果老百姓短期內看不見新的就業機會,又眼見加征關稅導致食品雜貨價格進一步上漲,高通脹又回來了,立即就會轉變為對現實的不滿情緒,給特朗普政府巨大的政治壓力。
宏觀經濟學家、中央銀行家、企業家。如果因為加征關稅導致通脹抬頭,美聯儲不僅會放棄降息通道,而且可能不得不加息。這就會推高利率,抑制企業/資本投資,同時提高老百姓的按揭成本。減稅 + 加息導致資本流入,推高美元,也會降低美國出口商品的吸引力,減少企業在美國布局產業的動力。
總而言之,美國通脹再次抬頭,既不利于經濟,也不利于民生,對于所有人來說都是壞消息。特朗普真的能夠承受加征關稅帶來的諸多成本嗎?
資本市場表現
特朗普對股市非常敏感,他將股市的表現等同于經濟的表現,等同于美國的經濟實力,等同于經濟政策的成功。因而資本市場表現會作為一個重要因素,限制他的政策選擇。從前面諸多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如果特朗普短期內對中國大幅加征全面關稅,將嚴重攪亂全球供應鏈,影響美國企業的收入利潤,增加美國國內的通脹壓力(同時,特朗普還醞釀對各種盟友及合作伙伴國家開打貿易戰,給全球經貿及地緣政治均增加了諸多的不確定性)。他的關稅政策如果從“口頭”轉化為實操落地,則金融資本會“用腳投票”,通過市場把明確的信號傳遞給新政府:他們不喜歡全面升級的美中貿易戰和全球貿易戰。對市場極為敏感的特朗普將會聆聽身邊幕僚和專家的建議,審慎決策。
以上五條,是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對短期內大幅對華加征關稅提出反對聲音,同時給出了替代方案(“漸進”“精準打擊”),避免采取正面“關稅戰”。
特朗普的算計
特朗普非常相信關稅的威力,自稱是“關稅俠”(tariff man), 認為關稅是解決一切沖突的手段(包括經濟與非經濟沖突)。但他在決策時,應該很清楚以下幾條:
1.在他的任內,必須解決通脹問題,而不能讓通脹再次抬頭。這是基于政治、經濟、社會等的全方面考慮;
2.食品雜貨價格、房屋這些涉及生活成本的價格,很難一下子壓下來;
3.利用能源價格降低物價水平,從所需時間,到具體效果都有不確定性;
4.將有無數企業前來游說反對全面加征關稅,或者游說尋求豁免,這些企業的實在利益是受到影響的。他也很難四處豁免,不容易“一碗水端平”;
5.包括馬斯克、貝森特在內的幕僚其實已經在建議漸進方案或其他替代方案,他手里并非沒有其他的政策錦囊;
6.他的目標是重振產業,這是個“慢活兒”,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哪怕他親自招商引資,簽下來項目,到真實落地形成就業和產出,需要數年時間;
7.他的加征關稅更適合用作威脅,真的落地就“不靈”了,而且“傷敵八百,自傷一千”馬上會顯現;

8.資本市場/金融資本對“貿易戰”升級毫無胃口,股市可能做出劇烈的負面反彈,給他形成巨大壓力;
9.特朗普任期僅四年,很快就會過去。他肯定要考慮遺產問題,即在短短四年里,到底能夠展現哪些業績。
如果特朗普威脅的對華全面大幅加征關稅真的落地,那就說明談判已經失敗。這時中國也不會妥協,美國就和中國“杠”上了。擺在眼前的只有關稅帶來的短期負面效果,而且基本可以確定,如果關稅有任何中長期的正面效果,也不會在特朗普的任內兌現。
我們看看特朗普到底想要什么,哪些是他真正喜歡的:
第一,要能在短期見效,最好幾個月內、最多一年內就有成果;
第二,要有視覺效果,“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第三,最好契合“產業回流”的主題;
第四,退而求其次,在其他美國民眾、MAGA非常關注的問題上取得進展也可以,例如移民問題、芬太尼問題、俄烏問題等。都可以算成他的業績;
第五,務必避免推高物價指數、增加通脹預期;
第六,要避免進入“靴子落地”后懸而不決、陷入困境和僵局的狀態。所以關稅不能輕易落地;
第七,受到資本市場歡迎,可以幫助推高股市。
特朗普自認為他揮舞關稅大棒,就可以談出他想要的交易。那么,哪些是他心目中的典型交易呢?

經濟方面:
逼迫中方同意強售TikTok,之后保留其運行。這就是他的巨大業績;
談出一兩個大型交易,例如中國龍頭企業到美國投資建設工廠或研發中心;
中國重新承諾并兌現首次貿易戰(第一階段)中承諾的對美國商品的采購。
非經濟方面:
在移民問題、芬太尼問題上得到中方更多的配合和承諾;
在國際問題上,例如俄烏、中東等問題上得到中方的配合;
特朗普更現實的一招是:持續對中國打擊,但就是不出大額加征全面關稅這張牌,也不放棄威脅。
大幅加征全面關稅就是一個懸在空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但這個劍只有懸在空中才能有效,所以是一個“不能落地的靴子”。他選擇的應該是:維持口頭對中國的關稅威脅,但主要選擇其他的方式打擊中國,譬如各種“精準打擊”的政策;更多的出口管制和制裁;同時,在一些非經濟領域限制中國(例如留學簽證、H1B簽證等)。但他絕對不會放棄用關稅做威脅。
特朗普不會上來就大幅加征關稅,而會更加謹慎地行事。在PNTR(永久正常貿易關系)的問題上,也會小心行事,雖然這更多的是由立法機構主導,而共和黨政客也都需要考慮企業、資本和民眾的反饋。如果有了這樣的判斷,中國也可以更加巧妙和沉著地應對。
(編輯 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