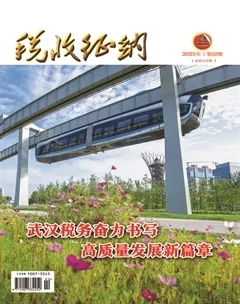楊炎:首創“兩稅法”,助唐度危機
被譽為“中唐理財雙星”之一的楊炎,青年時以“文藻雄麗”而出名,因在墓邊小茅屋服喪的孝行而被朝廷下詔旌表。47歲時,官拜宰相;任上第二年,定議改革賦稅制度,推行“兩稅法”。后期,卻因恃才傲物、擅權弄職、“睚眥必仇”,排擠殺害位高權重、同被譽為“理財雙星”的劉晏,而被政敵傾軋致貶官,55歲時被德宗賜死。不過,由他主持推行的“兩稅法”卻為中國稅收史留下了一段炫麗的篇章。
危難之際提出“兩稅法”
唐朝初期,沿用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后實行以人丁為本的“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的“租庸調制”。“安史之亂”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饑癘,征求運輸,百役并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土地兼并嚴重,賦稅戶籍混亂,百姓流離失所,唐帝國的財政已接近于崩潰的邊緣。
唐德宗李適即位后,為政清明。經宰相崔佑甫引薦,楊炎入朝為官。崔佑甫去世后,楊炎拜相。他認為當時的形勢已是“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因此繼續施行租庸調制的基礎已被破壞。于是向德宗上奏“創兩稅之新制”的倡議,指出“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
楊炎向德宗提出了“兩稅法”的具體設想:對待農民,要“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即不分本地戶和外地戶,以實際居住的地方為依據進行戶籍登記;不論人丁有多少,以擁有的財物多寡為依據,劃分貧富等級進行稅額分攤,這便是“兩稅法”的核心,“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實行“量能負擔”的原則。而且,它改變了以往賦稅集中在農民身上的不合理狀況,一定程度上能夠擴大稅基。
對于商人,楊炎認為“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即對于沒有固定居住地的商人,要在經營所在地納稅,稅率是1/30,與當地居住戶的稅賦大致相當,公平稅負。同時,他還對征繳時間進行了規定,“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征繳入庫,簡化納稅流程。
“兩稅法”簡并稅種,分為田稅和戶稅,統一了全國稅收。“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即戶稅以秋夏兩季征繳,實際征收時交陵絹,如有不便者可以適當進行調整,這就給了地方官吏便宜之權。“其租庸雜役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即除戶稅之外的一切租庸雜徭全部免除,繳納標準還是按照以前的規定執行。“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位準而均征之”,即田稅的稅率以大歷十四年(779年)的墾田數量為準進行均攤,按畝數交納米、麥,分夏秋兩季征收,統一計稅方法。這種田稅和戶稅的征收方式,標志著以人丁、力役為主的傳統賦稅制度,開始向以資產、實物為主的制度轉變,意味著統治者對農民的人身控制趨于松懈。
“逾歲之后,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即如果來年之后出現戶數增加而賦稅減輕,或者百姓流散、稅負失衡時,可以由尚書統一對長吏進行考核和獎懲,間接強化了地方官吏的征繳責任。
改革稅政為“兩稅法”鋪路
不過,“兩稅法”卻遭遇了當朝保守派的攻擊。“掌賦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余年,舊制不可輕改”。但在唐德宗的全力支持下,“兩稅法”仍在傳統勢力的反對聲中于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在全國推行。
推行“兩稅法”的阻力并不僅僅來自于保守派的舊思維。“安史之亂”后,唐朝吏治漸壞,不僅官員腐敗成風,軍事實力日益強大的地方勢力也漸漸顯露出欲成為“國中之國”的野心。史書記載,當時權臣滑吏,“或公托進獻,私為贓盜者動萬萬計”;藩鎮大吏,“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
由于中唐時國家財權被地方權臣、軍閥瓜分,各地“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稅收管理秩序混亂,苛斂繁巨。但是,權貴地主富豪能夠用各種辦法逃稅溜賦,而窮苦百姓“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稅負不均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口流散,“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因此,楊炎又建議德宗要規范朝廷的稅收管理秩序。
自西周以來,歷代統治者信奉的財政原則是“量入為出”,楊炎卻反其道而行,指出“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希望通過預算來控制賦稅的總額,以糾正以錢代役等征繳弊端,杜絕地方官吏橫征暴斂等痼疾,減輕百姓稅負壓力。

這也是楊炎面對朝廷“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于稅率少多,皆在牧守裁制”的局面,不得不推行的改革之法。
這種“量出制入”的財稅辦法,是基于他整頓稅權的理念而提出來的,也是目前已知的古代財稅史上最早提出“財政預算”的概念。
然而,朝廷派出的官吏在確定各州“兩稅”征繳定額時,采取的是“劾驗薄書,每州各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谷數量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的辦法。從“量出為入”制定稅額變為參照收成最好的一年的錢谷數量制定稅額,楊炎的改革初衷被各地官吏嚴重“扭曲”。
改變皇室“占公肥私”之弊
另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皇室財務和國家財政的互相糾纏。
“安史之亂”前,“天下財賦皆納于左藏庫(即國庫)”,太府每年按季節上報財賦數額,尚書核實錢帛收支情況,“上下相轄,無失遺”。“安史之亂”平定后,賦稅被移貯到大盈內庫(即皇帝貯存私財的倉庫),再加上宦官把持皇家內庫,虛領私占并大肆揮霍,導致“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這種混亂的財政狀況竟一直持續了20多年。
所以,楊炎向德宗提議,“天下公賦”,乃“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不能變成“人君私藏”,應交給有關部門管理,“量數奉入”。德宗深感其理,下詔將財賦重新納歸左藏庫,之后每年國庫“大盈”。
在德宗派員到各地推行“兩稅法”時,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與各地主管官員商定賦稅的分割比例。史載,“兩稅法”實行后,天下財稅共分為三部分,一是“上供”,即上交中樞;二是“留使”,即交給各地的節度使、觀察使以供支配;三是“留州”,給地方官府治轄所用。這種朝廷與地方“綜合分成”的財稅分配辦法,初步實現了財政方面的“輕重之權”皆歸于朝廷的目標。影響深遠。
“兩稅法”推行以后,“天下果利之”,取得了“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奸無所取”的良好局面。核定人口不再以土地定戶籍,而是以是否能夠務農安居為依據;官府不額外征賦,財政反而增加;不需要重新修造戶籍,卻能知道國家的真實人口;官吏不用厲法,而觸法者卻沒有藏匿之處。因此,楊炎獲得“救時之弊”的美譽,“兩稅法”也被稱為“誠適時之令典,拯蔽之良圖也”,成為使中晚唐150多年局面相對穩定的重要基礎之一。
但“兩稅法”的瑕疵同樣明顯。比如,各州稅率不一,于是重稅區的百姓就會流散到輕稅區,輕稅區的人口增加,但稅收總額不升;重稅區人口減少,而稅收總額不降,這就進入了“輕者愈輕、重者愈重”的惡性循環,導致稅戶遷逃之風盛行。另外,戶稅交綾絹時,無絹者就會折錢高價購絹完稅,出現“物重錢輕”的現象;同時,又會降價賣出擁有的物品,加上市場物價波動,無形之間百姓損耗日增,漸成“錢重物輕”之狀,百姓壓力陡升。再加上地方豪強恣意操縱“戶等”評定,有勢力的會勾結地方官降低戶等、資產增加的又不提高戶等,最終都會將稅負轉嫁給農民,漸漸衍生出新的弊端。
“理財成,侍君敗”,是后人對楊炎的評價。他一生毀譽參半,雖然挽救了唐帝國的財政危機,卻“險害之性附于心”。因劉晏參與審理宰相元載案時,楊炎曾被牽連遭貶,遂懷恨于心,伺機報復,劉晏被殺后,“天下以為冤”。楊炎為平息輿情,又派心腹散播流言,將責任推到德宗身上,招致德宗猜忌,最終在遭貶赴任的路上被德宗賜死。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運城市稷山縣稅務局
延伸閱讀
立法減稅讓古人安心發展
歷代封建王朝多看重立稅制,而輕于建立減稅制度。這就出現一種怪圈,往往王朝剛建立時、國力強盛時輕徭薄賦,但隨著社會生產力下降、政治積弊加深,就又回到橫征暴斂上來。所以,為了不使稅收成為危害社會安全的惡政,就必須給稅制打個“補丁”,修補制度本身的缺陷。在歷史上,也有過通過稅制改革以實現減稅的案例。
唐朝的“兩稅法”就是這樣一種制度改革。“兩稅法”表面上看只不過更改了計稅方法,但從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計稅本質上看,確實起到了對大多數百姓減免賦稅的作用。
“兩稅法”的出現,從稅收層面推動了社會公平,讓富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平民、貧困百姓可以適當減少納稅負擔,無疑緩和了社會矛盾。
據《通典·賦稅下》記載,“兩稅法”實行一年后,朝廷的財政收入從唐代宗時代的每年1200萬貫,增長到唐德宗時代的3000余萬貫。唐德宗的孫子唐憲宗之所以能平定藩鎮、取得“元和中興”,與百姓負擔減輕、社會矛盾緩和是分不開的。
明朝萬歷年間,由張居正總結推廣的“一條鞭”法,也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稅制改革,“一條鞭”法的核心思想與“兩稅法”相近,但在稅制思想上又進了一步。其核心要求是,以往的田租也好、力役也好,還有其他雜稅,由朝廷統一折價按白銀計算,百姓只需要交這些銀子,其余不用再交納、承擔別的賦役。好處在哪呢?其一,標準明確,百姓不用再受各級官吏盤剝;環節變少,壓縮了各級地方官吏貪腐截扣的空間;其二,解放了百姓的力役負擔,讓他們能夠專心于農業生產。
制度性的減稅,相比于皇帝心血來潮式的恩典,無疑更具有長效性和歷史意義,不僅使當時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也逐步推動著稅制思想的演進,可謂功莫大焉。
(據《北京晚報》陳峰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