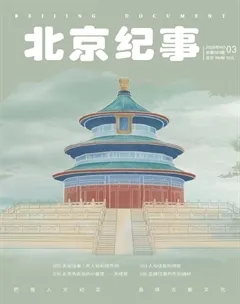匠心巧手鹵煮“香”
幾個小凳,幾張小桌,北京鹵煮江湖便由此誕生;一群食客、幾代相守,一碗鹵煮火燒卻承載了口味之外的迷人溫度;手手相承、余味悠揚,堅守著的不僅是手藝,更有敬畏。坐在北京老字號小腸陳的店中,聽著第四代傳承人陳秀芳分享著小腸陳的故事及技藝,折射出的卻是不少北京老字號所共同經歷的步步鏗鏘。
據史料記載,小腸陳的鹵煮火燒可追溯至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陳兆恩、陳世榮父子在宮廷御膳中“蘇造肉”的基礎上進行改良,將原有食材以豬內臟進行代替,并依據內臟特性對調料進行逐步改良,誕生了鹵煮火燒的雛形。經過發展,第三代傳人陳玉田從小攤兒到小店,讓鹵煮火燒受到越來越多食客的歡迎,更讓這普普通通的“平民飲食”引來社會的廣泛關注。第四代傳人陳秀芳接過接力棒后,不單堅守著父親所傳承下來的對于鹵煮火燒的各環節制作標準,更是以守正創新的思路,在京城打造出一家擁有獨特氣質、以經營鹵煮火燒為特色的現代企業。
1998年,小腸陳被認定為“中華老字號”“中國餐飲名店”和“中國特色風味餐廳”等稱號。1997年,“小腸陳鹵煮小腸”被中國烹飪協會認定為“中華名小吃”。2011年,小腸陳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重新認定為“中華老字號”。2014年,小腸陳鹵煮火燒制作技藝被正式列入北京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溫度,一位老人的守候
與陳秀芳的交流,并未和其他撰寫者一樣,從文化或口味開始,而是提出了一個問題:“雖然小腸陳的歷史非常悠久,又在北京飲食江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如今各家鹵煮字號遍布京城,為何還有如此之多的老饕衷心于這里?”
“我們很幸運,首先這是光陰賦予我們得天獨厚的優勢。”陳秀芳回憶起父親陳玉田,那是一位不善言辭的忠厚男人,家族的歷史只能在他的只言片語中逐步具象。
在大眾探源中,不管鹵煮火燒最初的淵源有多尊貴,有多傳奇,但其落腳點卻真真正正離不開人間煙火,它的誕生離不開“群眾基礎”。當時太爺爺和爺爺在農閑時支起爐灶、擺起小攤位,將當時價格低廉,甚至沒什么人能看上眼的豬下水作為原料制作鹵煮火燒。當時的鹵煮火燒只能算作是雛形,更多目的是一方面可以為家中改善生活,另一方面又幫助經濟拮據的百姓,在有限的條件內滿足口腹之欲的需求。其實,“下水”(北京對于內臟的稱呼)的價值到近幾十年前仍舊沒有改觀。以大腸為例,別看如今動輒幾十塊錢一斤,那時候才9分錢一斤,可想而知鹵煮火燒的價格也屬于親民一類。
鹵煮火燒之物從陳家而起,又從陳家而“興”,這要從第三代傳承人陳玉田說起。當時家里并沒有認為制作鹵煮火燒的手藝可以成為一門營生,而是為他選擇了另外一項與文化有關的職業——名片作坊。此名片與我們如今的名片有所不同,當時的名片并非小卡片,而是做工精美,帶有禮儀性質的“拜帖”,邀約吃飯、上門拜訪等均需提前“過帖”,提早知會。然而事與愿違,或許上天為每個人、每件事都設定好了機緣。為了生計,陳玉田拾起了老家兒傳下來的制作鹵煮火燒的手藝,支起了小攤兒,讓“鹵煮”再次出現在北京的鬧市中。
這樣的“再出江湖”便引出了小腸陳在京城鹵煮業的另一特色——實踐出的真味。
鹵煮火燒雖然從宮廷“蘇造肉”跳脫而來,但畢竟如今的主角“下水”擁有著眾所周知的“臟器味兒”。所以陳玉田在繼承的同時,也在做著不斷改良的探索。因為當時的市場環境,可以說這樣的過程并沒有太多來自外界的示范與參考,陳玉田只得一邊經營一邊摸索,逐步在祖上傳下來的技藝與配方的基礎上,結合食客們的反饋與喜好,對于調料、食材、技藝、火候等進行完善,通過實踐總結經驗,最終形成了京城食客為小腸陳鹵煮所總結出的“腸肥而不膩、肉爛而不糟、火燒透而不黏”的特點。
此外,這樣一種從實踐而出的真味,還是一種手手傳承的薪火,那更是第三代傳人給予第四代傳人的心緒傳承。
1956年公私合營后,陳玉田與他的小腸陳鹵煮并入燕新飯館,來燕新吃鹵煮成為老北京人曾經的記憶。不管買賣隸屬于誰,陳玉田仍未改變初心。用陳秀芳的話說:那幾年,在經營時間內,父親鹵煮鍋里的湯就沒涼過,所以父親幾乎沒有休息,直到快退休時有了徒弟,他才能帶著子女看場電影。
陳秀芳回憶,當時自己的學藝也經歷了不小的“心理斗爭”,作為一個女孩子,整天跟“下水”打交道,誰會愿意?更何況當時自己的工作也不錯,在印刷廠擔任著質量管理崗位。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改革開放的春風滋潤大地之時,南橫街附近的一座中式小樓成為小腸陳新的“主場”。第四代傳人陳秀芳一方面籌集資金,一方面積極對鹵煮火燒的制作與經營進行推動。為此,家里在賣了一輛摩托車后,啟動資金才終于湊齊,小腸陳在北京飲食江湖中再次“浮出水面”。
然而,當時北京市只有這一家鹵煮,老手藝人的工匠精神一點一滴地感染著陳秀芳。加之老廠長對自己的鼓勵,希望她能將北京的非遺技藝繼承下去,延續下去。另一方面,她小時候上學時,每天都要從父親的鹵煮攤前路過,眼瞧著父親的辛酸,與此同時又有越來越多的食客和父親成為老朋友,這之間的交往鏡頭潛移默化溫暖著陳秀芳的心。于是最終決定,全身心投入到這項事業中去。
可以說,這樣一個“從門外逐步走入門內”的過程是一份責任,更是因為情感的沁潤。這么一個手藝人,如此多的人對父親的友善與尊重,為了這口鹵煮,甚至有不少老演員帶著夫人從北影騎自行車專程過來吃鹵煮。另一方面,父親對于食客之情的回報與敬畏,也在感染著陳秀芳。那是一碗熱氣騰騰的鹵煮,面對上了歲數的老食客,父親總會親手為他們端到跟前。那是一小碟子香菜,與其他鹵煮店有所不同,并非是將香菜直接放入碗中,而是在努力保有鹵煮火燒本味的基礎上,會提醒大家如何才能吃得更舒服,更能品味鹵煮的真味,同時又起到了尊重愛吃香菜群體的需要。這種人性化的尊重更體現于食客的個性化需求,甭管你所需要的是有嚼頭還是軟爛的食材,經營者都會努力滿足,在鍋中為您翻找。
小腸陳從光陰深處走來,伴城市煙火發展,其實“匠心”也成為這里的特色。
雖然閨女接了班,但閑不住的陳玉田仍然堅持每天去店里,陪老主顧們坐會兒,為老食客們親手切上幾碗鹵煮,守著這爐火與湯鍋。陳玉田從青年走入暮年,守著這份食客與小店的溫情。陳玉田哪怕是幾十分鐘,仍然努力讓到訪者看到他的身影,在品嘗鹵煮的同時,多了一份安心與溫情。直至他88歲高齡時的一天,老人在小店為食客們切過了最后一碗鹵煮之后,便再也沒有出現在食客們的視野中。
陳玉田走了,留下的是北京飲食江湖中的一段充滿暖意的情,是因為“倔強”的堅守而為食客留下的味蕾深處恒久不變的標準,同時也是不斷思考、努力完善的耕耘之道。陳秀芳正沿著這條路,耕耘著、傳承著、跋涉著,也如父親一樣收獲著食客們的情感交融。
對話,手與食材的交流
一碗鹵煮火燒,之所以能夠享譽京城,深受幾代老饕喜愛,更有癡迷者坦言,一個月不吃就想,就饞,其中的奧秘何在?針對小腸陳的技藝技法,陳秀芳一一道來:
對原材料的把控,成為一碗地道鹵煮的首要“門檻”,這樣的門檻是小腸陳經歷多次考量而誕生的。那是一鍋沸騰的開水,三根腸子在沸水中翻滾,腸子上用繩子做好標記,按照鹵煮火燒所需的烹飪時間進行燉煮。結果發現,從屠宰場直接進貨的原材料,與從市場買來的,以及供貨商送來的相比較,質量擁有很大優勢。雖然這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代價,但把控食材的第一道關才是重中之重。
有人會發現,小腸陳的鹵煮沒有那么大臟器味道,但在口感上,又并不“發干”仍然非常滋潤。這是因為,在原材料的清洗環節便已經總結出了一定的經驗。例如腸子的清洗,首先要通過清水的初步清洗,而后將腸子由內而外翻出,使腸內壁露在外面,在這一過程中不單要保持腸子的完整度,也要注意清潔到每一細節。面對翻出的腸內壁,將多余的油脂一點點去除,與此同時按照口感要求,也要進行相對保留,使腸子在燉煮過程中,受到油脂的滋潤,達到最好的口感。去除一定腸油的腸子,再經過清水的細致揉搓、清洗達到清潔去味的效果。與腸子的清洗相類似,對于肺的處理同樣不可馬虎,結合如今消費者的飲食習慣,小腸陳盡量采用肺葉部分作為主要食材。清潔好的腸子與肺,由于是“下水”類食材,還要經過汆燙進行再次去味,并便于后續配送。
除了“下水”類食材的前期處理,豆腐與燒餅的制作也是一門學問。曾幾何時,為了保證食客的口感與飲食衛生,小腸陳都是自己制作豆腐,但由于現代市場法律法規的要求,如今的豆腐也都選擇從正規大型豆制品企業集中采購。采購來的豆腐,首先被切成方塊,而后改刀切成三角,一塊塊加工好的豆腐瀝干水分后進入油鍋炸至金黃。鹵煮中所用的火燒與平日里的火燒有所不同,以硬面形式出現。首先將和的面稍微醒發一會兒(醒發時間依據季節溫度也有不同)便要進入制作環節,按照一定標準揪成的面劑子,經過折疊按壓等手藝,還要便于餅在湯中入味達到2-3層,才能入鍋烙制,剛出鍋的小火燒圓潤可人,一斤面可以制作12個左右火燒。
有人會問,原材料準備好了,是不是就可以入鍋燉煮了?其實遠沒有這么簡單。別看深色的湯頭平淡無奇,卻擁有著深奧的內涵。根據春夏秋冬,小腸陳都會在二十來味調料中進行調整,把控住湯的醇厚味道不會因季節、溫度等因素受到影響。在這些調味品的基礎上,再配以豆豉、醬油、腐乳等調味料,加入清水,才能為鹵煮火燒的湯頭打下良好的基礎。
其實,入鍋的順序也被數代傳承的小腸陳傳人研究透了,這便是火候的奧秘,也成了一碗鹵煮成敗的決定性因素。通過經驗總結,首先將收拾好的“下水”入鍋,這類食材都屬于“平滑肌”需要長達2.5—3.5小時燉煮,才能更好地去掉原材料的臟器味兒,而且最終完美入味兒,達到適中的口感,用一句行業術語來說:“不能吐核兒。”顧名思義,好嚼、好咽、好消化。在出鍋前1小時左右放入炸豆腐,使其充分入味,最后再放入火燒,依據食客口感,進行售賣。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擔任小腸陳的廚師,必得有一雙“鐵手”,這其實也是鹵煮火燒傳承至今的“匠心”融入。之所以要求廚師徒手從湯鍋中快速拿起食材放于案板上切制,是因為在這一過程中,廚師會感受到食材的成熟度,針對每一食材的成熟尺度把控食客的口感,這樣一個過程宛若“手與食材的對話”。“對話”過程讓鹵煮火燒這一味蕾享受的飲食,擁有了更多一層欣賞的價值,廚師迅捷地從鍋中拾起原料,利索地斬切,有序地入碗,這不正是一場充滿味道的“演出”嗎?
其實這樣的“對話”同樣擁有著順序。最先出場的并非久候多時的“下水”,而是圓圓的火燒,它們被以“井字格”的方式切成數個小塊,成為一碗鹵煮火燒的基礎,為的就是碗中入湯后,餅的內心兒也可繼續泡至入味。而后依次出場的是豆腐、肺頭與腸子,一塊“炸豆腐”切成兩三塊、1—2兩肺頭、1兩腸子,成為一碗鹵煮的“黃金比例”。
見此程序您便會豁然,之所以沒有火燒的鹵煮會被稱之為“菜底兒”,是因為這豐富的內涵足可以當成下酒佳肴。那一整碗鹵煮火燒也可為您達到,“先吃下水解饞蟲,再食豆腐品濃湯,后吃火燒巧果腹”的綜合口感。
如今,小腸陳已經發展為具有一定規模,融入連鎖合作的餐飲企業,直營店就有7家,未來還在逐步開設分店,滿足北京的食客需求。從一家小店到此時的規模,推動陳秀芳改革的是一件有點“尷尬”的經歷。
當時小腸陳還是在南橫街的小店,但名聲早已遠揚,甚至到了海外。因為經營場地有限,又有諸多忠實的食客粉絲,所以本來局促的空間,經常被購買與排隊的朋友擠滿。一次,幾位外國友人來到小店,面對遠道而來的朋友,陳秀芳可犯了難。情急之下,她只能向街坊求援,能否暫借鄰居家的空間,讓外國友人一品北京味道。從那以后,陳秀芳總是不甘心,幾張桌子,幾個碗,外加一口鍋的小腸陳怎么就不能像剛剛興起的洋快餐那樣,打造成為窗明幾凈,遍布京城的鹵煮店吶?
于是這樣的想法,通過實踐逐步豐滿、成熟,南橫街、方莊、草橋、舊宮……一家家小腸陳傳遞著“舌尖上的北京”記憶。伴隨著經營場地的擴張、經營網點的布局,小腸陳也在做著有關餐桌上的更多嘗試。
一碗鹵煮火燒,幾代人的薪火傳承,不知我們的后代會以何種方式品嘗到小腸陳的味道,但相信這段與小腸陳有關的故事,會讓那鹵煮碗中的滋味更加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