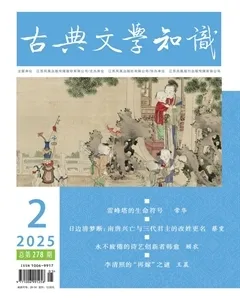談劉勰《文心雕龍》中的自然美
《文心雕龍》是南朝齊梁時期劉勰所撰,全面而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與創作經驗,被譽為“文學理論之巔峰”。劉勰在書中提出了中國傳統美學中獨特的自然美學觀念。
自然之美作為文學本原
劉勰生活的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在文化交流中逐漸交融。儒家的“天人合一”與道家的“道法自然”共同影響了劉勰的文論體系。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多次引用道家經典與儒家經典,體現了這一思想交匯。他的自然美學觀相比之下更多地受到老莊哲學思想的影響,深刻體現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自然之美是文學創作的源泉。
在《原道》篇中,劉勰將這一過程歸納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是萬物之靈,實為天地之心。有了心靈思維,就有了語言;而有了語言,就有了文章辭采,這是自然的道理。劉勰將文學的起源歸結為自然之道,認為文學創作應當遵循自然的規律,追求真實和美的統一。他進一步闡釋:“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 萬物有靈,自然界中的動植物、云霞草木都以其自然狀態呈現出美,這種美不是外加的裝飾,而是內在的、自然的。劉勰認為文章所要表現的,正是這種本原之物,自然的形態色澤之美,音響聲韻之美,龍鳳虎豹,草木魚蟲,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自然之美的體現,是道的體現,而文本于道。
《明詩》篇是這一觀點的鮮明體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生而有七情,這七種感情受外物的刺激而感發,為外物所感而吟唱出內心的情志,這無非是自然的流露。古往今來無數文人有感于自然,詩歌表達吟詠的內容也無非是自然之美。
《物色》篇更完整地闡發了自然山水是啟發文思的府庫這一觀點。“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景物有不同的形貌;人的情志隨景物變化,文辭則是因情志而抒發。自然景物的變化,使得人的心情也跟著產生波動,創作出的文學作品也離不開對自然山水之美的描摹。“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目力所及之處,青山重疊,綠水環繞,樹木錯雜,云氣聚合。目光既在景物間流連顧盼,心靈也在其感發下有所傾吐。春天的陽光溫暖和舒,秋天的西風颯颯蕭瑟。向自然傾注情感就如饋贈,而文思涌來是自然的酬答。
自然之美作為文學創作對象
雖然對自然之美的表現是文學創作的母題,但在劉勰看來,文學創作不僅僅是對自然美的模仿,更是對自然規律的遵循,這一觀點在文學創作的內容和形式方面都有論述。《情采》篇中,劉勰提出,自然界許多事物都有文采,因此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文章也必然富有文采。“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正如五色糅雜而形成禮服上的花紋,五音相配就組成《韶》《夏》等音樂,五性抒發而成為辭采文章,這是自然神明之理的法則。
但文學創作又不能一味地囿于對自然之美的還原,創作技巧的運用也不可或缺,至于形式層面,主要涉及了體裁與風格、聲律、修辭技巧幾方面。《定勢》篇中集中討論了文章體裁與風格的問題,不論是作品的風貌還是風格,都有其定勢,應順應自然。各種文體,“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就如同弩機發出的箭是直的,山間的溪流是湍急回旋的,這都是自然的趨勢。圓的物體有圓的形狀,它的形勢自然旋轉;方的物體有方的形狀,它的形勢自然平正安穩,文章的體裁和風格,就像這樣罷了。由此看出,文章的體裁和風格就像自然界中的山山水水一樣在無形的拘束間肆意流淌。
《聲律》篇中,對用詞造句的各種問題作了探討,文章對于音律的最高要求,無外乎音律的自然與和諧。文章的聲律,本于人的語言,有高下急徐之不同,這是自然產生的;但要認識掌握其中的道理,并使得所作的文章聲韻和諧,確是不容易的。“聲得鹽梅,響滑榆槿。割棄支離,宮商難隱。”聲律如咸酸調和,音韻似榆槿滑潤。摒棄不合律的音韻,聲律之美自然呈現。
《麗辭》篇,著重討論了修辭技巧等創作方法在文章中的運用,即在自然美之外,人工的雕琢與修葺也十分重要。劉勰是駢文的擁護者,他十分強調麗辭的產生、運用的必然性。《詩經》中對于自然景物的描寫不斷增加、豐富,但自然之美并不能被完全刻畫出來,所以出現了重復鋪陳景物的狀貌。劉勰認為作文必用麗辭,猶如動物肢體成雙作對,把人工的修辭技巧和自然生成的形體等量齊觀,“炳爍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自然之美陶冶文人性情
自然之美與文學作品的創作主體也密不可分。劉勰認為,在遵循自然之道之外,文學創作應當追求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這種統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契合。文學作品應當能與自然界一樣,具有生命力和動態變化,這是文學創作的最高境界,即達到與自然和諧相融的藝術境界。這無疑需要創作者的情感和思想的表達,需要文人以自然為師,通過對自然之美的興發感動,與自然同頻共振,以求達到藝術的完美。
劉勰認為,這種對自然的審美體驗,是文學創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學家在創作時,應當像感受自然一樣感受文字,讓文字如同自然中的山水、風云一樣,自然流露,形成一種生動的、有生命力的文學表達。在《物色》篇中,劉勰以屈原為例,進行了較為具體的分析:“是以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余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四時景物雖然循環往復紛繁變化,但作者情感興會的觸發卻貴在嫻靜;自然景色雖然豐富繁雜,但措辭用語貴在簡練;這樣就能使文辭的韻味飄然而生,使得情采光艷鮮明更顯新穎。自古以來的作家,歷代相繼,無不錯綜變化,由因襲變革而獲得成功,景物有盡而情韻無窮,是由于懂得融匯變通。至于山林原野,實在是為文構思的豐富寶庫;寫得過簡則有所欠缺,描繪太詳又失之繁蕪。然而屈原之所以能深切體察詩歌的情韻,大概也是因為得到了自然山川的幫助吧。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自然之美是文學創作的根本,而文人的性情則是表達這種美的重要媒介。“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里的“自然之道”不僅指宇宙間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也是文學創作的根本原則。文人通過自己的性情和才華,將自然之美轉化為文學藝術,使之成為可感知、可欣賞的存在。這種轉化不僅是對自然之美的再現,也是文人內心情感和理性思考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