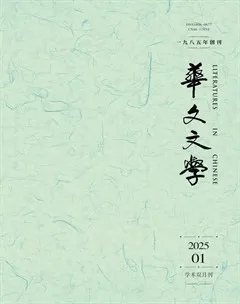“周樹人”如何成為“魯迅”
摘 要:日本的魯迅研究關注從“周樹人”到“魯迅”的形成,大致形成兩個研究路徑,一是竹內好、伊藤虎丸、丸山升、木山英雄、丸尾常喜、新島淳良、尾崎秀樹、竹內芳郎等關注從“周樹人”到“魯迅”的內在精神結構的變化,二是北岡正子、中島長文、吉田富夫等實證考察魯迅早期思想與留日時期明治三十年代文化語境的關系。作為旅日學者,李冬木接續了日本學者“原魯迅”的問題意識和實證研究的取向,近二十年來探討“周樹人”如何形成“魯迅”的命題,抓住進化論、國民性和個性主義這三個構成后來魯迅思想結構的基本元素,在歷史語境中就“國民性”“進化論”“尼采”“食人”“狂人”等魯迅思想與文學的關鍵詞進行扎實的材料實證研究,是文學史、思想史、社會史、理論傳播史等研究方法的綜合,整體呈現了明治三十年代博雜思想文化語境中“原魯迅”的形成面貌。
關鍵詞:李冬木;“周樹人”;“原魯迅”;“越境”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5)1-0037-05
“魯迅”為世人所知,始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從此“周樹人”成為“魯迅”。魯迅此時已滿37歲,在此之前,有一個頗長的“前魯迅”時期,不算離紹赴寧求學之前的家鄉歲月,自入江南水師學堂時被堂叔祖取名“周樹人”至《狂人日記》發表,以“周樹人”之名度過了早年求學、從教與為宦的近20年經歷,直到1922年底《〈吶喊〉自序》第一次自我披露,這些經歷才為世人所知。
“前魯迅”時期的1902—1909年,有長達7年的時間在日本留學,是周樹人21歲至28歲之間,這是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世界觀形成時期,堪稱“黃金年代”。因這一經歷,與中國魯迅研究者較多關注后來的“魯迅”不同,日本的魯迅研究者可以近距離關注“前魯迅”的日本時期,確切地說關注的是“周樹人”如何成為“魯迅”的。
首先是竹內好,在20世紀40年代初寫的小冊子《魯迅》中,開始追問“文學者”魯迅如何形成的問題,十年隱默與《狂人日記》石破天驚的靜動對比,吸引了他的注意,將考察重點放在《狂人日記》。竹內認為,“S會館”的隱默中孕育了某種可以稱之為“骨骼”、“根干”的東西,他以東方式的思維稱之為“無”,“魯迅的文學,在其根源上是應該稱作‘無’的某種東西。因為是獲得了根本上的自覺,才使他成為文學者的”①,竹內稱之為“罪的自覺”,而“賦予這種態度的是《狂人日記》”①。對于眾所共知的“棄醫從文”,竹內抗議對“棄醫從文”的功利主義解讀:“我是在把魯迅稱做贖罪文學的體系上來表達我的抗議”②,通過質疑“幻燈事件”的存在,竹內淡化了“棄醫從文”在魯迅文學中的起點意義。
竹內的關注形成了一個問題范式,其后的日本魯迅研究接著他的思路延伸。在“棄醫從文”問題上,新島淳良、尾崎秀樹、竹內芳郎等關注“幻燈事件”前后周樹人的思想變化,對棄醫從文的脈絡有進一步的梳理。循著竹內好的更深層的問題意識,丸山升和伊藤虎丸則試圖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理解,伊藤也試圖在S會館和《狂人日記》中尋找“‘小說家’魯迅誕生的秘密”③,但表達了不同的理解,認為魯迅獲得“個的自覺”,形成現實主義態度和科學方法,“和四十年前竹內提出的‘文學者’魯迅相反,如不妨取名的話,則是應該叫做‘科學者’魯迅的魯迅形象。”④丸山則將魯迅的沉默歸因于辛亥革命的失敗,并試圖建構與竹內“文學者”不同的“革命人”魯迅:“我的立場是探尋‘將革命作為終極客體而生活著的魯迅(倘若從他后來的話語中尋找形容這樣的魯迅最合適的詞,我想應該是‘革命人’吧)生發出文學者魯迅的這一無限運動’”⑤。木山英雄、丸尾常喜等則在《野草》中繼續探尋魯迅思想變化的線索。
日本學者的另一條探討路徑則更為具體實證,即還原周樹人留日的具體經歷及其所在的明治三十年代日本語境,并從文本入手考證魯迅作品所受日本語境的影響。北岡正子是專注這一問題的學者,1972至1981年在日本《野草》雜志連載的《〈摩羅詩力說〉材料來源考筆記》做過令人嘆為觀止的嚴謹考證(何乃英據此編譯成《〈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后又致力于對周樹人留日時期相關思想活動的考察,出版《日本異文化中的魯迅——從弘文學院入學到“退學”事件,青年魯迅的東瀛啟蒙》(關西大學出版部2001年版;臺北麥田出版社2018年版,王敬翔、李文卿譯)和《魯迅 救亡之夢的去向:從惡魔派詩人論到〈狂人日記〉》(關西大學出版部2006年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李冬木譯),前者基于大量原始文書檔案的調查,還原周樹人留日經歷及具體歷史情境,客觀呈現“置身于歷史現場的”周樹人,后者基于以前的《摩羅詩里說》“材源考”繼續探討留日時期周樹人“詩”與“人”的理想的確立過程;中島長文曾對《人間之歷史》的材源與日本書之間的關系進行揭示⑥,并編書統計魯迅閱讀過的日本書⑦;“棄醫從文”是魯迅自述的發生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的著名事件,日本“魯迅在仙臺的記錄調查會”對與此相關的史實做了詳細調查,編成《魯迅在仙臺的記錄》⑧,吉田富夫據此對“幻燈事件”進行翔實中肯的梳理,認為在仙臺醫專時代的周樹人還不是后來的“魯迅”,不能基于對后來的魯迅的判斷來闡釋“幻燈事件”⑨。
可以看到,日本學者的魯迅研究其實形成了一個與中國魯迅研究不同的側重點,如果說中國學者多關注后來的“魯迅”,日本學者則更關注留日的“周樹人”。1960年代,片山智行在對魯迅“初期文章”的解讀中提出“原魯迅”概念①,伊藤虎丸沿用了這一提法。“原魯迅”命題關注的,是留日時期“周樹人”如何成為“魯迅”,而不是從后來的“魯迅”逆睹留日時期的“周樹人”,這一研究視角與中國學者的研究形成了互補。
旅日學者李冬木是日本佛教大學教授,是魯迅研究家,也是優秀的日本魯迅研究的譯介者,前面列舉的日本魯迅研究著述如竹內好《魯迅》、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魯迅與終末論》、北岡正子《魯迅" 救亡之夢的去向:從惡魔派詩人論到〈狂人日記〉》、吉田富夫《周樹人的選擇——“幻燈事件”前后》等都經其嚴謹周詳的翻譯而面向中文讀者。作為旅日學者,李冬木兼具中、日學者魯迅研究的雙重問題意識,雙向吸收中、日研究的特點,既承續了日本學者“原魯迅”的問題意識和實證研究的取向,同時又受啟發于中國學者“魯迅”研究的豐富成果,基于此形成更大的研究設想,立足于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全局,探討“周樹人”如何形成“魯迅”的命題,近二十年來在日本和中國接連發表系列長篇論文,2019年在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兩卷本《魯迅精神史探源:進化與國民》《魯迅精神史探源:個人·狂人·國民性》,在此基礎上,2023年又推出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的《越境:“魯迅”之誕生》,這是第一次在大陸出版的結集,展現了二十年來苦心孤詣勾畫“原魯迅”面貌的精華。
從前文梳理可以看到,日本魯迅研究的關注點是從“周樹人”到“魯迅”的形成,大致有兩個研究路徑,一是探討“周樹人”到“魯迅”的內在精神結構的變化,二是實證還原周樹人的留日經歷及明治三十年代日本語境,并從文本入手考察魯迅思想與文學的日本影響源。李冬木的研究在兩個方面都有拓展,基于豐厚的中國魯迅研究界的學術成果,他對“魯迅”的文學和思想世界有全面理解和整體把握,先立其大,抓住進化論、國民性和個性主義這三個構成后來魯迅思想結構的基本元素,進行重點考察,研究目標更為明確系統;同時,他又延續日本學者的實證研究方法,利用深諳日文并身在日本的優勢,對留日周樹人及其日本語境的史料廣搜博考,以更大規模展開歷史與文本的實證研究。二十年來,他穿梭于明治三十年代的浩瀚文獻,就“國民性”“進化論”“尼采”“食人”“狂人”等魯迅思想與文學的關鍵詞,一個個排查考察,每篇論文都資料翔實理路嚴密,給人非常扎實的印象,更為整體地呈現了明治三十年代博雜思想文化語境中“周樹人”—“原魯迅”的形成面貌。
李冬木的研究展現了文學史、思想史、社會史、理論傳播史等研究方法的綜合,體現了關鍵詞研究的思路,對諸種思想元素如何由西方到日本,再到“周樹人”的實證考察,是觀念史和理論傳播研究的精彩個案。對魯迅接受史密斯的中間環節——澀江保的日譯本——的發掘,展示了近代“國民性”話語從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國的傳播路徑;在日譯“進化”取代漢譯“天演”的背景下考證魯迅與加藤弘之、楊蔭杭、丘淺次郎的影響關系,揭示了中、日接受進化論的不同樣式及復雜影響;對從摩爾斯、神田孝平到芳賀矢一的明治時代的“食人”言說的勾勒,展示了魯迅“狂人”與明治時期“狂人”言說史的潛在關聯;魯迅文本中的“斯巴達”也被當作“整個近代知識和思想傳播的一個環節來看待”,呈現出多重文本交叉中的觀念傳播與增值的過程;在思想史意義上對“國民性”概念史的梳理考釋,則展現了從西語到日語外來詞,再到漢語的傳播和演變過程,涉及話語史、觀念史和思想史的變遷。
這樣的研究自然屬于魯迅研究的前沿領域,但是看李冬木的寫作,卻沒有一般學術著作的枯燥,而是頗有“閱讀快感”。一是對每個論題的追索,都像破案一樣的精彩,甚至有點“懸疑劇”味道。如有關“進化論”研究,國內學者長期聚焦于與嚴譯赫胥黎《天演論》的關系,他則另辟蹊徑,鉤沉研究界尚未意識到的另一條線索,通過詳細考查,揭示從加藤弘之《強者之權力之競爭》,到楊蔭杭中譯本《物競論》,再到周樹人接受的線索,及其與丘淺次郎《進化論講話》的邂逅經歷。在這一過程中,李冬木展現了敏銳的發現與抓取材料的能力。魯迅與丘淺次郎的影響關系不易把捉,相關材料作為“斷片”散見于各時期的魯迅文本中,他從“奴隸根性”“偉人”“新人”“黃金世界”等細節相似性入手進行“破案”。
可讀性強的另一個原因是具有很強的“故事”性。考證研究難免艱澀,但李冬木在嚴謹的基礎上又發揮善于敘事的特長,將前沿的考證寫成一篇篇情節曲折的“故事”。對《斯巴達之魂》的材源考索就是這樣,他按兩個線索來講述,一是有關“斯巴達”的知識是怎樣傳到了周樹人那里的?二是這些知識如何經過篩選、剪裁和重構匯入《斯巴達之魂》的?順著——《瀛環志略》最初介紹斯巴達——《浙江潮》發表《留學界紀事·二 拒俄事件》——福田和民出版《西洋上古史》——中西副松發表《斯巴達武士道》——《清議報》《新民叢報》上有關“斯巴達”的言說——梁啟超發表《斯巴達小志》——周樹人在《斯巴達之魂》中通過對“德爾摩比勒”戰役的描述將“尚武精神”進行升華——的豐富情節,講述了一個駁雜語境中“斯巴達”話語曲折匯入“周樹人”的精彩故事,展現了“斯巴達”闡釋由“對其歷史、文化、政治制度、國民教育和尚武精神的借鑒”,到“拓展為一個包括思想、文化和國民性在內的文明實體”①的過程。
李冬木的研究與國內學界保持著緊密的互動。1995年中譯本《中國人氣質》由張夢陽、王麗娟翻譯出版,張夢陽先生寫了長篇的《譯后評析》附于書后,提到魯迅當年所讀到的“是澀江保的日譯本”②,李冬木讀了中譯本全部內容后,喚起了對史密斯與澀江保的研究興趣,因而特地在書中致謝中譯者,這是學術交流的佳話。筆者也與冬木先生有過學術“神交”,筆者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魯迅前期文本中的“個人”觀念,限于當時的資料條件未能進入明治三十年代思想文化語境進行考察,2006年赴東京大學開會,抽空到圖書館查資料,查獲《文化偏至論》中有關“極端個人主義”言述的材源(署名“蚊學士”),寫成論文發表,但“蚊學士”身份尚未查清,后與冬木先生第一次相見,向他討教“蚊學士”是誰的問題,他留意了我的問題并投入研究,寫成與筆者商榷的長文③,對“蚊學士”的身份進行了澄清,這是我們交流的開始。2018年我在《文學評論》第5期發表考證《狂人日記》的材源《狂人論》和《二狂人》的文章,同期也刊有冬木先生的文章,他也同時關注到這一問題,視野更開闊。編輯特意編在一起,這是一次互不知情的情況下的“相遇”,在魯迅的召喚下走到一起。
魯迅說文學是世界上的“文字之交”,李冬木將自己的新著命名為“越境”,我想,“文字之交”就是文化間的“越境”交往,魯迅的文學世界就是在“越境”的“文字之交”中形成的。人文學術研究也是“文字之交”,更需要“文化越境”的交往意識。李冬木說:“研究日本,尤其是研究明治日本,對中國而言也就并非是對他者的研究,而是對自身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④,希望“從狹隘的‘一國史觀’拓展到整個近代跨國界的處在不斷流動、轉換、生成狀態的廣闊的‘知層’。”①誠哉斯言,日本是西學中漸的中轉站,中國接受西學多經過“東洋”的中介,習慣性的中—西二元視角已不能描述現代轉型的復雜性,需將“東洋”納入考察視野,在更大的視野和更深的問題意識中關注中國、亞洲和世界的知識互動與精神交流。
(特約編輯:江濤)
How “Zhou Shuren” Became “Lu Xun”
---Li Dongmu’s “Transcultural”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al Lu Xun”
Wang Weido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Lu Xun in Japan focus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Zhou Shuren” to “Lu Xun”, roughly forming two research paths. One is the study of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spiritual structure from “Zhou Shuren” to “Lu Xun” by scholars such as Takeuchi Yoshimi, Toramaru Ito, Noboru Maruyama, Hideo Kiyama, Tsuneki Maruo, Atsuyoshi Niijima, Hotsuki Ozaki, and Yoshiro Takeuchi. The other is the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s early thoughts and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third decade of the Meiji Era during his stay in Japan, conducted by scholars such as Kitaoka Masako, Nakajima Osafumi, and Tomio Yoshida. As a scholar residing in Japan, Li Dongmu continued Japanese scholar’s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radition on the “Original Lu Xu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e has explored how “Zhou Shuren” formed the proposition of “Lu Xun”, focusing on the three basic elements—evolution, national character, and individualism—that constitute the later structure of Lu Xun’s thought. Through detailed empirical research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Li has analyzed key concepts of Lu Xun’s thought and literature, such as “national character”, “evolution theory”, “Nietzsche”, “cannibalism”, and “madman”. Li’s work synthesizes research methods in literary history, intellectu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dissemination history, presenting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formation of “Original Lu Xun” in the divers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third decade of the Meiji Era.
Keywords: Li Dongmu; “Zhou Shuren”; “Original Lu Xun”; “transcultural”
作者單位:汪衛東,蘇州大學文學院。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域外魯迅傳播和研究文獻的搜集、整理與研究(1909—2019)”(20amp;ZD339)。
① [日]竹內好著,李冬木譯:《魯迅》,見《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8頁。
① [日]竹內好著,李冬木譯:《魯迅》,見《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6頁。
② [日]竹內好著,李冬木譯:《魯迅》,見《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8頁。
③ [日]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李冬木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頁。
④ [日]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李冬木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頁。
⑤ [日]丸上升著,王俊文譯:《魯迅革命歷史——丸上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
⑥ [日]中島長文:《藍本〈人間之歷史〉》(上、下),《滋賀大國文》第十六、十七號,1978、1979年。
⑦ [日]中島長文:《魯迅目睹書目——日本書之部》,宇治市木幡御藏山,1986年私版。
⑧ [日]“魯迅在仙臺的記錄調查會”編:《魯迅在仙臺的記錄》,東京:平凡社1978版。
⑨ [日]吉田富夫著,李冬木譯:《周樹人的選擇———“幻燈事件”前后》,《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
① [日]片山智行:《近代文學の出発——“原魯迅”というべきものと文學について》,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編:《中國近代思想と文學》,1967年。
① 李冬木:《從“斯巴達”到“斯巴達之魂”——“斯巴達”話語建構中的梁啟超與周樹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年第4期。
② 張夢陽:《譯后評析》,亞瑟·亨·史密斯著,張夢陽、王麗娟譯《中國人氣質》,西寧: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頁。
③ 李冬木:《留學生周樹人“個人”語境中的“斯契納爾”:兼談“蚊學士”、煙山專太郎——與汪衛東先生〈現代轉型之痛苦“肉身”:魯迅思想與文學新論〉對話》,收呂周聚、趙京華、黃喬生編《世界視野中的魯迅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
④ 李冬木:《越境——“魯迅”之誕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27頁。
① 李冬木:《魯迅精神史探源:個人·狂人·國民性》,臺北: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