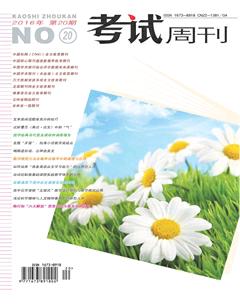因材施教,因地制宜
朱楓
法國思想家教育家盧梭說:“大自然希望兒童在成人以前就像兒童的樣子。如果我們打亂了這個次序,他們就成了一些早熟的果實,他們長得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會腐爛,我們就會造就一些年輕的博士和老態龍鐘的兒童。”一位心理學家說:“童年的價值就在于幸福。”那么,如何給予孩子一個幸福快樂的童年?語文順應減負增效的大背景,又能為學生一生的發展做些什么?南環實小的語文老師在多次教研活動的探討中總結了這樣幾行字:語言習得,打好扎實基礎;習慣培養,形成持久學力;興趣激發,引入讀書殿堂;價值引領,鋪墊人生底色。我以此為目標,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展開了個性化作業的初探。
南環實小是在依托南環新村改造重建的背景下,異地重建的一所新校,學校是嶄新的,可學生卻存在很大的差異,這就決定我們對每個年級學生的學情要進行詳實的分析后才能設計出符合學生實際情況的自主性個性化作業。我所執教的高年級是從原南環小學回遷的學生,這些孩子大多來自外來務工人員家庭,父母忙于生計,文化水平有限,在學習上對孩子的幫助不多,主要依靠老師在校時間的輔導,因此我在設計每周一練的時候從以下四方面進行了考慮:
1.夯實基礎,內容豐富,培養閱讀興趣。
以我在五年級上學期設計的第二周每周一練為例,第一大題看拼音寫詞語,都是在總結學生默寫錯誤之后精心設計的,數量不多,但囊括了學生的主要錯誤。如“炊煙”的“炊”,“引人入勝”的“勝”,“鍛煉”的“煉”,“公德”的“公”,“激勵”的“勵”,“拐杖”的“杖”都會產生同音字的混淆;“鞭策”是學生容易寫錯的字。也許這些詞語對名副其實的實驗小學五年級學生來說不在話下,可是在實際作業過程中卻真的發現有極個別學生錯誤率在四個以上,大部分學生都有兩個左右的錯誤,雖然情況很不理想,但是錯誤之后的訂正卻再一次加深了學生的印象,夯實了字詞基礎。“笨鳥先飛”,我的作業設計中唯有不斷出現這些基礎性習題,不斷地強化記憶,才能讓這些孩子打好扎實的語言基礎,為句段的訓練做好準備。
在另一期的每周一練設計中,在同樣夯實基礎的前提下,我又呈現出內容豐富、題型多樣的練習,如,讓學生用“心”組詞,再將這些詞語恰當地填入短文中,考查學生的語言文字運用能力。按課文內容填空,雖然簡短,卻概括整單元課文的中主要內容和主題思想,幫助學生梳理知識點。閱讀理解,甄選的文章挺長,卻沒有題目,貌似不完整,卻是我特意為之。記得我在課堂上做過一個調查:給你們一篇有題目的故事,故事很短,另一篇是沒有題目的文章,但是很長,你們愿意讀哪個?學生都不約而同地回答是后者。繼續追問,有個學生忍不住插嘴:“我們希望是沒有負擔的閱讀,這更能激起我們的閱讀興趣,而不是為了完成題目必須去讀。”回頭想想,孩子確實也不易,尤其到了高年級,太多的閱讀訓練,已經讓孩子們看到文章就望而生畏,甚至本來挺愛讀書的孩子,也漸漸失去閱讀興趣。更別說像這些本來課外閱讀就很少,甚至家中都沒有課外讀物的學生。于是我心生一計,何不將精彩的故事作為個性化作業設計其中,孩子一想,原來這一大題只要我讀讀這個神話故事或小說就好了,多輕松。當事情由被動變為主動的時候往往會呈現意想不到的效果,幾次嘗試后,我并沒有發現孩子偷懶不讀的,反而都在期待這一周的每周一練,甚至還能聽到下課孩子們在交流對故事的不同看法,既積累了課外閱讀量,又提高了孩子的閱讀興趣,無形中提高了他們的“解題”能力。
2.鼓勵創新和文本的多元解讀。
盡管孩子基礎不是很好,但思維還是很活躍的,因此高年級老師設計的作業必須滲透思考,拓展,甚至創新,這也是由孩子的年齡特征決定的。因此,在閱讀訓練中我精心設計了很多答案多元化的題目。如第九周的練習中,閱讀短文最后一個題目:有學生說,烏鴉不守信用。它曾信誓旦旦地答應為刺猬保密的,可到關鍵時刻,卻出賣朋友。這種鳥不值得與它做朋友。你怎么認為呢?請談談看法。在前兩次的“零負擔閱讀”中,學生的思路已經漸漸打開,并開始喜歡上討論,于是出現這樣的題目正中下懷。只是有部分比較謹慎的學生問道:“老師,答案是唯一的嗎?”“當然不是,只要你能自圓其說。”老師的回答贏得一片掌聲,就這樣多元解讀文本,這個概念,在他們心中慢慢生成,也鍛煉了高年級學生的自主學習及創新的能力。
3.注重積累,培養德行。
我利用原本不起眼的頁眉處,根據每一單元的不同主題,精心挑選配合單元主題的積極向上的名言警句,既在盡力彌補孩子課外積累少的不足,又在幫助他們樹立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
4.作業分層并進行分層評價不足。
至于作業分層,針對班里孩子的不同情況,我首先考慮到的是量的分層和難度的分層。誠然,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在高年級組,有一小部分從普通完小回遷來的孩子,由于各方面原因,基礎相當差,他們能夠完成并消化規定的語文作業就不錯,因此,個性化作業暫時只要求他們將前面夯實雙基的題目保質保量地完成就可以。對于另外一部分學生,當然要求他們完成一定的課外閱讀訓練。但是后來,我觀察到這些后進學生也有強烈的上進心,也希望自己能完成和其他孩子一樣的學習任務。于是我想到時間分層和分層評價。對于這些后進的孩子,當他們完成第一階段的習題之后就給予肯定和鼓勵,甚至獎勵,繼而給出比其他孩子更多的時間,完成同樣量的閱讀訓練,幫助他們逐步提高。學有余力的學生可以選做閱讀題,提高閱讀理解的能力。同時對分層布置的作業,采用分層評價法。只要學生完成了相應層次的作業,就可以得到肯定,既充分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又促進學生全面、持續、和諧地發展。
我在“個性化作業設計”的實踐中達到了一定的效果,也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良好效果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自主性作業設計使學生有主動完成作業的愿望,作業完成效率有所提高。他們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完成自己能力所及的作業,特別是對于成績落后生,現在作業的情況大有改觀。(2)學生能主動地保質保量地完成作業,每個人都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一定的進步。他們的思維力、創造力、想象力得到了發展,學會了創造性學習。(3)對于改進教師的教育方法、學習理論、提高教學效率有一定的作用。同時,也能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
需要我進一步反思、研究的問題有:由于時間和精力有限,我不能對所有學生都個別對待,不能保證每一個學生、每一天都能拿到適合自己的作業;學無止境,關于個性化作業設計方面的理論,還需進一步加強。當然這項工作我會長期堅持下去,這樣才能使教學工作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