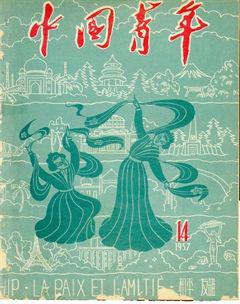關于藝術和政治(上)
陳涌
一
文藝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對象是知識青年。因此如何幫助他們正確地對待文藝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全國解放以后,報刊和學校對于宣傳馬克思主義關于文藝的基本觀點做了很多工作,文藝上的唯心主義觀點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大大地縮小了它的影響范圍,大多數青年都認識到文藝是階級的政治斗爭的手段,而新的人民的文藝應該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文藝上的超階級超政治的觀點,在青年中已級普遍地認識到它的錯誤。
問題自然并不是沒有了的。這種馬克思主義關于文藝的基本觀點的宣傳,不過是一種初步的宣傳,而且常常還有教條主義的缺點,在肯定文藝的階級性、政治性,肯定新的人民的文藝應該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時候,卻往往對問題達到了簡單化的結論。
肯定了文藝的階級性、政治性,肯定了我們的文藝應該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還不等于已經解決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的全部。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的問題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過去文藝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是不夠的,在理論上,在文藝工作的指導上和創作實踐上,都有過許多教條主義的表現,這便不能不給許多青年帶來不好的影響。
文藝的問題也和哲學問題一樣,唯心主義是有一定的階級的和認識論的根源的,不能把它看作只是一種胡謅,要征服唯心論是一件復雜的細致的工作。教條主義是不能真正征服唯心主義的。而且有時恰好相反,對于文藝的階級性、政治性,對于文藝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簡單化教條主義的解釋的不滿以至厭惡情緒,可能引起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動搖,而一部分本來便有脫離政治傾向的人也可能走向極端。因此,在我看來,在文藝問題上,反對脫離政治的傾向和反對教條主義常常是需要結合在一起的。
今年二三月間,北京清華大學的校刊上曾經展開了文藝問題的爭論,在三月底還由該校團委會文藝工作組組織過一次辯論會。爭論的方式是生動、活潑的,表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后,知識青年在思想上的活躍;而討論的問題實質上正是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這個重要的問題,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很大的興趣。
討論是從一篇叫“加強對閱讀文藝書刊的指導”一文開始的,這篇文章批評了這樣的一種意見,這種意見認為“評論一篇作品好壞的標準,僅僅是藝術性”,這篇文章也批評了不喜歡某些蘇聯和現在中國的作品,而一些“灰色的”甚至“黃色的”作品卻有很大興趣的一些同學,接著又出現了“應該從文學作品吸取什么”(廉之)、“他們在追求什么”(鋒芒)、“必須分清‘解花和‘雜革”(立人)等文章,這些文章的基本精神和“加強對閱讀文藝書刊的指導”是一致的,它們更具體地批判了在一部分同學中對待文藝問題實質上是脫離政治的現象。以后便出現了“是‘受教育還是‘欣賞”?是不同意廉之、鋒芒的意見的;此后還有叫作“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藝術感染”(野草)、“思想性——文學作品的靈魂”(安揚)、“感染人的主要是什么”(李隆瑞)等等,便連標題也可以看出他們的意見互相對立,爭論的熱烈,是可以想見的了。
問題的分歧之點是明顯的:對于一個文藝作品說來,重要的是政治還是藝術?在理論上,這似乎是沒有什么可以爭論的,因為關于衡量作品的標準問題,毛主席已經有過大家都很清楚的分析。從毛主席的分析里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毛主席肯定衡量一個文藝作品的時候,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但同時,毛主席又認為,政治不等于藝術,政治和藝術、形式和內容應該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這前后兩個意思粗看起來似乎是有點矛盾的,既然說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怎么又說政治和藝術、形式和內容應該統一,降低了任何一方面都應該反對呢?到底毛主席為什么同時說出了這兩個粗看起來是不盡相同的意思?
但是,如果我們稍為仔細地把這兩個“不盡相同”的意思聯系起來加以考慮,我們便會得出結論說,這里正包含著一個具有高度黨性的、馬克思主義關于文藝批評,同時也是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的完整的觀點。政治和藝術應該統一,要求政治和藝術統一,這在一般的理論的意義上說,是已經完備了的。在一般的理論的意義上,的確如毛主席所說的,降低了對于政治的要求和降低了對于藝術的要求都是錯誤的,都應該加以反對。但因為在文藝上,藝術與政治這兩方面是有區別,
同時又有聯系的對立的統一的關系,而在階級社會里,在文藝斗爭的實踐上,每一個階級對于文藝都不能不首先關心它的政治和思想的面貌。
政治和藝術、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這是我們對于文藝的經常的要求。但實際上,政治和藝術、形式和內容卻常常不能做到我們所理想的統一。政治和藝術的關系是一種對立的統一的關系。表現在具體作品里,政治和藝水的水平不一致,不平衡以致發生尖銳的矛盾,這是很平常的事,特別是在一個社會正在急劇轉變動的時代。
在一個社會正在急劇的變動的時代,人們對于現實的認識本來便是比較困難的。在社會暫時還比較援慢發展的時代,往往是,一個作家的一生都生活在幾乎同樣的環境里,沒有經歷過一次階級關系和社會性質的根本變化。作家在這里可以從容不迫地觀察他的環境,也可以從容不迫地從事他的創作,但例如我們現在的中國,情形便很不同了,在短短的幾十年里,我們經歷了三個時代,階級關系經歷過許許多多劇烈的變化,在這里,一個作家要想從容不迫地觀察和創作,是困難的。時代是飛快地前進,當舊的還沒有完全熟悉的時候,新的又出現了。為了趕上時代,作家不能不經常鞭策自己,不能不經常試圖盡力用自己的筆來表現那怕自己暫時還不夠十分熟悉的主題,而這,正是目前許多作家在藝術上的成就和他的主觀意圖不相適應的原因。
這是和一般的公式主義傾向應該加以區別的。
我們要求一個作家最好是他的藝術的成就和他的主朗的意圖相一致,但在這樣的時代,往往又需要濟多努力,經過一些時間才能一致。在這樣的情形下,暫時耐心的等待,還是必要的。
在這種情形下,文藝批評如果不首先看取作家要想和這個時代步調一致的努力,即使這種努力暫時還沒有能夠完全相應地反映到他的作品的實際成就里——那么,這種批秤就會成為沒有黨性的脫離政治的學究式的批評。
但是,我們也存在著把政治和藝術完全分離開來觀察文藝劇作的現象,把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作僵死的形而上學的了解,看不到政治與藝術一致是對于文藝創作的經常的要求,看不到政治與藝術之間的生動的不可分割的相互關系。這些人所了解的政治是抽象的表面的,是可以完全離開了藝術的實際成就來孤立地觀察的。一句話,他們只滿足于一些空洞的政治口號,滿足于作者主觀的善良的意圖以及意義重大的題材,等等。在觀察文藝現象的時候,他們完全拋開了政治和藝術統一的觀點。他們甚至把政治和藝術對立起來,好像有你無我,非此則彼,這也是很錯誤的。
二
如果我們根據前面所談到的理解來看我們的爭論,我們應該說些什么呢?
問題也正發生在政治與藝術的關系的理解上。爭論看來是集中在看文藝作品是為了“受教育”還是為了“欣賞”,或者為了“尋求養料”還是為了“尋求消遣”這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最后不能不歸結為政治和藝術的關系問題。
文藝應該成為讀者和觀眾的欣賞對象,應該滿足他們的藝術享受,這是不應該否認的。電影之所以成為擁有群眾最廣泛的藝術,文學書箱所以始終達到一般圖書館全都出借數目的最高比率,就因為藝術和文學能夠吸引人去欣賞,能夠給予人們以藝術的享受。這是文藝的特點,是科學不能具備的,因此最好的科學也是不能代替文藝的。我們不但不應該否認文藝能夠吸引人去欣賞,能夠給予人們以藝術的享受這個特點,而且應該正視它,珍視它。過去在文藝批評上,在創作實踐上,批評家和作家并不是常常考慮到這個問題的,忽視文藝的特征,忽視觀眾和讀者對于文藝應當是文藝這個正當的要求,枯燥無味、生硬的說教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在我們面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應該承認,是“‘受教育坯是‘欣賞,”,“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藝術感粱”等文章,是有它的合理的一面,是反映了相當多的知識青年對于文藝的一種正當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對于公式化概念化以及理論上的教條主義的正當的不滿。我們不應該忘記在這里吸取教訓。
問題在哪里呢?問題在于這兩篇文章都把藝術的欣賞或者“尋求消遣”“受教育”或者“尋求養料”分離以至對立起來。例如“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藝術感染”這樣的提法便是不恰當的。沒有藝術感染力的作品決不是好作品,但是有些有害的作品或者有些作品的有害的部分也是有藝術感染力的,否則這些作品便不能迷惑觀眾和讀者,不能發生壞的作用了。難道我們大家都反對的黃色的作品或者那些充滿小資產階級的情調的作品,沒有藝術的感染力么?如果要談藝術的生命力,那么,首先便應該從藝術和現實的關系去著眼。唯物主義的藝術觀認為藝術應該現實地反映現實,藝術的生命也在這里——真實地反映現突。真實地反映現實的作品,或者簡單些說,在藝術上是真實的作品,它是有思想的,同時也是有藝術感染力的。但是,單單提出藝術的感染作為藝術生命力的標志,是離開了對藝術的真實的要求,也導致離開判斷藝術的政治要求的。
作者的思想也不能不是這樣。他的文章里便曾經這樣說過:“當一部文學作品不能同時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即思想性和藝術性這兩方面的要求——摘引者注)時,應該說藝術性較高的才稱得起好作品”,這是不妥當的。
“是‘受教育還是‘欣賞”?非此則彼,這種提法本身便是機械的。當然,有各種各樣的“欣賞”,黃色的作品也使有些人在“欣賞”,但我們從正確的立場來看,“欣
賞”和“受教育”也不是不可以并立,不是不可以同時存在的。而且恰好中外古今許多好作品都證明這點。“紅樓夢”和“戰爭與和平”,大家都說了不得了,但讀它們的時候,可以是欣賞,同時也可以是“受教育”,可以是“尋求消遣”,同時也可以是“尋求養料”,如果一定要這樣提出問題的話。甚至像“浮士德”這樣的作品,是包含著許多哲學思想成份的,學者們說它有不少辯證法,但因為它到底是藝術,我們看它的時候,可以是受教育,同時也可以是欣賞。使人望而生畏,引不起人的欣賞趣味以及只講趣味,而沒有什么正當的教育意義的作品,都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缺點。
就說是文藝可以使人愉快,可以使人在精神上得到休息這種說法也未必可怕,但是需要加以具體分析。只是強調文藝使人愉快,使人在精神上得到休息,這是不妥當的,但文藝使人愉快,使人在精神上得到休息,這對于我們也是一種作用。大家都知道,魯迅是一向主張文藝要有戰斗性的,他反對林語堂他們認為小品文的特點只在“閑適”。但他也并不否認小品文也可以使人“休息”,但魯迅卻補充說,這種休息正是戰斗之前的準備。因此,在魯迅看來,這種能夠使人休息的作品也并不是和戰斗無關的。
如果我們今天有些作品,也能使我們得到正當的愉快和休息,這也不能說是脫離政治。不,它也是服務于社會主義,服務于我們今天的政治的。
在爭論當中,有些人在強調文藝的欣賞作用文藝使人得到愉快和精神上休息等等的時候傾向于排斥或者輕視文藝的政治思想意義、教育意義,但也有些人在強調文藝的政治思想意義、教育意義的時候卻傾向于排斥或者輕視文藝的欣賞的作用以及使人得到愉快和精神上的休息等。雖然后者并沒有直接否定欣賞,而且表示“并不反對”欣賞,但實際上,他們所理解的藝術的政治性,教育意義等等,和一般的宣傳教育是沒有什么不同的,他們的文章幾乎完全沒有實際估計到文藝的特點,甚至連文藝應該反映生活,應該用生活,用事實來教育讀者這樣起碼的要求也是被他們看漏了的。這表現出了我們青年當中對于文藝問題的另一種傾向。
有些文章都一致把藝術性看作只是技巧或者表現手法等等,它的任務不過是要表達思想,這是拋開文藝作品所應有的豐富的生活和藝術內容,而一心一意地追求赤裸裸的思想,實際上就是追求那些盡人皆知的概念。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公式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曾經是相當流行的。例如,在“新清華”里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話:
“真正的文學藝術作品,其生命基礎只能是思想性。所謂思想性,也就是作品的形象所代表的政治傾向,階級觀點等等”(“思想性——文學作品的靈魂”)。
還有:
“真正的藝術是形式和思想內容的統一體,而且起決定作用的應當是思想內容,形式或者說表現手法也好,只是為了更好表現它的思想,更充分地適應它的思想”(“應該從文學作品吸取什么”)。這兩段話其實都是把文藝作品歸結為思想內容,再加上技巧,或者表現手法、“形象”等等。這實際上正是否認藝術,否認藝術作品的獨特的意義。這和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正相適應的。
但把這些話引用出來,也不是打算很多地責備它們的作者,因為這些意見其實并不是他們自己的創作,他們不過是采取了在文藝批評和文藝閱讀指導曾經很流行過的意見,或者在采用了以后加以改造、發揮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