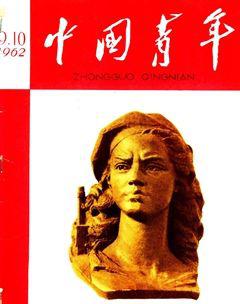勤學苦練攀登藝術高峰
1962-08-16 03:35:56杜近芳
中國青年
1962年9期
關鍵詞:白蛇傳
杜近芳
我——一個在舊社會中出生,嘗過一段舊社會的煎熬,而在新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京劇演員,也是在黨的關懷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整個青年一代的一員。
我從小就很喜歡戲劇。但是我家里很窮,舊社會學戲難,窮人要學戲就更難。在我八歲的時候,我家和一家科班住在一個院里。看到一些孩子在學戲,我非常羨慕。在求得科班教師的默許后,就站在門外做了個旁聽生。我很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學得很用心,不管刮風下雨,常常在門外一站就是一整天。有時屋里的正規生還沒全領會教師的意圖,門外的旁聽生已會演會唱了。我的幾出開蒙戲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學會的。不久,科班解散了,我失去了唯一的學習機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已投到一個封建把頭家里,名為學戲,實際上是洗衣服、擦地板、做飯、管門房。一件事沒做好,就要受到打罵。只有在把頭的女兒要學戲的時候,我才能以“書童”的身分在旁邊陪著練功。1947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了王瑤卿老先生,他看我很用心,條件也比較好,認為是可教之材,表示愿意教我。但是引起了把頭小姐的忌恨。她對我說:“你是陪我學戲的,學了有什么用。我說不讓你演,你用死了心也算白費。”就這樣輕易地奪去了我向王老先生學戲的機會。
以后,我開始了演戲生活。在舊社會,藝術往往只是豪門貴族的消遺品,藝術家也常常是統治階級的玩物。京戲更是如此。擺在一個藝人面前的,是失業、窮困、迫害,以至貧病潦倒而死。……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黃梅戲藝術(2022年1期)2022-05-07 02:00:52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3期)2019-04-02 11:58:36
電影(2019年2期)2019-03-05 08:33:36
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18年4期)2018-04-26 06:21:38
戲曲研究(2018年3期)2018-03-19 08:46:36
考試周刊(2017年54期)2018-01-29 10:04:04
北方文學(2018年2期)2018-01-27 06:29:40
戲劇之家(2017年6期)2017-05-04 09:34:33
名作欣賞·評論版(2016年1期)2016-01-16 09:23:28
東方論壇(2015年2期)2015-12-29 23: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