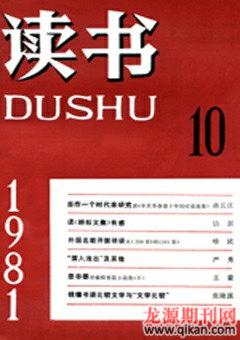1981年第10期,總第31期-海外書訊
《資本論草稿》第四冊,《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草稿摘錄》,馬克思著,日本大月書店出版。
日本《資本論草稿集》編譯委員會編譯的《資本論草稿集》和中峰昭悅、伊藤龍太郎譯的馬克思《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草稿摘錄》均系馬克思《資本論》的準備著作。馬克思自一八五○年后遷居倫敦,研究經濟學,為創作《資本論》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留下幾十本手稿,其中包括一八五七一一八五八年經濟學手稿(共七本)、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手稿(共二十三本)等。
日本出版的《資本論草稿集》,計劃出十五冊,現已出版其中的第四冊。這一冊包括馬克思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手稿的前五本,是根據蘇聯馬列主義研究所和東德馬列主義研究所共同編輯、由東德迪茨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國際版(MEGA)第二部分第三卷第一冊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國際版自一九七五年開始出版,預計一九九○年全部出齊,共百卷。其內容共分四個部分,第二部分即《資本論》及其準備著作。第二部分第三卷包括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手稿,共六冊,第一冊是一八六一年八月至一八六二年三月的前五本手稿。這五本手稿的內容包括資本的生產過程、相對剩余價值和絕對剩余價值,恰與一八五七一一八五八年手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收入新國際版第二部分第一卷)以及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收入新國際版第二部分第二卷)相銜接。
《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草稿摘錄》是根據手稿的影印件并參照蘇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七卷翻譯的,包括手稿的第五本第211—219頁、第十九本、第二十本,內容與上述《資本論草稿集》第四冊相接,均屬“資本的生產過程”這一篇,后來構成《資本論》第一卷的內容。
馬克思一八六一—一八六三年手稿是研究《資本論》成文史的重要文獻。日本出版的上述兩本除國際版和俄文第二版的原注釋外,增加了一些譯注,可作參考。(益民)
《帝國主義,干涉和發展》(Impe-rialism,Intervention and Develop-ment),安德魯·馬克,大衛·普蘭特及烏爾蘇拉·道伊爾(AndrewMack,David PlantandUrsulaDoyle)編,倫敦克羅姆·海爾姆圖書出版公司(London,CroomHelmLtd.)出版,393頁,4.95英鎊。
這本國際政治論文集初版時曾以《東西方、南北方:干涉,發展和帝國主義》的書名出版。所收論文的作者大多是英美二國研究當代國際政治的專家或學者。他們多年來經常在英美一些重要報刊上發表理論性較強的文章。
本書在再版時,編者從初版中刪去五篇論文,另外補充了史密斯等撰寫的四篇論文,并以“第三世界的貧窮和西方國家”為題,作為新版論文集的第六章。
編者在引言中指出,這本論文集“除了闡述戰后東西方之間的沖突和對抗之外,更重要的是論述南北方,也就是富裕的工業化國家和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的分歧和斗爭。”
全書共分為二大部分和八個章節。第一部分著重分析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進行經濟滲透和軍事擴張所采取的不同手法,指出第三世界各國人民戰后紛紛要求擺脫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他們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旗幟下,團結起來,向新老殖民主義展開了斗爭,針對戰后第三世界人民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新殖民主義者不得不變換手法,采取更為隱蔽和狡猾的手段來干涉和破壞方興未艾的民族獨立運動。作者指出,對第三世界的政治干涉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在新的條件下的客觀需要,干涉與反干涉的斗爭必然要延續很長的時間,而且是構成國際局勢動蕩不安的主要根源。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編者選用了S·M.密勒在《社會政策》雜志上發表的一篇論文:“美國經濟需要帝國主義嗎?”,作為全書第一部分的一個總結。
第二部分共分四章,著重論述第三世界長期處于不發達狀態的社會原因,指出帝國主義的干涉和掠奪是阻礙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第三世界人民日趨貧困化的根源,并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分為“非洲次沙哈拉地區”、“拉美地區”和“南亞地區”等三種模式,進而就世界人口的膨脹是否必然導致糧食危機的問題展開了爭論。
最后一章選用了渥德瓦德和布拉杰爾撰寫的兩篇論文:《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探討》及《中國與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關系》。作者指出中國在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對第三世界各國具有深遠的影響,并認為中國在改造舊的經濟基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過程中所創造的許多方法,對第三世界也是十分寶貴的經驗,可以作為他們發展本國經濟的有益借鑒。(炳
《中國的現代化與法;法學家所見之中國》,加藤一郎編,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年出版,387頁。
本書收入日本人類環境訪華代表團(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二十八日)成員歸國后寫的二十三篇文章。該團成員共十八人,多為從事法學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律師,他們在北京、上海、南京和武漢等地參觀訪問,同我們法律工作者進行了座談,旁聽了法院的開庭審判等情況,本書收入的文章多為見聞錄和感想。
所有文章一致認為,中國自打倒“四人幫”后,總結歷史經驗,恢復法治,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設置司法部,是值得慶賀的。律師木宮高彥說,中國對外國人采取開放政策,允許外國人旁聽公審,允許拍照、錄音,這比日本的法院還開放;這充分表明中國追求公正審判的愿望和對法治事業的自信。東京大學法學教授加藤一郎說,在法學研究所座談時,中國方面介紹了目前對民法和經濟法的三種分歧意見,介紹人還坦率地講出他個人的意見,這在中國是沒有先例的。
在一些文章中對中國的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審判制度等方面,也發表了個人的意見和感想。加藤指出,中國的法律條文不夠詳細、嚴密,如在刑法第七十九條上規定,凡無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可根據最類似的條文定罪科刑。這在日本是行不通的,因為法律上無明文規定的就不構成犯罪。律師伊藤淳吉說,審判的依據有時不夠明確,尺度太抽象,可能會產生掌握標準上的不統一,難免出現誤判。但他又指出,從江蘇省的情況來看,一年受理的民事案件只有八千件(日本多達一百四十萬件),其中離婚案和房產糾紛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因此其他無法可依的案件并不多,矛盾不嚴重。伊藤談及審判制度時說,日本過去也有陪審制度,但后來取消了,現在又有人要求恢復,這是值得研究的。關于辯護制度,有不少文章都提出了問題,認為目前中國的辯護制度不夠健全,不能令人滿意。木宮旁聽了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的開庭審判后說,在法庭調查過程中證人的供詞和被告的供詞有出入,但竟無人提問,律師一語不發。但他相信,在這一方面今后會有改進。
多數文章中認為,對中國的法律和審判制度不能用日本的法律來衡量,制度不同,法律體系自然也不同。中國的法律存在一些缺點,但是次要的,首先應該看到中國正在致力于法治,這是一大進步。
(益民)
海外書訊
益民/炳炘/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