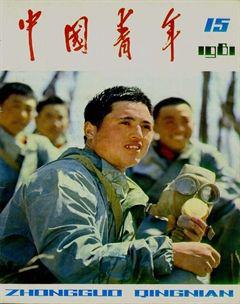堅定地實現戰略轉移
牛欣芳
《戰爭和戰略問題》是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結論的一部分。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具體分析中國革命所經歷過的歷次轉折,指明了戰略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意義,闡述了必須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實行戰略轉移這一重要思想。這篇文章既是研究戰爭和戰略問題的軍事著作,又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學習毛澤東同志運用哲學原理來分析制定革命戰略的觀點和方法,對于我們今天加深理解《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于認識三中全會以來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正確性,都有現實的意義。
在這篇文章里,毛澤東同志概述了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這兩個過程的四個戰略時期之后指出,這之間共存在著三個戰略轉移——“第一個,國內游擊戰爭和國內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二個,國內正規戰爭和抗日游擊戰爭之間的轉變。第三個,抗日游擊戰爭和抗日正規戰爭之間的轉變。”接著,文章具體剖析了這些戰略轉變的復雜情況,強調指出,我們黨只有實現并完成這些轉變,“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即才能同客觀形勢相符合。
客觀形勢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革命黨人只有隨時從實際出發,適應新的形勢,才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凡清醒認識形勢的變化并及時轉變了自已的戰略任務時,革命戰爭就節節勝利;凡認不清形勢的變化而沒有隨之轉變戰略任務時,革命就遭受挫折和損失。抗日戰爭爆發后,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我們黨抓住了這個變化,及時進行戰略轉變,確定了團結國民黨抗日的政策,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同時,對地主階級的政策也相應地作了轉變,由打土豪分田地,改變為減租減息。這個戰略轉變,保證了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解放戰爭中,當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即將被打垮,全國大陸即將解放時,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及時地指出,從1927年開始的用鄉村包圍城市,工作重點在鄉村的時期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新時期。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解決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將成為主要矛盾,由此提出了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提出了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要求全黨同志的思想轉向經濟建設,完成新時期的新任務。這就保證了我們的國家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在各條戰線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根據變化了的形勢來重新確定自已的戰略任務;這種轉變不是自然而然或輕而易舉可以實現的,它是對革命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個嚴峻考驗。那么,從思想方法上說,怎樣才能正確而及時地實現戰略轉移呢?根據毛澤東同志的一貫教導,應該注意以下三點:
首先,要求人們具有發展地看問題的觀點。不少同志會講“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之類的話,但他們不懂得,這個“實際”是在不停地發展變化著的,是個動態的概念。客觀實際的存在是一個過程。在發展的全過程中,由于性質的轉變而構成階段性。如果把“實際”看作僵死的,固定不變的,就不可避免地會違背從實際出發這一馬列主義的原則。這一方面,我們黨對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的實際的認識,是有嚴重的教訓的。當時,國內階級關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基本消滅,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得到基本解決。我們面臨的新情況是人民要求迅速發展經濟、文化來滿足生活的需要。因此,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要求我們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黨的八大正確把握了這一變化,作出了把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生產建設上來的決定。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惜,這個偉大的戰略轉移沒有能夠實現。究其緣由,因為我們黨長期生活在復雜、激烈的階級斗爭環境中,從建黨的那天起,一直搞階級斗爭。我們的黨員和黨的領導者,熟悉于搞階級斗爭,習慣于搞階級斗爭,而當著階級斗爭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再是主要矛盾,需要著力于經濟文化建設時,許多同志的思想認識就沒有跟上這今新形勢,還停留在已成為過去的舊階段里。
其次,要求人們具備全面地看問題的能力。整個形勢發生了質的轉變之后,仍會殘留著舊階段的某些社會觀象,這就要求人們弄清楚形勢的全貌,而不能把小范圍存在的現象夸大為大部甚至全部。1956年以后,我國社會進入了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已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階級斗爭確實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這種現象,在一個剛剛結束了幾千年階級對立的社會中,本不奇怪。但黨內的一些同志被這些現象迷惑,夸大起來,以偏概全,影響了自已對整個形勢的觀察,甚至推翻了黨的代表大會上正式通過的關于實現戰略轉移的決議。隨后的十多年,更是愈演愈烈,不僅認為階級斗爭是主要矛盾,是“綱”,而且認為貫穿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就導致了全局性的長期錯誤。
再次,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不能抓住片言只語,生搬硬套。社會主義實踐是開天辟地的新業績,遇到的新矛盾、新課題層出不窮。面對從未見過的新形勢,只能系統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幫助我們思考、分析,從而創造性地制定新的戰略任務。但我們在一段時期內,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把他們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內對社會主義社會某一特征的描述,搬用到我國的現實中來。在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我們沒有依據新形勢來實現戰略轉移,反而離開客觀實際越來越遠,從學風上找原因,就是由于陷入了“本本主義”。
黨的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這是在新時期運用毛澤東思想重新實行戰略轉移,也是二十多年來幾經折騰、慘遭失敗所換來的寶貴教訓。正如《決議》總結的那樣:“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歸根到底,就是沒有堅定不移地實現這個戰略轉移。”然而,即使在問題已如此明確了的今天,仍有一部分同志不清醒、不理解,懷疑黨中央的這個決策“右了”、“倒退了”。他們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舊觀念難舍難分,對聚精會神搞四化三心二意。毛澤東同志在文章中指出過的“由于干部對已經變化的敵情和任務估計不足而發生的”不愿實行戰略轉變的情形,又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當年黨中央“曾經做了艱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漸地轉變過來”。我們應該記取全黨全國人民以重大代價換來的經驗教訓,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提高認識,堅定地實現這個偉大的戰略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