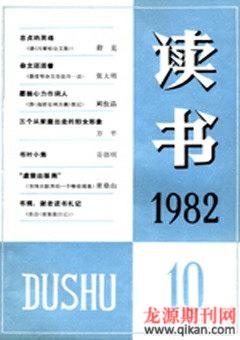學如富貴在博收
劉宗漢
讀《選堂集林·史林》
近代的史學家往往是很博學的。王國維在甲骨金文、宋元戲曲、西北地理、文藝理論等各個領域的成就,都是大家所公認的。陳寅恪的魏晉隋唐史的研究,成就當然是巨大的,但他的研究領域遠不限于此,晚年寫的《柳如是別傳》就是研究明末清初史事的。陳氏對佛道二藏有較深的造詣,我們看他在《柳如是別傳》中廣引釋道典故箋釋錢牧齋的詩句,真是叫人嘆服。博學,是一個歷史學家取得成就的重要條件。
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所著的《選堂集林·史林》是一部有多方面成就的、題材廣泛的史學論文集。這是一部淵博的著作。從時間角度說,它幾乎涉及了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時代,從史前(如《有虞氏上陶說》)、先秦(如《由卜兆記數推究殷人對于數的觀念》)、秦漢(如《新莽職官考》),歷魏晉(如《安荼論
博學,不等于沒有特色。《史林》在博學中又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
長于敦煌學,對敦煌遺書中釋道經典進行考釋,是《史林》的一大特色。
研究道教史的學者,都會很熟悉《老子想爾注》。這原是被斯坦因劫走的敦煌遺書中的一種,久藏英倫,直至一九五六年饒宗頤先生刊《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才得問世。《校箋》刊布后,在國際上得到很高的評價,法國巴黎大學東方學院道教史研究班甚至把它刊為教材。收入《史林》的《老子想爾注考略》,是作者繼《校箋》之后又一研究《老子想爾注》的著作,對于研究道教史同樣是重要的。
敦煌遺書中有一個宋初人用十一曜推人流年的批命本子,叫做《靈州大都督府白衣術士康遵課》。十一曜出《聿斯經》,但研究《聿斯經》并撰有《都利聿斯經及其佚文》(刊《東亞文化史叢考》)的日人石田
同樣,饒宗頤先生對敦煌遺書中的佛教典籍也做了非常有價值的校理研究工作。唐德宗貞元八——十年(公元七九二——七九四年),在吐蕃曾發生過一場我國僧人摩河衍與婆羅門僧人蓮花戒關于佛教教義的辯論。這場辯論在漢文史籍中了無痕跡,后期藏文資料雖然談到了這場辯論,但因為夾雜著傳說,令人難以置信。在敦煌遺書中有一部唐人王錫撰的《頓悟大乘政理決》(p4646、s2672),記述了這場辯論,證實了它的歷史真實性。饒宗頤先生將《頓悟大乘政理決》的兩個寫本作了校勘,這就是收入《史林》的《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記并校記》。同時又對摩訶衍其人及辯論的時間進行了研討,寫成了《神會門下摩訶衍之入藏兼論禪門南北宗的調和問題》和《論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兩篇文章(均收入《史林》)。關于這場辯論的年代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關鍵在于吐蕃攻占敦煌的年代不易確定。以往,學者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應用的大多是典籍中的文獻資料。然而作者思路廣闊,根據敦煌遺書用唐朝紀元的資料終于七八七年,有吐蕃紀年的資料始于七八八年,再參以其它文獻,確定了敦煌陷落在七八七年,并進而確定了這場宗教爭論發生在七九二——七九四年。這種說法雖然是法人戴密微首先提出來的,但是是作是最后論定的。于此,可見思路寬廣對一個歷史學家的重要性。我國學者張廣達撰有《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有關的敦煌文書》(刊《學林漫錄》三集),羅列國外對這場爭論的研究成果甚備,但未及饒先生的《頓悟大乘政理決》校本和上舉兩篇論文,讀《史林》可補張文之闕。
《史林》中收有不少研究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史的文章,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用梵文文獻和漢文文獻互相比較的辦法來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問題。請看下面一例:
中國儒家經典有一套傳統的注釋方法,大體是:
西漢傳經主于誦習而已,其訓故惟舉大旨,記說或非本義,但取通義,不尚多書:此秦燔后經學之權輿也。逮后漢廣為傳注,然后語必比附經文,字承句屬,靡有漏缺,至魏晉而解又大備:此既傳后經學之宗旨也。洎宋齊以降,則多取儒先傳注,條
對于宋齊以降產生的經疏學,近代學者中有人認為它是受佛教影響產生的。牟潤孫先生甚至寫過一篇題為《論儒釋兩家之講經及義疏》的文章,認為“義疏”是經生仿照佛徒講經時的“講義”或“記錄”。這種觀點在海外有很大的影響。
饒宗頤先生不同意這種說法,他指出:產生這種說法的原因,在于“對彼邦經疏之體例,仍未深究”。他說:
佛家經疏沿襲自婆羅門,故論梵土經疏之始,非追溯至吠陀分(Ve—dānga),無以明其原委也。婆羅門經與佛教經書性質又略有不同。釋氏書原多不稱經,佛徒漢譯,附以“經”名者不一而足,乃借漢名以尊重其書。婆羅門之經(修多羅)大都為極簡質之語句,非有注疏,義不能明,故經與疏往往合刊。又其注疏之體裁,每因對話方式,假為一問一答,究元決疑,覃極閫奧,亦與漢土經疏不盡相同。
華梵經疏體例既“不盡相同”,漢土的“義疏”自不能源于梵土。
至于儒家講經和“義疏”也在漢土自有淵源。最早的“義疏”,是南朝宋大明四年皇太子撰的《孝經義疏》。據饒先生的考證,當時所謂“義疏”,實際上是漢以來傳統經注的一種延續,與佛經無涉。至于講經,在西漢即已出現,并不是受佛徒講經產生的。佛徒對經生的影響只是在講經形式上的雷同及疏體文字撰寫上“日趨深蕪”而已!
上面的論述見于《史林》所收的《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饒宗頤先生對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這樁公案,解決得很圓滿,其得力處全在于他通曉梵文,能夠直接閱讀梵文本婆羅門經典和佛教經典。
饒宗頤先生是廣東潮州人,青年時代即關心桑梓文獻,曾補訂《潮州藝文志》,刊于一九三七年的《嶺南學報》。因此,研究廣東地區的歷史文物,也是《史林》的特色之一。作者筆觸所及,廣東的歷史、人物,民族、考古,均有精到的論述。這里只舉一個例子:
廣東潮州地區很早以前就有人類活動的蹤跡,在這方面,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已經做了不少的考察和研究。但容易被人遺忘的是,潮州地區第一篇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報告是饒宗頤先生撰寫的。這就是《史林》中的《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這篇文章敘述了韓江流域史前遺址的外貌,描述了當時采集到的新石器和陶片的特征。這在《史林》中為別格,但它卻說明作者熟悉考古學的方法,而這對一位史學家來說,顯然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饒宗頤先生對東南亞華僑史的研究。饒先生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任教時,曾注意訪求新加坡、馬來西亞一帶的漢文碑志,輯成《星馬華文碑刻系年(紀略)》(收入《史林》)。所錄碑文,上起明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的《黃維弘墓碑》,下迄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年)的《重建香山會館捐題小引》,共近百通,為我們研究新、馬地區的華僑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另外,《史林》中的《三教論及其海外移植》一文,博考三教論的源流,并論述了它在東南亞華僑中的影響,這對于國內的讀者來說,讀來也是耳目一新的。
饒宗頤先生除考史外,兼工倚聲。《史林》所收《蘇門答臘島北部發現漢錢古物記》一文中,有一首詠印度尼西亞萬隆復舟火山的《念奴嬌》:
危欄百轉,對蒼崖萬丈,風滿羅袖。試撫當年盤古頂,真見燭龍噓阜。薄海滄桑,漫山煙雨,折戟沉沙久。巖漿噴處,巨靈時作獅吼。只見古木蕭條,斷槎橫地,遮遏行人走。蒼狗寒云多幻化,長共夕陽廝守。野霧蒼茫,陣鴉亂舞,衣薄還須酒。世間猶熱,火云燒出高岫。
近代中國詞人詠域外風景的,首推呂碧城女士,但讀了這闋《念奴嬌》,轉覺《曉珠詞》中所作,有些失于纖秀了。
宋人蘇東坡說:“學如富貴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在淵博中有自己的特色,在特色中又處處見其淵博,這就是《選堂集林·史林》給讀者的印象。
(《選堂集林·史林》,饒宗頤著,全三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八二年一月第一版,港幣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