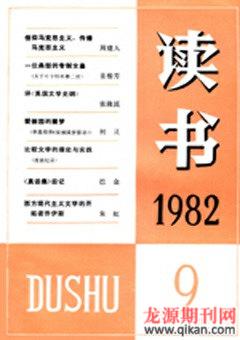美好的回憶和良好的祝愿
何金銘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五十周年紀念,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由《讀書與出版》雜志發起的“學習合作”活動,去年三月《讀書》三月號上湖南向華樹同志也談到這些活動,這都勾起我對往事的美好回憶。
那是個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正迅速走向勝利。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巨大影響,深入到從大中城市到窮鄉僻壤的祖國大地。生活在尚未解放地區的知識青年,通過多種渠道,感受到大時代的脈搏,接受了革命理論和進步思想的熏陶,一個個先先后后地擺脫了家庭的束縛,學校的禁錮,投身到迎接新中國的戰斗隊伍中來。我是那時這樣的千百萬知識青年中的一員。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我剛滿十四歲,才進入初中,政治上還十足是個糊涂蟲。引我從愚昧達到啟蒙,從荒謬接近真理的,首先是黨領導的解放大軍的正義反擊和勝利進軍,是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卓越努力,而進步書刊,特別是《讀書與出版》、《中學生》和《開明少年》三個雜志,也是我忘不了的良師益友。
那時,《讀書與出版》發起了“學習合作”,《中學生》也辟有“中學生的朋友”一欄,我在這兩家雜志上都刊出了希望同愛好文藝的青少年交朋友的自我介紹。出乎意外和使人振奮的是,很快,就有幾十位青少年朋友寫來了熱情洋溢的信。在一年多時間里,和我通信較多、筆談較深的,有上海的茅行健、朱培明,湖南的周衍權、朱正,開封的王恕茵,廣東的謝洋,江蘇的邵恬,福建的黃端楷,西安的李平等十幾人。他們多數是大、中學生,也有失學失業青年。我們的書信往來,不僅在學習上互切互磋,而且在思想上互相幫助,因而成了我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些被禁止的進步書刊,通過郵件而互相傳閱。在江蘇某圖書館工作的陳濤,曾把《馬凡陀的山歌》寄給我。李平從他的通信朋友處得到《王貴與李香香》,也拿給我看。我們還互相寄送了油印、鉛印或手抄的進步刊物。
反動派倒行逆施,人民英勇斗爭的消息,通過書信告知給朋友們。上海浙江大學學生抗暴的事跡,以及反動派迫害學生的真情實況,就是朱培明寫信告訴我的。
對于天下大事的討論,是我們筆談的重要內容。記得一九四七年間,生活書店曾編輯出版過《世界政治手冊》,我函購好久,遲遲不見寄來。忽然報上有消息說:恢復郵電檢查。我同茅行健通信中談到這件事,他說:“真令人長嘆也!”我說:“扼殺文化的工作越做得明目張膽,憤怒的種子越埋得深,其結果如何,是不言可知的。”
筆談還涉及到人生觀、戀愛觀、文藝觀等問題。那時學校中封建主義的東西很多,男女同學一般極少有正常的往來,稍一接近,就被認為是“戀愛”,或者“胡鬧”。我同王恕茵等在通信中,都批評了這種現象。大家說,時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竟仍然流行著清朝的觀念,實在令人難于容忍。
我的通信朋友中,有好幾位小學教師。書信中談到的教師生活片段,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邵恬教自然課,小朋友問蕎麥到底是什么樣,難住了他,因此要我寄一穗去,讓南國中人也見識見識。程潛波教語文(不記得他是哪省哪市了),有幾個得意學生,特別寄了他們的習作來給我看。向華樹同我討論過教師的職責問題,我們在信上交換過這樣的意見:“教育事業同祖國前途有密切關系。教師要認清這個時代,至少也不應該把腐臭的思想灌輸給青年。他應負誘導之責,而不應以嚇打為教導對策。要記住,自己在學生時代所遭受的不合理,所感到的痛苦,千萬不能重演在更年青的一代身上。”
這個通過書信進行“學習合作”的活動,不僅由《讀書與出版》雜志發起,也得到了她的指導。事實上,《中學生》和《開明少年》也起了指導作用。通信朋友們都是這幾個雜志的熱心讀者,一些人還為雜志寫了不少稿子。編輯同志在給我們的回信中,常常推薦一些好的書籍,有時還介紹一些青年朋友。《讀書與出版》為“學習合作”辦了“國文班”專欄。孫起孟和魏金枝先生對我的一篇習作的評改,使我受益很深,久久難忘。我是在一家書店里看到他們的評改文章的,他們勸我寫文章“應該特別在穩實兩字上用功夫”,我把這句話記在了日記上。
這種頻繁的書信往來,后來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遭到了迫害。我曾收到一封匿名恐嚇信,說什么如果對言論行動繼續不加檢點,就要“以一粒子彈奉送,勿謂言之不預也。”個別朋友遭到逮捕。當然,這種威脅和迫害并不能達到它的預期目的,許多參加“學習合作”的青年朋友,在讀書與實踐中,提高了政治覺悟,更加堅定了跟著共產黨走的決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