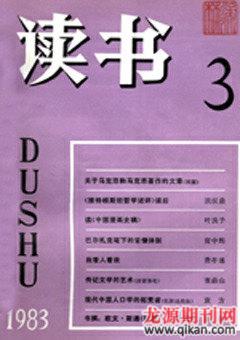時間的歌
鄒荻帆
《呂劍詩集》斷想
一
我跟呂劍說,我們是幾十年的朋友,也讀過你幾十年的詩,感情驅使我對你一定要說幾句話,可是我確實不善邏輯思維。后來我找了一條藏拙的辦法,仿照古人的“詩話”來寫上幾句。這決非貶低古人的“詩話”,而是說我想學,而所學的僅是其皮毛。呂劍也認可了。
我說幾十年,是指從抗日戰爭初期,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到全面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的四十來年,而呂劍詩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他的思想感情在這四十來年的大變革中,不論“雷雨天也罷,大雪天也罷”,他祝愿石竹開花,“常常閃爍”在他的夢中。這就是對家鄉(祖國)的祝愿,人民的祝愿,詩的祝愿。
我總認為,詩歌應有時代的脈搏。翻開一本詩集而不能感到詩人的心是在哪一個時代跳動,為我所不取。
我還認為,一首詩總應有一點在現實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告訴讀者。它區別于其他文藝表現形式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更強烈地以詩人的感情向讀者談心。感情要真摯,而感情的是否崇高偉大,終究取決于詩人是否抒了人民之情。
我以為呂劍是努力這樣做的。
二
翻開《呂劍詩集》(下簡稱《詩集》),令人驚心地看到從一九五七到一九七八年,有二十年的空白。二十年沒有聽到詩人唱自己的歌,二十年窒息了詩人的呼吸。不是詩人交了白卷,而是被勒令退出了試場。
今年十月,我同呂劍一道去武夷山訪問。當地的一位蛇醫告訴我們,武夷有還魂草,可以封閉在石墻里經二十年再取出,給以水分陽光,仍然可以綠葉復蘇。而《詩集》中的《六十自詠》寫道:
相信二十年決沒有白過,
不能只看經歷了多少頓挫。
額上增添了幾重沉思的皺紋,
因襲的古堡就是攻破了幾座。
盡管作者擱筆二十年,時間的烙印在額上增添了皺紋,呵,注意,這是“沉思”的皺紋,因為有“沉思”,這“沉思”的不只是作者,而是千千萬萬人,因而那些被攻破的因襲古堡也不只反映于詩人的額頭,也深深印入千千萬萬人的心中。二十年決沒有白過。于是我體會了“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那決不是只是指三年長的時間,從語言文字等技術上下了多少工夫,而自憐地吟詩流淚,更重要地是三年辛酸生活中,提煉出兩句,用這兩句來說出他的所有的詩創作的辛酸,而成為“生活的課本”。
三
在南方的旅程中,呂劍談到他過去的詩時(指的是他早年在抗日戰爭期中的詩),他對那些作品給予否定,似乎不值一提。這種情況是常有的,作家往往在此一時期,否定他自己彼一時期的作品。我們搞文學評論研究工作的,也往往容易在今天否定昨天的作品。
我想起馬克思把希臘神話稱為不可企及的高峰,我看,馬克思不是說今天的作家在今天寫不出那時代的思想與藝術的作品,而是放在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準衡上,那是不可企及的。物質文明、思想發展到了今天,你來寫那個時代的神話,那算什么樣的“靈魂的工程師”呢!
提希臘神話,那是太遙遠的年代的創作了,而談中國新文學從五四運動算起,這是應從各個時期的創作中總結經驗的。
我扯遠了,我意是在說明呂劍在早期有一些詩是給了我深的印象的。其中如潘梓年同志早年曾在茅公主編的《文藝陣地》上著文介紹過的《大隊人馬回來了》。
還有《打馬渡襄河》。我記得我是在一九四一年編《詩墾地》時,冀
七百里風和雪,
我向東方,
打馬渡襄河。
這里既寓意著走向抗日前線,而東方,又寓意著朝陽、黎明、春天、新時代,在那時代人們多么熱望新時代到臨,多么憎惡國民黨統治區的黑暗。因而
趕著春天去,
去豐收一個秋天。
充滿著希望、朝氣、青年的銳氣……呵,這些可能是六十來歲的呂劍不能再寫出來了的,而再寫一首打馬渡襄河,又豈非是可笑的事。這首詩使我想起古詩“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它有著那種激情慷慨。而時代不同,這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特定的時間和環境下,一首有鼓舞力的詩。
《大隊人馬回來了》寫的是人民的子弟兵回來了,在那個時期出現于白區的報紙上,是多么令人興奮的事,詩中有幾行寫道:
告訴老楊,
快去烏龍山,
給游擊隊報個信,
說咱們的
大隊人馬回來了!
我想,當新四軍、八路軍正在前方和敵后展開英勇戰斗時,有詩贊頌他們,很好!另外,白區的詩人作家在國民黨統治區能突破封鎖,發出對人民子弟兵的歡呼,也需要勇氣與激情,這是文藝戰士們的特殊的“游擊戰”。
一個時期的詩,不要輕易否定。
四
讀著《詩集》,大體上感到他基本上是采取了自由式,沒有嚴格的腳韻。甚至,有些形式很整齊的詩,讀來也不覺得被形式所束縛。而且從他的某些詩看來,成為他的代表作的,正是幾篇自由體詩。如前面提及的兩首,以及《詩集》的壓軸作《故鄉的石竹花》,還有《復仇》、《不要忘了他們》等。
但是,我又從他的一些有較整齊的形式的詩中,看到作者在中外古今詩歌中汲取的營養。譬如說,當他行走于內蒙草原而寫的《八個姑娘》,都是四行一節,寫了她們颯爽英姿,結尾時寫道:
兩個騎著云青馬飛奔向東,
兩個騎著沙栗馬飛奔向西,
兩個騎著棗騮馬飛奔向北,
兩個騎著丁香馬飛奔向南。……
這很快使我聯想到古詩:“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但是,時代不同了,這八位蒙古姑娘是在旗委會學習后,“要把北京的福音傳到草原”,“用歌唱般的聲調互相道聲再見”,而后奔向草原四方。給我們帶來的是草原春色。
《羊城留別》,也使我聯想到杜甫的《贈衛八處士》,杜詩有:“少壯能幾時,鬃發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但是,當“四人幫”已粉碎,而政策尚未落實,冤案尚未昭雪,兩個“凡是”還束縛著人們的思想之際,作者留別友人寫道:
有的故人已經含冤而死,
而生者也都已鬢發蒼蒼。
對于死者何以為之招魂?
生者何以依然緘口未唱?
比之杜詩又有絕大的不同,鳴響著我們這時代的聲音。
甚至《等待啊,追尋啊……》,使我聯想到何其芳的《預言》。《什么時候你來呀》使我聯想到西蒙諾夫的《等著我吧……》。而《等待啊,追尋啊……》是在粉碎“四人幫”后,作者充滿愛情等待真理之聲,追尋光明幸福之道。《什么時候你來呀》是在抗日戰爭出現陰霾的時刻,呼喚人民的旗幟上升。
我前面所提的幾首詩都是形式整齊,音韻有致的。也是好詩。而讀來并不感到形式與韻律的存在。
那么,怎么跟我說的那幾篇代表作聯得起來呢?于是我體會到正因為作者很好地學習了中外古今的名詩,鑄一爐而冶之,于是得到了更大的自由。沒有好的學習,則不善于創造。袁枚的《隨園詩話》中,主張性情,而不受韻的約束。他說:“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我想,忘記了形式有兩層意思,一則是不受形式的束縛;一則是運用自如,雖有某種形式,而達到“自由的王國”。總之是為了詩更好地表達詩情。何況我們是要更好地使形式也隨詩情而發展。
五
但,這也會有一些副作用的,有時可能由于錘煉不夠,而使詩有散文化傾向。于是在學寫詩的青年人中,產生兩種傾向,以為押了韻就是詩;或者以為散文分行就是詩,而不押韻是當今的風尚。這都是誤解。
老詩人也可能由于邏輯思維力較強了,而當生活感性還不足時,或者感情還不達到白熱時,或者藝術地加工錘煉還不夠時,或者匠氣加工而造作痕跡顯露時,也都會使詩散文化,只有直白地敘述與說理。
我不是說這《詩集》里已有某幾篇有這傾向,作者還是精選了的,而是我們要共勉。在這本《詩集》中,也有幾篇顯得平淡,而未能給我留下深的印象。
六
從《我的村莊》到《故鄉的石竹花》是三十六年時間。作者在《我的村莊》中勾畫出了在四十年代初期中國農村衰憊的圖景,土地是那樣磽薄,人民是那樣窮困,然而:
但我們村莊也是個驕傲的村莊,
你以無比的勇敢參加了戰爭;
子弟兵為保衛自己的村莊,
慷慨地交出了自己的性命。
結語上還寫著:
我的村莊呀,你又是多么光榮,
你要在廢墟上建起新的房舍;
無情地和你的過去告別吧!
你要走上世紀的新的方向!
作者懷著熱愛和希望,在四十年代抗戰末期的陰霾中,人民處于水深火熱時寫了這首詩,那個年代,正如他的《斷章》中的佳句所寫的要復仇的人們:
要想殺掉敵人,
高粱葉也可當刀。
時間推移到八十年代初,詩人已從青年時代的熱情幻想,進入到深情的沉思。而我們的國家一方面是開創了人民民主專政的萬世的基業,而另一方面在前進中也不可免地遇到礁石和暴風,應該說《故鄉的石竹花》一詩也達到了作者的藝術的高度。他在《春天!春天!》一詩中,以“春天”的回答寫道:
讓東風盡快將柳條染黃,
讓鴨群嬉戲湖水乍解的漪淪,
讓歸燕呢喃早花的初放,
讓萌芽趁著時雨破土而出,
讓人們心中亮出復蘇的歌唱!
石竹花一詩中,沒有很多地寫春天帶來的希望。但是,我們閱讀一個詩人的詩篇,是不能只從一篇而概百篇的,要看到他的詩的軌跡。詩人在寫故鄉的石竹花中,寫的是石竹花,而實際作者是寓花于故鄉的土地、鄉民,乃至祖國、人民,詩人與詩。
故鄉的石竹花,
聽著送糞運草的獨輪車的呻吟聲,
聽著手拔蒿艾的婦女們的太息聲,
聽著牧者趕羊時吹的悒郁的牧笛,
聽著父親下地時唱的蒼涼的土戲,
從夏到秋,一直開不敗,
點染著我們寂真的山野。
作者還回憶到自己在家鄉的簡陋的小學,曾摘過它夾在課本里;想起母親的白發,想摘一朵而插到她的鬃邊;都加深了對石竹花的愛情,對故鄉的深情,因而水到渠成。詩人沉吟著說:
你可知道,你可知道,
雷雨天也罷,大雪天也罷,
遠方有一位你的早年的朋友,
日日夜夜地默禱你的來日嗎?
這也就是前面所說的石竹花的寓意。顯然,這首詩比他的《我的村莊》在藝術上是更前進了,不象《我的村莊》所寫的比較單純。
……啊,似乎我該修改我的意見了,《故鄉的石竹花》好象是一首形式較整齊的詩,你看第一節以二行開始,最后一節以同樣二行結束。中間有七節,又每節都以“故鄉的石竹花”開始,每節都是七行,這不是很整齊的格律詩嗎?但是,我應該告訴讀者,我初讀、再讀都沒有感到它的格律的存在,使我忘記它有任何整齊的形式……啊,啊,這是作者的“自度曲”,是作者自創的一種自由而整齊的形式,這也是他的藝術上的功力吧!
(《呂劍詩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第一版,0.5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