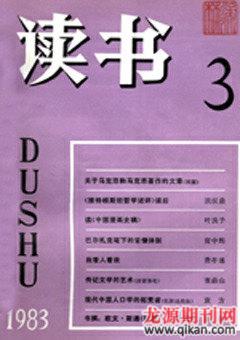《相聲藝術與笑》
姜 昆
有不少業余相聲作者,他們很喜歡創作相聲,但由于沒有掌握致笑的規律,寫出的作品總是逗不樂人家。我就收到過不少這樣的作者的來信。有些信里還提出,干脆由他們寫作相聲的情節,由我來給添“包袱”。每逢見到這樣的信,都使我汗顏萬分。我雖忝列于相聲作者之林,可不是開包袱公司的:各色貨物齊備,拿出一個隨便往那兒一套,聞者立即粲然。但是來信者的殷殷期望,又使我不能敷衍。于是只好在回信時,自以為是地胡“哨”一陣包袱的寫法和規律,但常常是寫著寫著,連自個兒也糊涂起來了。從主觀上說,是我在這方面畢竟沒有什么研究,所以說不出個子午卯酉;從客觀上說,這方面還從來沒有人加以歸納,上升為理論的,所以無可遵循。
王力葉的《相聲藝術與笑》,彌補了這個不足。它以“主要篇幅著重闡述相聲中的笑料即‘包袱兒,以及相聲笑料的基本因素和笑料構成的各種方法,并舉例加以說明”。我以為,作者從相聲研究出發來探討笑的規律,作出的嘗試是開創性的。它起碼是使我,受益不淺,因此,我很想把它推薦給從事相聲寫作的伙伴們。
相聲中的“包袱兒”,老先生們講它時,總告訴我們要掌握“筋勁兒”,“抖包袱兒”時要注意話音的“尺寸”。只有“寸”住嘍,才能“抖響”嘍。可惜的是,這么幾句話,只有內行人,或是老北京、老天津人才能聽明白。離開京、津這塊地兒再講,就跟中國電影里講的外國話似的,中國人外國人都沒人能聽懂。實際上,這也說明了相聲理論研究的薄弱。
相聲屬于市民文學范疇,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據現在掌握不過一百年左右(見侯寶林等著《相聲藝術論集》)。從事相聲藝術的演員,舊社會幾乎全是沒有文化并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解放以后,有相當文化水平的人也是屈指可數。老一輩留給我們的相聲腳本比較豐富,而理論方面,則幾乎是個空白。從歷史上形成的相聲師承方式——口傳心授,就說明了這一點。這種情形,嚴重地影響了相聲創作的繼承和發展。長期以來,大多數相聲演員走的創作道路,一直是“單干”或“自產自銷”。這就造成了對于包袱的組織方法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有人云亦云的,也有別樹一幟的。同時也產生了這樣的現象:同一個相聲中的例子,這人說是“順水推舟”型,那人說是“三番四抖”型,第三人則稱之為“因果相差”型,分析起來還都有板有眼,條條是道。苦的是初學寫作的人,聽了簡直“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生活當中笑料很多,能說笑話的人也大有人在。可生活中的一些原始素材,拿到相聲中來往往產生不了“包袱兒”的效果。我認為原因之一是:相聲作品中的“包袱兒”,不是光用“幽默”、“滑稽”、“詼諧”幾個字就能代替得了的。單純的幽默,起到的效果是使人處于一種“莞爾微笑”之中。而相聲當中的“包袱兒”,必須是“擲地有聲”的,話音一落而滿座即刻哄然,必須是使人開懷大笑,令人捧腹,令人放聲才行。單是使人微微一笑,或是使人回味之后才在心中暗暗一笑的作品,我認為還不能算作是成功的相聲作品。我們演相聲,即使是有經驗的演員,在自己的作品當中組織的“包袱兒”,也不能保證預想和演出的實際效果沒有距離,必須到舞臺上“撞一撞”(即實地演出),看看“響不響”(即能不能使觀眾笑),才能證明“包袱兒”是不是成功(侯寶林先生諧稱為“立體藝術”)。這些都說明,相聲當中的“包袱兒”確有它自己的構思邏輯、語言排列和獨特的技巧。對此加以系統、全面、正確的總結,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歷史上的空白,嚴肅的現代研究的缺乏,相聲表演的“立體”特點,都迫切需要有人來作研究笑的規律的工作。
王力葉同志作了二十多年專業文藝團體的領導。他接觸過傳統相聲,自己也嘗試過相聲創作,較有影響的有《美蔣勞軍記》。作為不是專門從事相聲研究的行政領導,能夠在六四年——相聲藝術尚未引起海內外普遍重視的情況下,毅然提筆開始本書初稿的寫作,這是很有見地的。
在這本書中所寫到的相聲分類和包袱特點,笑料基本因素及構成方法,分析態度嚴肅,條理性強,不淺薄,比較有說服力。書中對于相聲歷史及相聲表演的一些看法,很有自己的見解。盡管我對王力葉同志對一些相聲作品的評價,還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但是讀完整個書,還是感觸甚深、獲益頗多的。我想,在相聲藝術受到人們廣泛喜愛的今天,如果能多一些人多下點工夫去研究相聲寫作的方法論,去探究相聲藝術引人發笑的特點和規律,應該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相聲藝術與笑》,王力葉著,廣播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版,0.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