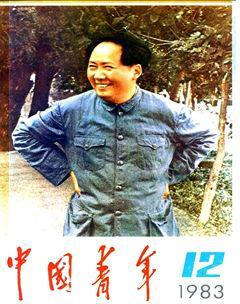一位美籍華人的熱戀
文洋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深夜。北京。北太平莊農貿 市場的小客棧里,一個用破舊木板搭成的床上,和衣躺著一位美籍華人姑娘。她的身旁是兩個農 家女孩。 此刻,月光灑在她安然入睡 的臉上。有誰會知道她今夜為 什么要借宿在這里呢?又有誰 知道僅僅幾小時前她還在作折 磨人的選擇呢?
她叫胡靜婉。一九五五年 出生在上海,五歲那年由外婆帶到香港。她在香港讀了小學、中學,又到美國紐約市的一所市立大學讀書。
兩年前,胡靜婉告別了在美國生活的雙親,遠離新婚的丈夫,只身一人到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回祖國工作”——這是她多年的宿愿。就是在結婚時,她還和丈夫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回祖國工作;第二、不信教。然而,前不久,她丈夫卻“變了卦”:如果她不回美國就離婚。一個重大的生活難題擺在胡靜婉面前,逼她選擇。
她的丈夫是一個從事航天科學研究的技術人員。是因為他的工作難以在中國安排?是他怕自己難以適應中國的生活習慣?……總之,他下了“最后通牒”。胡靜婉的選擇也是翻來覆去的,但是,“回祖國工作”的信念是堅定的,她作出了決定:要在祖國繼續完成她剛剛開始的事業,同意離婚。
胡靜婉不認為自己的選擇有什么錯。可是,對于這一選擇,一向理解自己女兒的父親,這次卻不理解她了。雖然這次女兒是以美籍華人的身份回到她呱呱墜地的國土的,但女兒從小就認為自己是個中國人。因此,當女兒在普林斯頓大學剛剛通過博士學位資格的考試,不等完成論文拿到文憑就匆匆忙忙地要回祖國工作時,他絲毫沒有阻攔。但是,女兒為了在祖國工作而不惜離婚時,作為父親,他在感情上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女婿,他是熟悉的;親家是印尼華僑;這門親事是雙方家長合力促成的。
于是,為了讓任性的女兒回美國去,父親便親自出馬了。三月十五日深夜,他風塵仆仆地從美國乘飛機來到北京,徑直奔到女兒任教的北京師范大學。
父親說:“我是來接你回去的。你收拾一下行李,明后天辦理手續,十八日就走。”父親已和校領導談妥。女兒也沒有說不走。父親松了一口氣。
三月十七日傍晚,女兒突然神情嚴肅地對父親說:“我借了學校一位留學生的錢沒有還,現在去一下。”父親同意了,因為他們明天就要啟程回美國了,應當料理清這些雜事。
然而,胡靜婉并沒有去留學生宿舍,而是步出校門往北太平莊方向走去。她拖著沉重的雙腿,想讓自己的思緒在這靜謐的春夜中安靜下來,再一次作出選擇。
回去吧,父親和在美國的母親、弟弟、妹妹都在等待著你的歸來——不!不!那將意味著自己在中國剛剛開始的事業的終結。
一項事業的開拓,對于每一個人都是艱難而曲折的。她從香港到美國去上大學,開始選擇的是化學專業,目的是為了掌握實際的技術本領。因為她聽說祖國建設很需要從事技術的人才。可惜,講課的教師并不重視實際。教材從理論到理論,抽象又抽象。既然如此,她覺得不如索性改學一門新學科。于是,她又把數學作為專業,主攻數理邏輯。盡管這也十分抽象,但祖國這方面的人才不多,自己可以多做一點開拓性的工作。一門數學專業不過癮,她同時繼續學化學專業。
大學一畢業,她就想回到祖國去工作。但當時是“四人幫”橫行之時,她回國工作的希望成了泡影。
一九八0年,她剛剛通過了博士學位資格考試,就迫切要求回到祖國。她找到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把有關自己簡歷和工作志愿的申請交給他們,請他們轉給祖國的高等院校。
不久,住在她家里的中國訪問學者、復旦大學數學講師張錦豪了解到她的情況,主動給教育部寫了一封信,請正在美國訪問的華羅庚教授帶給蔣南翔部長。隨后,北京師范大學數學系副教授王世強經過學校同意,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表示非常愿意聘請她到這里講學。
盼望已久的愿望終于實現了。一九八一年春節一過,她立即啟程,乘坐春節后第一架航班飛機來到北京,隨身只帶了兩箱書籍和幾件普通的衣衫。
在日夜思念的出生地,她開始了新的生活。她以全部精力,投入教學工作:忙著編講義,忙著刻教材,忙著審習題,忙著答疑難……每天從上午十點到第二天凌晨四點鐘,她都是這樣忙碌著,不知疲倦,卻感到異常的充實。在中國的六百多天中,她幾乎沒去光顧過學校的食堂,廉價而又能快速充饑的方便面條成了她在中國的家常便飯。她幾乎沒有娛樂的時間。逢年過節,有關部門安排宴會、座談會、電影招待會,她一概謝絕參加。名園美景,京華風光,她也無暇瀏覽。她只去過一次頤和園,那是系里請她陪同南京大學的莫紹揆教授。
她無暇去考慮生活得舒適些,更無暇去注意人們對自己這個身材瘦小、衣著隨便的美籍華人的評判。在師大的校園里,她甚至比留學生還不起眼。她當然也不知道“此人甚年輕”這個評語。當師大數學系聘請她任教后,有人擔心“此人甚年輕,因此……”后面的意思也就是“她行嗎”?也難怪,特殊的時代造成我們的大學里有相當一批研究生已經是三四十歲的人,而滿頭白發的教師也不過剛剛評上一個副教授的職稱。一個二十幾歲的女青年,居然登上大學講壇,給那些年紀比她大得多的攻讀博士、碩士學位的人們講課,自然會有人擔心了。更何況,她又是雖有水平卻無文憑的人。
其實,她只要在美國多呆上一兩年,寫出論文,通過答辯,便可穩操文憑。但是,迫切希望回祖國工作的愿望使她作了另一種選擇:一面在祖國工作,一面完成博士論文,然后利用回去探親的假期進行答辯。“文憑有什么?我的實際能力可以勝任我的工作。”她的想法不能說不對。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組織學術答辯委員會時,就聘請她擔任委員。北京大學哲學系、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計算所舉行答辯會,委員們事先征求她的意見,她實際是沒有被正式聘請的委員。
“我不管這些名譽、待遇。要圖這些,我就不回祖國來了。”的確,如果晚兩年回祖國工作,拿到正式的博士文憑,她可以獲得專家待遇。而現在呢,她每月工資200元人民幣,一年2400元。這在國內來說,可是個不小的數目,但對她來說,還不夠一次回美國探親的路費。但她并不在乎這些。
她不管別人欽佩也罷,費解也罷,她反正就是如此。“為祖國而工作,是我唯一的追求。我要把一生中最旺盛的精力全部貢獻給祖國人民。”“我滿意的就是我現在的工作,而工作占了我生活中全部內容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
她的工作算得上是第一流的。她一個人承擔著國內兩個副教授以上的工作量,教學水平也在副教授以上。她的工作不但受到了學生們的普遍好評,而且也獲得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胡世華教授、北京大學王憲鈞教授以及丁石孫、吳允曾教授等國內專家和學者的高度贊賞。胡世華和王憲鈞教授多次表示,我國數理邏輯這一薄弱學科的發展,除了依靠國內自己的力量之外,在國外學者中,主要應依靠象胡靜婉女士這樣難得的年輕有為而又熱愛祖國、不怕艱苦、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人。
這里需要她,她又何嘗不需要這里呢?她如此執著地眷戀著這塊生育自己的土地,如此深情地熱愛著中華民族。她有義務,有責任使這個古老的國家跨入世界強國的前列。
夜深人靜了。她的思緒仿佛被春夜的清風梳理過一般清晰了。她的腳步似乎也輕快了。
她快步奔向北太平莊農貿市場的小客棧。
她躺在簡陋的床上,看了一眼手表,還不到十二點呢。她第一次這么早地躺在了床上。剛才紛亂的心平靜了。她遙望星空,真想把自己的歸宿告訴父親,好請他放心。
父親只身離開了祖國。胡靜婉又一次堅定地作出了選擇:把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眷戀、自己的全部熱情都傾注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