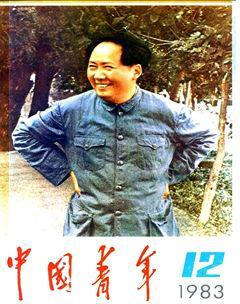激揚吧!中國的黃鐘大呂
孔維民
在我精心制作的音樂卡片Z-14頁上有這樣一段值得自豪的記錄:“應世界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邀請,中國的四位音樂家韓中杰、劉德海、姜建華、黃河前往美國參加馬薩諸塞州的一個音樂節(jié)。他們用中國樂器演奏的民族音樂《春江花月夜》《江河水》等引起了巨大反響,被譽為迷人的東方藝術的經(jīng)典代表。當?shù)匾患胰A人報紙由此發(fā)表評論說,中國的黃鐘大呂*震響了美國,震響了全世界。”
我凝視手中的卡片,思緒翩然而起……
近年來,隨著閉鎖政策的打破,我國許多優(yōu)秀的民族音樂作品被介紹到國外,眾多出訪的音樂團體載譽而歸,不少中國音樂家獲得了國際性的大獎,胡曉平、葉英、譚盾、呂思清、傅海靜、梁明……一個個音樂之星在國際樂壇上相繼升起。啊!祖國的黃鐘大呂并沒有因年代久遠、屢遭劫難而被毀棄,反而以其更加激揚昂奮的樂聲不斷在世界的回音壁上發(fā)出轟響。
愛國,就要了解和熱愛我們源遠流長的祖國文化;愛國,就要了解和熱愛祖國文化寶庫中燦爛輝煌的民族音樂。
這是一份多么豐厚珍貴的遺產啊!
我國的民族樂器已經(jīng)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當中,就有竽、鼓、磐等樂器的記載。甚至在七千年前的古墓中,就發(fā)現(xiàn)了骨制的三孔笛。近年出土的楚國曾侯乙編鐘,以其規(guī)模之宏大,造型之精美,音律之準確,音色之優(yōu)美,震動了全世界,被譽為“世界第八奇跡”。我國第一部詩歌集《詩經(jīng)》產生于春秋時期,它本來帶有曲譜,能夠形之歌詠,可惜后來曲調大都失傳。早在二千八百年前的西周后期,我國就出現(xiàn)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本系統(tǒng)完整的音樂美學文獻——《樂記》。與西方文化史比照,這些音樂的發(fā)現(xiàn)和記載比希臘早大約數(shù)百年。中國歷代對音樂都十分重視。當西方還在把音樂視為宗教的“仆人”時,中國的統(tǒng)治者已經(jīng)把音樂看作與政治、經(jīng)濟并重的東西。先秦時把“樂”列為“六藝”之一。春秋時的教育家孔子將禮、樂并稱,強調“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著名的《禮記·樂記》上寫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jié)”,把音樂視為宇宙萬物的諧和規(guī)律的體現(xiàn),從哲學高度揭示了音樂的本質。從狩獵、祭祀、賓宴到勞動、婚喪、娛樂,音樂幾近成為維系中華民族經(jīng)濟文化生活的經(jīng)緯干線。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它的音樂源流也是國內各民族音樂的融合體。《詩經(jīng)》中的十五國風,就代表了十五種地方曲調。昔日在絲綢之路上廣為傳播的龜茲音樂,就發(fā)源于中國西部的新疆一帶。今天民族樂器的主要吹管樂竹笛,也來源于“何須怨楊柳”的羌笛。漢代邊疆的匈奴、鮮卑、氐、羌、羯等少數(shù)民族,很早就為發(fā)展中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古往今來,當各民族的音樂文化密不可分地融匯在一起的時候,一個統(tǒng)一、興盛的中華民族便形成了。
我熱愛祖國的民族音樂,但我并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中外的音樂發(fā)展史告訴我們:中國音樂,作為世界文化的一支,它正是在同各國音樂的互相影響,兼收并蓄的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今天,交響音樂、古典歌劇以及國外各種現(xiàn)代音樂都已成為我國人民音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如果我們也不是一個民族虛無主義者的話,可以從中外音樂史上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源遠流長的中國音樂在世界各國的音樂發(fā)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詳篇》上記載,“18世紀末進入歐洲的中國笙,啟發(fā)了西方創(chuàng)造出三種簧片樂器:口琴、手風琴和(簧)風琴。”中國古代的一種吹奏樂器“尺八”,初唐以來就在東南亞一帶國家流傳,至今仍是日本和美國音樂舞臺上的一種獨奏樂器。中國唐代的音樂,是世界藝術史上的瑰寶,亞洲各國音樂都與唐樂有親緣關系。著名日本音樂教授小泉文夫曾對中國音樂界說,日本流行的雅樂就直接起源于唐樂。澳大利亞音樂中心主席默克多來中國訪問后說,他們接觸過許多亞洲音樂,這次來中國聽了音樂會,才感到總算找到了它們的源頭。偉大的匈牙利作曲家、音樂學家巴托克曾撰文分析中匈兩國音樂的師承關系,說明了“古老的匈牙利五聲音階是中國等中亞民族五聲音階中心的一個分支。”著名的美國作曲家、指揮家阿甫夏洛穆夫也曾直接采用中國音樂素材,寫下了不少有名的交響曲和輕歌劇……一位中世紀的哲人說得好,一個民族,哪怕只對人類思想文化的進展作出過一點貢獻,這個民族就配享受最高的敬意。
啊!中國,我生于斯、長于斯的祖國啊,你在世界音樂史冊上留下了多少光輝的篇章,我由衷地為你感到驕傲!我熱愛音樂,更熱愛我們中國自己的民族音樂。這不僅因為它首先把我引入了藝術的大千世界,而且它使我深刻地認識了自己的祖國。我的父親喜歡民樂笙,它那爛漫的和聲代替了我兒時的催眠曲。我的母親當過小學音樂教師,她曾用我們民族的歌聲進行抗日宣傳,喚起民眾。從她用老年抖動的音調唱出的《游擊隊之歌》中,我理解了我們民族不可摧毀的原因。“文革”前,親戚朋友常聚在我家舉行家庭音樂會。每到那時,笙簫對答,民歌賦詠,一種家庭、民族之愛在我的血管里奔涌。我的四表姐李谷一演唱的湖南花鼓戲和民歌是最受歡迎的節(jié)目。一九七四年她調中央樂團擔任獨唱后,家人們還常去信勉勵她走民族化的演唱道路。可以說,李谷一完全是在民族音樂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在這種濃厚的藝術氛圍中,我自己也培養(yǎng)了對中國民族音樂的深厚感情。一九八O年我上大學時港臺之歌盛行,我卻登臺演唱了岳飛的《滿江紅》。一曲唱畢,整個晚會完全改變了氣氛。對著臺下雷鳴般的掌聲,我深深地感到,真正的民族之音可以溝通當代中國每一個青年的心。
歷史的回顧促使我思考,為什么祖國的民族之聲有一種經(jīng)久不衰的魅力呢?深入欣賞中國的音樂、詩歌及繪畫,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中西方的美學思想有個很大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西方人較看重形美,中國人更注重內品和形美的統(tǒng) 一。好比西方人喜歡玫瑰,因為它的外形的確很美。中國人則更喜歡蘭花、竹子,這不僅因為它們外表秀美,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內品,它們是高尚品德的象征,是高潔精神的體現(xiàn)。中國的音樂也很重視內品,那就是它用精巧的藝術形式所表達的中國人的感情。有友誼之情,一首《高山流水》古琴曲,觸動了天下多少知音;有相思之情,一曲悲涼的《江河水》,牽扯了無數(shù)天涯斷腸人;有愛戀之情,一支哀婉的《梁祝》,歌不盡古今多少矢志不渝的有情人……我喜歡中國的民族音樂,就是喜歡它能細致入微地表達中國人蘊籍深邃的獨特情感。這種情感是中國人民莊重、含蓄、深沉、堅韌、自強不息的民族性格的折射之光。
國運昌,樂運昌;樂運昌,國運昌。祖國幾千年的興衰史不是已經(jīng)反復證明了這個真理嗎?
激揚吧,祖國的黃鐘大呂!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為了人類文明的昌盛。
*黃鐘大呂:中國古代音律名稱;黃鐘為十二律中第一律,大呂為十二律中第二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