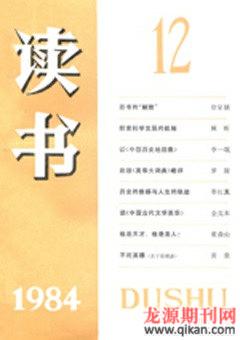談葉圣陶的文學創作
吳泰昌
金梅的《論葉圣陶的文學創作》攤開在我的書桌上。北京少有的炎熱天。熱的空氣和熱的記憶使我邊看邊揩汗。終于讀完了。我為作者多年努力的成果高興,真心實意的。
我和金梅的初識,是三十年前。我們分別從江南考入了北京大學。他比我早一年畢業了,留校教書,他說因家在天津,他自愿調走。當時河北省會在天津,他去了河北省文聯。此后,他隨著河北省會的變異,到了保定,到了石家莊,一直在名稱來回變換的一家省文藝雜志社當評論編輯。時代的動亂,不安定,朋友間的走動也就少了,只好彼此在心里相互惦記著。“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想不到和金梅在一起共事了一二年,一個編輯部,一個組,一個辦公室。可以說得上是朝夕相處。晚上,九點多鐘,我看書看累了,到院子里散步,見辦公室的燈還亮著——金梅單身,辦公室就是他的宿舍——我推門進去,和他閑聊一陣。深夜,我們談起了大學時代的往事和一些不知去向的同學,感觸叢生。當我離去時,常常過了十點,我勸他早點休息,他總是點上一支煙,微笑著說:再干一會。我想他還要翻一會書。我也養成了這個習慣,入睡前總得翻點什么看。這次,葉老文學創作這本書的初稿完成于六十年代初,一九七九年又動手修改。我想,在我和他相處的那些日子里,在靜悄悄的夜晚他肯定在積累資料,作修改的準備。那個年月,現代文學史講葉圣陶還需要點膽量,他不得不靜悄悄地干。我后悔,若早知道他在從事這項工作,當時我雖幫不了什么忙,至少不會幾乎每天晚上剝奪他一段時間,影響他靜悄悄地工作。
我稍為詳細地敘述了我和金梅的相識和交往,旨在提醒讀者,書的作者寫出這本書,實非易事。這是地地道道的業余之作。他學的是新聞專業,現代文學史只捎帶讀過,長期的編輯生涯,使他缺乏完整的讀書和寫作的時間。知難而進,而上,這是五十年代許多大學生所追求的樂趣。我打心眼里欽佩金梅治學上的這股韌勁。
我與金梅同是葉圣陶作品的愛好者,而又認為對這位重要作家研究不夠是一種遺憾。遺憾何止即這一點。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史很有光彩的一頁。我們的研究工作,顯然還沒有很好地跟上去。雖然對一二個或幾個偉大作家的研究出了一些專著,研究水平在不斷提高,但整個說來,還不夠深入,不夠全面。即使一向被重視的對魯迅的研究,也難說成果能令人十分滿意。對文學史上存在過的為數眾多的,有特色有成就的一批作家,單個研究不夠,對一些復雜的文學現象,認真剖析不夠,這勢必影響文學史水平的提高。近幾年,現代文學史出版了好幾部,每部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進展,顯示了特色。但總的說,新鮮感不夠,材料上或觀點上,多少給人以大同小異的印象。我以為,這與對一批有影響的作家缺乏細致的考察有關。我們需要靜下心來,扎扎實實地分析研究一批作家的創作,從中引出實事求是的見解。在這樣的廣泛耕耘的基礎上,再加以綜合,這樣寫出來的文學史可能會踏上一個新的階梯。前些年,聽說上海文藝出版社有意編輯出版一套現代作家研究叢書,我很贊賞編者的這種眼力和魄力。現在已經見到一批成果了,其中就有金梅的這本書。在葉圣老九十壽辰之際,也算得是一份薄禮吧,至少表達了讀者的一點心意。
葉圣陶是“五四”新文學初期影響較大的作家之一。在現代文壇活躍了七十個春秋。他創作涉及的面廣,小說、戲劇、詩詞、童話、散文、評論,都有顯著的成就。他一生的多半時間是用在編輯和教育事業上,平日為文又嚴謹,作品的數量不算太多,但也有數百萬言了。這樣一位對我國新文學發展有顯著貢獻的作家,這幾年引起中外研究者的興趣。解放前,茅盾、朱自清、夏丐尊等零星寫過評介葉圣陶作品的文章;錢杏
讀完本書,在論述上,我感到的一個缺憾是,有些地方多少缺乏一點鋒芒。這主要是指在個別存在著尖銳分歧觀點的問題上,看不到作者應有的意見。比如說,魯迅對葉圣陶創作發表過意見。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給日本增田涉的信中說:“葉的小說,有許多是所謂‘身邊瑣事那樣的東西,我不喜歡。”我平日留心魯迅的這段話,有些研究文章實際上也采納了魯迅的意見。我希望在本書中看到金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不知是作者忽略了這一材料,還是有意避開了對這個敏感問題的表態?我有點失望。魯迅先生是我們最最尊敬的偉大作家,他關于文藝的許多深刻精辟的見解,至今仍給我們以教誨。但是,對文藝作品的欣賞與評價,再有慧眼的人,也難免有失之偏頗的地方。在對待一些作家、作品的看法與愛好上有不一致,是正常的現象。中外文學史上這類例子并不鮮見。羅曼·羅蘭就不如我們現在這樣推崇巴爾扎克老人。而對羅曼·羅蘭的作品,當時法國文壇,也不如今天我們中國研究者評價那么高。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價,自然有客觀標準,但不一定每個大作家和權威所發表的每一個具體意見都是真理,都是定論;就一定全面,一定正確。所以列寧一再告誡人們要將黨的領導者對文藝的具體意見,與黨對文藝的主張區別開來。我個人對魯迅先生談論葉圣陶小說創作的那段話,有不敢茍同的地方。喜歡不喜歡,這是個人的欣賞口味的問題,可不討論。主要是立論的那句話。我以為,綜觀葉圣陶小說的全貌,得不出“有許多是所謂‘身邊瑣事那樣的東西”的結論。這里,首先涉及到一個創作理論問題。什么才算是寫“身邊瑣事”?文學反映社會生活,題材的大小是重要的,但不是決定性的。關鍵在于題材本身所包涵、所沾濡的社會意義大小。魯迅先生一些被公認為杰作的小說,如《一件小事》,就題材而言,很難說就不是“身邊瑣事”,但它卻具有深刻的社會內容。葉圣陶的小說,幾乎都是寫他熟悉的教育界、知識分子的生活,何況他還寫過膾炙人口的短篇《多收了三五斗》,不能一概說,這些生活多是“身邊瑣事”。葉圣陶的多數小說,都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其次是,魯迅先生一九三六年對葉圣陶小說作這樣的概括,也不符合葉圣陶小說的發展實際。如果說,葉圣陶從辛亥至“五四”前后,有些小說對時代的脈搏把握還不夠,那么“五卅”之后,他創作上的這一弱點得到了很大的克服。長篇《倪煥之》的出現是一個明顯的標志。這部長篇,生活之厚實,時代氣息之新鮮,藝術描繪之精致,使其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杰作。茅盾推重《倪煥之》是近十年來的“扛鼎之作”,說“這樣‘扛鼎似的工作,如果有意識地繼續做下去,將來我們大概可以說一聲:‘五卅以后的文壇倒不至于象‘五四時代那樣沒有代表時代的作品了。”我的上述理解不一定對。借此就教于讀者和本書的作者。我之所以說這層意思,是期望我們的學術研究帶有更強的針對性、論爭性。正確的意見往往是在爭辯中形成的,穩定的,真理是愈辯愈明的。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鼓勵和發揚學術上的勇氣。在我看來,即使與學術權威的“定論”相左,只要是認真從可靠的材料中引出來的結論,就要敢于發表。這樣,我們的學術水平才可望大幅度提高,研究者也才能形成鮮明的個性。而這,又需要有學術上的民主空氣作保證。
讀罷本書,還想到一個問題。這就是作為文藝評論家的葉圣陶,也應該引起我們研究者的重視。“五四”以來,許多作家在創作的同時,寫了大量有特色的評論文字。不象我們現在分得這么一清二楚:作家就是作家,評論家就是評論家,編輯就是編輯,三者往往是交錯在一起的,熔一爐于一人。葉老就是這樣的一位多面手。他一生寫了數十萬字的評論文章。解放前的多側重于語文角度,象《文章例話》里的那些篇什,但,其意義決不僅僅停留在文章結構和語法修辭的推敲上,涉及到對文藝新作的評價和理論問題的探求。例如,一九三六年夏衍的報告文學名篇《包身工》發表不久,葉老就對此加以熱情評介。通過對作品入微的剖析,闡述了報告文學的特性,呼吁這一新型文學樣式的蓬勃發展。解放后,葉老的主要精力在教育事業上。他寫了一些作品,散文多,小說只一篇。評論文章不少,大多收在《葉圣陶論創作》一書中。葉老對新的創作十分關心,能看就看,不能看就聽廣播或由家人誦讀。記得一九七八年《文藝報》復刊時,我去向葉老求援。他說正在聽廣播一部小說,聽完了,若有想法再說。后來至善來電話叫我去取稿,是葉老聽完這部長篇小說后寫的隨想。這就是發表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三期上的《我聽了<第一個回合>》。葉老評論文章,長短不一,短小的居多,文風樸實,親切自然,毫無一個大作家說大道理的架子,寫法自如,角度多樣,給人以切實的東西。這兩年作家兼寫評論的漸漸多起來了。這是一個好現象,既擴大了評論作者的隊伍,又豐富了評論文章的品種。作家的評論文章活潑清新,更能道出同行的創作甘苦,自然也有它的短處。如果認真總結一下葉圣陶在評論上的成就,不僅對全面評價這位人品文品均為人敬重的老作家是必要的,而且對發展今天的文藝評論也大有益處。金梅的這本書題名已限定論述的只是葉圣陶的文學創作,評論不在此書的視野之列。我不是責怪金梅有什么遺漏,而是想應該有人研究這個選題。
一九八四年七——八月于北京
(金梅《論葉圣陶的文學創作》,即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