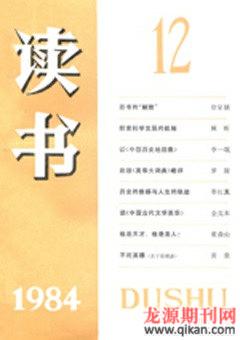讀《中國佛教典籍選刊》兩種
石 峻
佛教內容復雜,牽涉面很廣,如果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不從第一手材料出發,沒有比較系統的了解,就很難總結出具有現實意義的、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發展規律。中華書局編輯部有見于此,特在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擬訂了《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的整理出版計劃。
這項計劃中,最近已有兩種重要著作出版,一是郭朋同志的《<壇經>校釋》,一是方立天同志的《<華嚴金師子章>校釋》。
一般說來,目前要做好這一方面古籍的整理工作,確實存在不少難處。主要是由于各門“宗教學”的專業隊伍中,除了少數人之外,有人對于某一種宗教,例如佛教的信仰和經文典故出處等,確是比較熟悉的,但是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多少還有些欠缺;另一種情況是,有人對一般抽象的馬列主義原則,從概念到概念,可能是記誦得很多的,但是關于佛教思想的具體內容,由于接觸得太少,確實不甚了了,很難作出具體分析。其次是,由于學者們的專長各有不同,某些人平日只好注意古書的目錄、版本、校勘……等考據工作,有時不免忽略在理論上的深入解剖、批判分析。而另一些人平日專搞所謂思想批判的,又往往對這類古書的目錄、版本、校勘……等,所知不多,使一些工作上的具體問題,無法得到認真的解決。現在難得有郭朋、方立天兩位同志,他們對理論和資料這兩方面都有比較長期的鉆研,夠得上是新時代我國佛教思想史的專門研究工作者,因而可稱得上是選擇得人了。
談到這兩種書的性質,可說同是最具有中國古代宗教哲學特色的代表作。大家知道,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是無所謂“禪宗”和“華嚴宗”的。中國“禪宗”一派實際上的創始人慧能(六三八——七一三)的言行錄《壇經》,是我國人所寫的佛書中,唯一被信徒們專稱為“經”的,因此在宗教信仰和思想學說史上,具有非同尋常的地位和影響。《華嚴金師子章》,則是我國佛教華嚴宗一派事實上的建立者法藏(六四三——七一二)的理論綱領,而且這兩種書產生的年代,在歷史上是很接近的,雖然份量都不算大,也有在朝與在野之分,但皆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和佛教思想史的必讀書。并且又都早有外文譯本,在國際學術界上也頗有聲名,不斷有人在研究。
涉及《壇經》全書具體完成的情況,至今尚無定論。但后來屢次經過篡改增訂,有多種不同的版本(一九七六年日本由柳田圣山主編《禪學叢書》之七,影印《六祖壇經諸本集成》,共收全本十一種),則是事實。郭朋同志一九八一年曾由山東齊魯書社出版過《<壇經>對勘》一書,將其中四種最有代表性的版本(即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作了仔細的分段比較,并附加個人案語。這次中華本《壇經校釋》,則又特選目前認為時代較早的敦煌寫本,即上述所謂法海本的作為底本,它應該是此后各本《壇經》的基礎,而不采用在我國廣泛流行的元代宗寶本(一二九一),那是很有見地的。因為這才最便于說明我國佛教禪宗思想的本來面目,以及后來演變的基本線索。這本《校釋》的特點之一,是作者專門寫了長篇的“序言”,系統地介紹了這書的性質和已往研究的情況兼及本人的新得,并附載參考書目以及歷代有關重要史料原文。至于《壇經》本文“校釋”部分,則又參考了過去國內外的研究成果,包括了日本上一代著名學者如宇井伯壽、鈴木大拙……等人的部分結論,以及我國臺灣地方著名佛學家印順法師的近著——《中國禪宗史》。對胡適過去的某些考證,也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可謂包羅宏富,實是有關《壇經》研究帶總結性的著作。如果求全責備,還說有不足之處的話,那就是作者限于環境,尚未有機會見到教煌抄本原件或影印本,從而未能再進一步核實作為底本的民國《普慧大藏》本,即重印日本學者鈴木真太郎(鈴木大拙)、公田連太郎兩人校本的貢獻和缺誤。
至于《<華嚴金師子章>校釋》一書的底本問題,則比較簡單,歷來各種注解本的差別并不太大。但是作者還是下了功夫,仔細地加以校勘,注明了各本之間字句的差異,希望能成為定本。同樣,書前載有作者《華嚴金師子章評述》一篇長文,用代“序言”,全面地進行思想內容的具體分析,可知在科學研究上,本書也是帶有批判性和總結性的。按《金師子章》一篇,本是唐代有名的原居康居國的法藏和尚對女皇武則天的宮廷說法,就便用鎮殿金師(獅)子作比喻來講明華嚴宗一派佛學的基本論點,是一篇富有思辨色彩的經過整理的發言提綱,可說是“言約意豐”。校釋者根據我國自宋代以來,有名的華嚴宗和尚承遷、凈源等人的注解,以及日本僧人景雅和高辨的有關著作,和《新修大正大藏經》重排明刊本進行了校勘、比較研究,并收了中日兩國上述幾個本子近乎全部的注釋。然后再用現代漢語對書中的固有名詞、專門術語和那些比較難懂的字句,作了深入淺出的解說,為了串講各段的大意,并加上“總釋”,是很費過一番心思的。附錄有法藏的傳記資料以及各種注本的“序言”和“題解”等,共十一篇,確是研究唐代佛教華嚴宗思想一冊比較簡明扼要的書。
(《<壇經>校釋》,郭朋校釋,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0.71元;《<華嚴金師子章>校釋》,方立天校釋,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0.8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