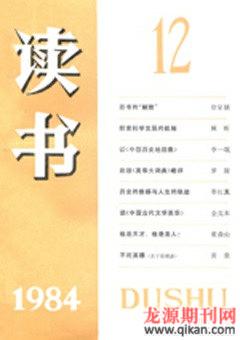《世說新語箋疏》的特色
曹道衡
《世說新語》一書,內容頗為復雜。劉義慶在編纂此書時,除了雜采前人記載外,又記錄了一些當時的傳聞。后來劉孝標作注,又搜集了許多有關史料。這些關于魏晉名人的言行、軼事,有些是事實,有些則與史實不符。余嘉錫先生遺著《世說新語箋疏》,博采眾說,對前人懷疑《世說》而有根據的,就加以采用。如《自新篇》關于周處向陸云求教事,勞格已辨其說。對前人懷疑《世說》,而事實上并非不可能者,則予以駁正。如《言語篇》王羲之登冶城規勸謝安事,姚鼐《惜抱軒筆記》曾以為不可能,而《箋疏》引程炎震說,指出此事確有可能,而時間則在永和二三年間王羲之為護軍時。對《世說》所記軼事有誤而前人未提懷疑者,《箋疏》引證了確切材料,證明其不可能。如《政事篇》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事,《箋疏》引《后漢鴻臚陳君碑》及《后漢書·陳紀傳》考定陳紀十一歲時,其父陳
《世說新語》一書所記軼事雖不盡可信,而所載當時社會情況、風尚習俗,則各有極重要的價值。《箋疏》對這些方面有許多精辟之見。如《方正篇》中載諸葛恢不愿嫁女與謝裒事,《箋疏》論到了謝氏在東晉初年社會地位還不高,至謝萬、謝安以后,才與王氏并稱。由此又論到世族與寒門的升降。這對研究晉代社會史是很重要的貢獻。又如同篇載王獻之看門生樗蒲事,《箋疏》詳述了當時的“門生”制度,對東晉南朝的等級制作了詳細的論述。又如《德行篇》“客問陳季方”條及“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條,《箋疏》論證魏晉清談名士風氣大抵都發源于后漢;《方正篇》“五中郎年少時”條,《箋疏》談到晉代士人對尚書郎的看法,從社會風氣加以解釋,都頗精當。《德行篇》“殷仲堪既為荊州”條,《箋疏》對“天師道”的考證;“劉尹在郡”條,《箋疏》對六朝人乘牛車的解釋;《文學篇》“簡文稱許掾云”條,對玄言詩向山水詩的發展以及謝混在其中的作用,也都有獨到之見。這種對社會狀況和學術源流的研究,在古書的注疏中極為少見。
《世說新語》的版本較多,《箋疏》專門列了校文一欄,把各本校文一一列舉。作者遵循清人傳統,不輕易改字,只在“校文”或“箋疏”中說明自己的看法。這種方法是很謹嚴的。另一方面,《箋疏》中關于《世說》的異文,頗多確切不易之見。如《排調篇》“簡文在殿上行”條的“
《世說新語》中所載魏晉人口頭語言,由于時代久遠,有許多已不可解。《箋疏》在這方面,也作了許多精當的詮釋。如《德行篇》“吳道助、附子兄弟”條中的“料理”二字;《政事篇》“王丞相拜轉揚州”條中的“蘭
《世說新語箋疏》對《世說》中的藝術特點,也有所論述。如《言語篇》中衛
當然,《箋疏》是一部遺著,由于作者晚年因病擱筆,所以說還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世說》中有若干記載,似亦有可疑處,《箋疏》未予指出。如:《規箴篇》“謝中郎在壽春敗”條,劉孝標注云:“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不信謝安在謝萬軍中。但考《方正》、《簡傲》兩篇,可見謝安確在軍中,劉注誤。對此,《箋疏》并未駁正。《惑激篇》“韓壽美姿容”條,劉注引《郭子》以為是陳騫女事。《箋疏》從《太平御覽》中引了《郭子》原文。但此說恐未可信。因為據《晉書·賈充傳》,賈充無子,立韓壽子謐為孫,改姓賈。這顯然因為賈謐乃賈充外孫,有著血緣關系。如果賈謐之母乃陳騫女,恐難立以為嗣。這些地方可能作者另有考證,也可能因病停筆,所以沒有來得及指出。但這些小小的不足,只是個別的。總的來說,《箋疏》是一部極有價值的著作。此書的出版,嘉惠后學,其功夫決非淺鮮。
(《世說新語箋疏》,余嘉錫著,周祖謨、余淑直整理,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八月第一版,4.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