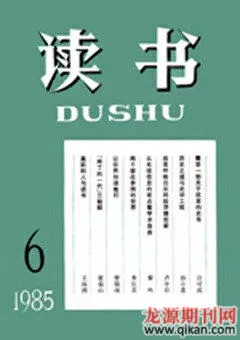英譯《易經(jīng)》
柯大詡
十九世紀(jì)末第一部《易經(jīng)》的英譯本出現(xiàn)時,譯者曾說,“若依我們想來把這些小圖畫湊在一起一定是饒有詩意的,但實際的結(jié)果卻干燥如灰塵。”“究竟為什么要弄這一堆亂七八糟的圖畫?這些小線段告訴我們什么?”如果這代表前一個世紀(jì)西方人對待《易經(jīng)》的態(tài)度,那今日可是大不相同了。從二十年前的垮掉的一代起,《易經(jīng)》就和禪宗、印度哲學(xué)等一起大走其紅運,而現(xiàn)在據(jù)贈送我這本書的西友所談,物理學(xué)家也在《易經(jīng)》中找靈感。究竟他們要在這部書中探尋什么?他們是怎樣評價我國這部最古的(人類最古的?)純哲學(xué)著作的?這便是我打開這部譯本時所想解決的。
這部在一九八○年重印的譯本是根據(jù)衛(wèi)禮賢(Richard Wilhelm)的二十年代德譯本英譯,但由衛(wèi)氏之子補充校正過,另有瑞士著名心理學(xué)家榮格(C.G.Jung)的一篇長序,所以可以算得是個新譯本了。據(jù)說這個譯本在介紹此書到西方起了最大的作用。我國研究《易經(jīng)》當(dāng)然有悠久的傳統(tǒng),但似乎缺乏近代的觀點。而現(xiàn)代的研究者雖然有不少新發(fā)現(xiàn),但還沒有出一部整部頭整理《易經(jīng)》的書。那么看看這部書怎么把《易經(jīng)》內(nèi)容譯成現(xiàn)代人所能理解的形式,也是不無好處的。
譯本的編排分作三卷。第一卷題名“本文”,包含了六十四卦的圖形及其彖辭、爻辭。另外譯者又把大象包括在內(nèi)。第二卷題名“材料”,包含了十翼中的大傳和說卦。第三卷題名“注釋”,則是按六十四卦拆開分列的彖傳、小象、文言、序卦、雜卦。我覺得這的確比我國傳統(tǒng)的排列清楚些。譯者自己又撰寫二文。其一叫“卦的結(jié)構(gòu)”,講的是二與五應(yīng)這些基本常識,并談到互體,放在卷二之末。其二講揲蓍之法,作為附錄一(附錄二是六十四卦分八宮之表,附錄三索引)。譯者不贊成漢儒那些附會,河圖洛書根本沒有提,先天后天只是十翼中原文提到的地方才有,卦變亦未提。每段譯者都有注釋,大都是沿著王注程傳朱子正義這條路子,頗穩(wěn)妥曉暢。譯者態(tài)度是謹(jǐn)慎的。書前尚有董作賓的題字(用甲骨文)。
為什么重視《易經(jīng)》?由榮格的序倒可看出端倪來。他說西方傳統(tǒng)哲學(xué)注重因果性,把它放在公理的地位,而忽視偶然性。中國卻相反,注重偶然性。《易經(jīng)》正是研究偶然性產(chǎn)生之各種情形。近代物理發(fā)現(xiàn)了因果性只是統(tǒng)計地正確,宇宙本身是偶然性的。這些話,筆者認(rèn)為當(dāng)然是正確的。序中又說所以現(xiàn)在一剎那的某種情況可以反映宇宙的情況以及歷史,正如觀察樹木的年輪一樣。我覺得,這就無怪西洋現(xiàn)代仍停留在把《易經(jīng)》當(dāng)作卜筮之用這個階段了。實則從王弼以后,讀《易》的人越來越注意的與其說是現(xiàn)在卜出何卦,不如說是在各卦的情形下一個人應(yīng)該怎么做?至于這六十四種“局勢”哪一種適合于現(xiàn)在的局勢則不一定由卜決定了。這樣,此書變成了一本“處世應(yīng)變的指南”,這在封建時代的政界實在是大有用途的。在現(xiàn)在也不敢說毫無價值吧?
此書有個缺點就是譯文究竟太老,不大能吸收新近的研究成果,如“無妄”中“無妄之災(zāi)”,現(xiàn)在有人解為“妄”即“望”字,“無妄之災(zāi)”是“無希望之災(zāi)害”,后文“無妄之疾”也是這樣,所以才說“勿藥”。而此譯本仍是Undeservedmisfortune總之,《易》和《詩》一樣,到了今日,只憑先儒傳下的注解是絕對不夠的,須得由文字學(xué),考古學(xué),人類學(xué)……各方面的研究去創(chuàng)新解,才能回復(fù)它原來的面目。
(TheIChing,trans.byRi-chardWilhelm,PrincetonUnivcr-sitypres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