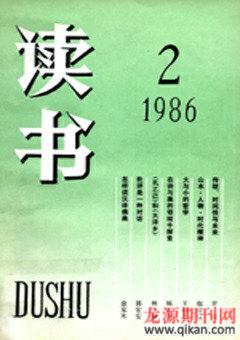自然美的思考
徐建融
自然美是美學中最通俗易懂的一個課題,但是,要想探究其中的內涵意蘊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美學家們把它稱作“阿喀琉斯的腳踵”,各種美學理論都要在這里暴露出它們的致命弱點。
伍蠡甫先生主編的《山水與美學》,是迄今所能看到的研究自然美的第一部論文集,共選有三十四篇文章,大都出自專家之手,從美學和文藝科學的角度,分別對自然美的一般理論、山川名勝的審美觀、歷代(主要是古代)山水詩和山水畫的美學根源、園林美學、自然美和藝術美的關系諸問題,作了深刻的研究和探討,代表了近三十多年來我國美學界對自然美的一些主要觀點。這些觀點,不盡一致,有時甚至正相
最困難的莫過于自然美的本質定義。朱光潛的《論“自然美”》(第18頁)、《山水詩和自然美》(第98頁)倡為“主客觀統一論”:“我們覺得某個自然物美時,那個客觀方面對象必定有某些屬性投合了主觀方面的意識形態總和。這兩方面的霎時契合,結成一體,就是自然所呈現的具體形象。”蔡儀的《談自然美》(第26頁)力主“純客觀論”:“自然事物的美是指天生的自然有的,所謂天生的,是說不受人的影響的。……自然美在自然本身。”李澤厚則認為,要表現和說明自然美的特征,最好用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一句話來說明,就是“人化的自然”;只有從人類“實踐”的哲學高度,才能準確地詮釋自然美的原因(第29頁、124頁)。此外,蔣孔陽、施東昌、蕭兵、林同華等也從不同的層次和側面提出了各自對于自然美本質的看法見解。眾說紛紜,令人莫衷一是。
柏拉圖早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就已強調把握美的本質的困難,因而不得不用一句古諺來結束全篇:“美是難的。”這并不奇怪,因為包括自然美在內的美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或者用林同華的說法:“自然美是一個流動范疇”(第119頁)。所以,單純從主客觀統一論、純客觀論、實踐論乃至近代西方美學界比較流行的純主觀論(按,朱光潛先生在三十年代亦持此說)等等,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概括人類對于自然審美的復雜現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自然美本質的“不可知論”,如L·維根斯坦等所認為:“美”是屬于不能說的命題。(《邏輯哲學論》)盡管我們不可能“界定”自然美的本質定義,但通過爭鳴、探索卻可以逐漸地“接近”它。本書所引各家之說,正可以看作是從不同的側面向自然美本質的接近和靠攏。
自然美和藝術美的關系問題是又一道中西共通的古老的美學難題。究竟自然美高于藝術美?還是藝術美高于自然美?聚訟千古,迄無定論。眾所周知,車爾尼雪夫斯基是極力主張自然美高于藝術美的(《生活與美學》);黑格爾則認為藝術美高于自然美(《美學》)。本書所選各家之論基本上不出車氏或黑氏的觀點。值得一提的是朱光潛的意見:“如果就自然形態的‘美(其實只是“美的條件”)和美學意義的美來比較高低,那是比擬不倫。這兩個概念之中的關系不是價值高低的關系而是本質異同的關系。”比較應該是同一層次上的比較,這當然是不錯的;但即使如此,也還是難逃兩難的境地。且看朱先生的比較:“如果所指的都是美學意義的美,‘自然美只是雛形的起始階段的藝術美,藝術美當然比自然美要高些。但是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最偉大的詩人和藝術家都有時感到苦惱,覺得自己的作品不能完全表達出自己所見到的形象,特別是關于‘雄偉或‘崇高方面的印象。讀拜倫詠海的詩究竟比不上大海本身所產生的那種雄偉氣魄。”(第24頁)
要之,《山水與美學》所提出的一系列有關自然美的命題,既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隨時都會遇到的切身課題,同時又是中外美學史上淵源已久的傳統難題。對這些問題,本書并沒有(也不可能)提供讀者一個結論性的答案,但卻啟示了讀者自由的選擇和深層的思考。由此足以窺見編者的睿智和苦心。在美學研究中,自然美比之其他的各種美無疑具有更廣泛、更深厚的群眾基礎。從這一意義上,我們似乎更有理由把自然美比作“安泰的腳踵”,一切美學理論端賴了它才得以腳踏實地地從大地母親那里汲取無窮的生命活力。因此,我們衷心期望《山水與美學》的問世,能推動自然美的研究蔚然成風、推動一般美學的研究更加深入。
(《山水與美學》,伍蠡甫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平裝2.30元,精裝4.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