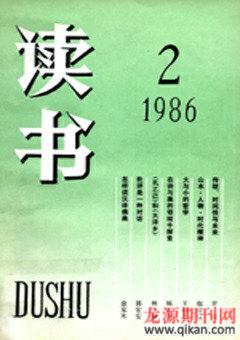漢武帝和秦二世
李開元
漢武帝即位之初,向儒學大師董仲舒發出了這樣的疑問:“蓋聞虞舜之時,游于巖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
根據舊史家的說法,上述疑問產生于漢武誦讀儒家經典后的思索,是他向董仲舒策問治世之道的求教,由此而引出了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著名言論。這確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即著眼于漢武安邦治國大義的一方面。
眾所周知,漢武倡儒而不盡信儒,汲黯一語中的道破他:“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在堂皇的經典大義下隱藏著恣肆的私欲。從這個角度考察上述疑問,我們不難看出,漢武之所以質疑于勞和逸,奢和儉之間,實質上反映了他隨心所欲的個人意志和克己求治的社會責任心之間的沖突。隨心所欲作玩主嗎,勵精求治作圣君嗎,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縱欲求治兩不誤?從他的一生看來,他是選擇了后者的。
班固稱贊漢武說:“漢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觀,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這是對他一生治績的總結。
司馬光批評漢武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為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這是他一生縱欲的匯總。
把班馬二人的評論結合起來,漢武一生行事的輪廓就大致清晰了,最大限度的勵精圖治,又最大限度的縱情極欲,這就是他一生行事的信條。
無獨有偶,亡國之君秦二世,在他即位之初,向著名法家李斯也提出了類似的疑問:“吾有私議而有所聞于韓子也,日:‘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
秦二世自幼學法,他以法家的明快坦率,直截了當地道出了之所以設疑的原因:“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他感嘆人生之短促,深知之間地位之難得,希望在享樂和求治人主求得一條萬全之道,從這點上講,他和漢武帝是相同的。
于是乎,我們難免不發生一種疑問,漢武帝和秦二世,一為儒家的倡導者,一為法家的信徒,一為治世的雄主,一為亡國的暴君,為何都在即位之初發出類似的疑問,為同一問題所苦惱呢?
節制私欲以盡社會責任,放縱天性以恣情享樂,這是并存于人性中的兩大特質。作為個人的封建帝王,一旦登上了最高權力者的高位,就陷入了一種孤獨的窘境,面臨何去何從的選擇。一方面,由于沒有任何強制性的約束,他受到了可以為所欲為的巨大誘惑;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擔當起統治國家的重任,勢必感到巨大責任的威壓,這種威壓迫使個人的一切行為都應符合治理天下的要求。漢武帝十六歲即位,秦二世二十一歲登基,沒有經驗的心靈陡然落入令人眼花繚亂的權力的峰巔,天性中兩大特質的爭斗,自然成了他們特別敏感而緊迫的問題,而他們自身的選擇取舍,往往影響了一個時代的面貌,甚至決定了一個朝代的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