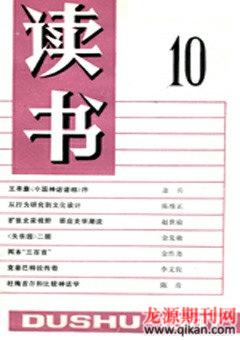周憲王·朱權·王關正續本
張人和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圣嘆批本西廂記·例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西廂記》“王作關續”或“關作王續”之說,起源很早。明末凌
不知什么原因,《例言》的撰寫者張國光同志,竟然把“周憲王”說成是“朱權”,而且認定《西廂記》五本不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的說法是從他們開始的。這是一個誤解,事實并非如此。
如所周知,周憲王和朱權雖然都是明宗室,同為戲曲作家,但并非一人。周憲王乃明太祖朱元璋之孫朱有
關于《西廂記》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大體上有王實甫作、關漢卿作、關漢卿作王實甫續、王實甫作關漢卿續四種。就時間順序來說,以“王作”說出現最早,“關作”或“關作王續”說次之,“王作關續”說最晚。大致說來,從元代中葉至明代初年皆以為《西廂記》為王實甫作。換言之,在朱權(一三七八——一四四八)、朱有
“關作”或“關作王續”說大約是在弘治前不久出現的。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北京金臺岳家刊刻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的附錄里,收載了幾首〔滿庭芳〕曲(與《雍熙樂府》所載〔滿庭芳〕《西廂十詠》順序有所不同),其中有“漢卿不高,不明理性,專弄風騷,平白地褒貶出村和俏”和“王家好忙,沽名吊(釣)譽,續短添長,別人肉貼在你腮頰上”的曲詞。這些曲詞在貶斥《西廂記》作者的同時,也表露出“關作王續”的傾向。針對這種情況,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詩話》這樣寫道: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為首,俗傳作于關漢卿,或以為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實甫,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蕖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盛行于時。
都穆根據《點鬼簿》(即《錄鬼簿》)對“關作”或“關作王續”的“俗傳”做了明確的否定,重新肯定了王實甫對《西廂記》的創作權,并對王實甫加以介紹。都穆的看法,在當時是很有見地的,具有撥亂反正的作用。
“關作”或“關作王續”說之后,又出現了“王作關續”說。嘉靖三十七年,王世貞在其所著《藝苑卮言》中寫道:
《西廂》久傳為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為王實夫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黃花地而止,此后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為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廂》為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廂》,則亦可據。
王世貞正是根據朱權《太和正音譜》的記載,否定了“久傳”的《西廂記》為關漢卿作的說法,而重新肯定《西廂記》為王實甫作。但是,王世貞的做法并不徹底,他在否定“關漢卿撰”的同時又輕信了“王作關續”的傳說,認為第五本為“漢卿所補”。與王世貞同時,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顧玄緯所作《增編會真記雜錄序》也記載:
……知《西廂》作于關、董,而不知《錄鬼簿》疏云王實甫作。豈實甫、漢卿俱家大都而遂誤耶?抑關本有別者耶?今董記已刻之吳門,惟王四大出(本)外,或稱關補……
這兩則文字的記載是一致的。由此可見,“王作關續”說是在嘉靖末年才出現的。這與朱權、朱有
張國光同志之所以認為《西廂》五本不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的主張是從“周憲王”始,是由于他誤信了凌初的話。實際上,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