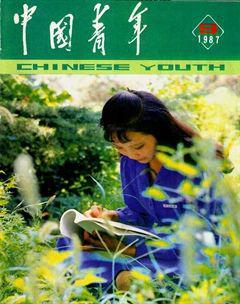不死的棕櫚樹(小說)
1
天依舊下著雨,雨依舊是那樣漫不經心,繭絲般
飄忽著。下課了,操場上卻空蕩蕩的。他兩肘支撐在欄桿上,點燃一支煙,頓時,大團淡藍色的煙霧濕漉漉地彌漫著,擴散著。
她從辦公室里走了出來。
“又下雨了。”他說。
“又下雨了。”她說。
不知什么時候起,他們開始喜歡起在這走廊里閑聊。談談天,談談地。她覺得這似乎是一種勞頓后的輕松,他覺得這可以沖淡些不知來自哪個角落的莫名的惆悵。
“都下了一個星期的雨了。好久不見太陽了。”“不,才六天。”她伸出一只手,屋檐上的雨滴滴在纖細的手心上,一個滾圓的水珠在手掌里來回地滾動。她得意地看了他一眼。
他淡淡一笑。
“小時候,我就喜歡下雨天,一下雨,我就拼命往外跑。奶奶說我是‘見雨癡。”她的臉上溢出孩子般的笑意。
“是嗎?”他問。
“你一定覺得很傻吧?”她側仰起頭,看著他。“女孩子,總是喜歡把什么都想象得十分美好。”他說得平平淡淡。“可男孩子,也不一定全把什么都看得那樣糟呀。”她反唇相譏。他回過頭,默默看了她一眼,然后猛抽了一口煙,將捏在食指和中指間的煙蒂扔到樓下。煙蒂在空中劃出一道漂亮的弧,跌落在一個水洼中。水洼邊有一棵枯死了的棕櫚樹。
她不再看他,那雙漂亮的眼睛注視著水洼中漸漸融開的煙頭。“你們學科又來了個新同胞?”她問。
他點點頭,“來來往往,就象是馬路上的過客。”
遠處汽車站,傳來公共汽車與人混雜的聲音。“大家一個勁兒地往城里擠,唯恐落后,似乎就只剩下了末班車。可總有那么幾個人趕不上趟,被孤零零地扔在了車站上。”他的聲音不緊不慢,似乎是在朗讀一篇枯燥無味的課文。
“這也難怪,我們校太窮,連獎金也發不出,再說,學校離城區又是那么的遠。”
“其實,窮,倒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是……”他沒有再說下去。
一陣風吹了過來。風是涼的,他打了個寒顫,“你沒覺得這里的風太涼了?”他說。
“你說什么?”她問。
“有些事最好不說明白。鄭老夫子說得好,‘難得糊涂,糊里糊涂反而會覺得輕松。”
“你什么時候改講哲學了?”
“不,這是生活。”“我不明白。”她搖了搖頭,還想說什么,但忍住了。幾個教師在辦公室下起棋來,圍觀的同仁們七嘴八舌,聲浪一股股的,從門的縫隙間傳了出來。他輕聲地噓了口氣,瞇起的雙眼只剩下一條細小的縫。朦朦的雨簾中,那棵枯死的棕櫚樹,垂下了片片的枯葉。
2
誰也弄不清這棵棕櫚樹在學校里生長了幾年,更搞不清它是什么時候枯死的。它挺立著,褐色的棕毛裹著筆直的軀干,枯葉盡管披拂著,可片片堅硬。“你說過,這棕櫚樹還是我們校的第一任校長栽種的,是這樣的嗎?”這天,她的興致特別的好。
他點點頭,并沒看她。
“聽說那校長死得很慘?”她問。
“他是在被批斗了三天三夜后,跳樓自殺的。頭觸了地,滿地是腦汁,當時沒有一個人,看守的學生們去睡了。第二天人們才發現了他。”他掏出一支煙,“他臉上什么表情也沒有,真奇怪。”他點燃香煙,大股的煙霧遮住了他的臉。
“他死了,他親手種的那棵棕櫚樹也死了,一個悲慘的故事。”她的聲音充滿了柔情。“這樣的故事太多了,何況時間又過去了那么久。”他把視線投向空中,天上有云,也有鳥兒。
“可我倒覺得,它是一種象征。它死了,可它還是站著。”她很認真地說。
他沒有什么表示,只是若有若無地嘆了口氣。學生們的嘻鬧一陣陣傳過來,一些男孩子玩著紙飛機、紙船,飛機在空中滑行,小船在水洼中晃悠,幾個女孩子在棕櫚樹下,來回地扔著沙包,毫無顧忌地笑著。
她仿佛受到了感染,“他們很快活。”
他淡淡一笑,“他們不知道這棕櫚樹的故事,他們不知道。”他又強調地說了一遍。
“我曾聽你說過,你要寫一篇小說,寫這棕櫚樹的故事。”她提醒著他。“我要寫小說?我說過嗎?”他有些茫然,好象是在回憶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是的,我記得你是說過的。”她肯定地點了點頭。
“不會吧,也許我忘了。”他不相信似地搖搖頭。“我有個朋友,也同你一樣,總是這樣恍恍惚惚的。”她有些失望。
“是嗎?”他象在竭力回憶,“真的,不記得了。”“這種恍惚,突然也成了一種時髦的東西。”她刺了他一句。“時髦的東西太多了。”他并不在意,平靜地看了她一眼。顯然,他不希望這樣的話題繼續下去。他們同時將目光投向天空。天空不再象以往那樣陰沉,但也不是那樣晴朗。沒有風,一團團的云朵凝固著,只是在這塊云與那塊云的中間,透出一點光亮。“聊天哪。”一個教師急匆匆從他們身邊走過,接著推門走進了辦公室。辦公室里傳來一陣不大不小的聲音,也許是在重述著某一件新聞,也許是在繼續某一個爭論。“一天一天的,時間過得很快很快。”他說得很輕松,嘴角卻不由自主地顫動了一下。“是的。”她也有同感,“還記得兩年前調走的小李子嗎?”“記得,一個快活的洋娃娃,跑到哪里,小喇叭就廣播到哪里,走起路來一蹦一跳的,就象一個小女孩。”他的話多了起來。
“你總是把人看成小孩。”
“還是小孩的好。”他對她寬厚地笑笑。
“人家都有孩子了。星期天,我在城里看見了她。”“一個洋娃娃,再帶上一個小洋娃娃?”他不置可否地一笑,“挺夠意思的。”
“她還是那樣一點沒變。”
“想象得出。”“那男的待她很好,她很滿足。”她說,“真奇怪,開始我們聽說那男的是搞體育的,起勁反對,現在想想,真是一點道理也沒有。”
“她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很多女孩子都會這樣的。”他感到兩肘撐在欄桿上很吃力,便直了直身子,做了一個深呼吸。“她很快活。”她強調著,“那時,我們在一起時,也是很快活的。”不知她又想起了什么,眼光迷離地瞧著那棵棕櫚樹。
3
白晝的時間,開始一天比一天長起來,可太陽還
是遲遲不肯露面。殘留的水洼象一面面破碎的鏡子,極安分地眨著眼睛。那些本已不見白色的墻壁,到處是一道道污穢的痕跡。
他依舊站在欄桿前,手里依舊捏著一根香煙。她向他走去,這似乎成了一種默契。
“昨天,我生日。”她說,臉上的表情很生動。
“哦?”他認認真真看了她一眼,“回家啦?”“沒有。”她說,,“昨晚,來了好幾個學生,是和他們在一起的。”
“快活嗎?”她肯定地點點頭,“他們跳舞、唱歌,還一定要我唱。”
“你唱了。”“唱了,他們很高興。”她伸手撩了撩額上的一綹頭發。光滑的前額上透出光彩。“只是當他們點燃了25根小蠟燭時,我才覺得自己是個大姑娘了。”她自嘲地一笑。“是的,25歲,不再是輕松的年齡了。”他并沒有去安慰她。
“4年了,完全是不知不覺的。”
“再過4年,你也會不知不覺的,生命就是這樣無為地運動著。”
她很掃興,不滿地瞥了他一眼。
他感覺到她的不滿,他想說些什么,可一時又不知說什么,“張靜上班了。”許久,他冒出這樣一句。“我碰到了她。”她覺得無滋無味,“病了3個月,她胖了許多。”“病?她母親可是個醫生。”他的語氣中,有一種讓人不舒服的嘲諷,“她想要的,終于得到了,校長已答應放她走。”
“她確實有病,她暈車。”
“是嗎?”他的嘴角嘻弄地咧了咧 。“只有它是永遠不會走的。”她的眼光移向了那棵棕櫚樹。
“那,你為什么不走?”他突然問。
“為什么要這樣問呢?”她反問著。
幾只雀兒在那一排水杉樹枝上嘰嘰喳喳地叫著,它們快活地從這根枝丫上跳到那根枝丫上,然后“撲棱”一聲飛走了。空空的枝丫在不停地抖動。
“連雀兒也不選擇它。”她有些傷感起來。
“它死了。”
“也許它并沒有死。”她說。“你真愛幻想。聽說,有個副市長的公子追過你?”他問。
“那是過去的事了。”她說,淡淡的。“你也是應該走的。”他的聲音里有一種疲憊不堪的味道,“她們都走了,你還留著干什么?誰也不會責備你。”
“我也說不清楚。”
“是因為那個故事?”他的眼光里流露出一絲迷惘。
“也許。也許不僅僅是這樣,我總覺得那棵棕櫚樹好象變了。”“變了?”他有些吃驚,“不會變。它還是和昨天一樣,明天將還是和今天一樣,沒有什么不同。”放學了,學生們象一群歡騰的雀兒擁出了校門。一個女學生走上樓梯,“老師,明天下午我們開班會,我們請你參加。”
“是嗎?什么主題?”她問。“‘我們的明天。你一定要來呀。”女學生甜甜的聲音。
“好,一定。”她愉快地答應了。
女學生急匆匆下了樓梯,去追趕伙伴們,在樓下她回過頭向她揮了揮手。“他們挺可愛的。”望著女學生歡快而去的背影,她說。“‘我們的明天?”他輕輕搖搖頭,“就同我們的昨天一樣。”“明天和昨天不會一樣的,就象她們和我們不會一樣。”她因為他的冷漠而有些掃興。
“你很樂觀。”他似乎什么也沒覺察到。
沉默。
“聽說你中學的時候,登過一篇作文,是寫當教師的理想的。”
“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很幼稚。”“為什么什么都要否定呢?連美好的東西也要扔掉?”
他的心里一顫,不由看了看她。她的眼光是真摯的,坦率的。他忍受不住,連忙躲避地回過頭,“我很感激你,那確實是一段美好的回憶。”
“我不明白,你為什么要躲進一個貝殼里,把自己嚴嚴實實地裹起來,這高深莫測嗎?”“這……”他第一次結巴起來,一時無言以對,心里有有些惶惑起來。“天都已暗了,再過一會兒食堂就沒晚飯了。”她說,腳步遲疑著。“是的,你該走了。”他感到站著的姿勢很吃力,便干脆伏在了欄桿上,“又一天結束了。”他顯得有些木訥。
她走了,皮鞋聲敲打著空蕩蕩的走廊。他又點著了一支煙,呆呆地看著那棵棕櫚樹,眼光漸漸呆滯起來。
4
太陽出來了,圓圓的,紅紅的。校園的一切變得明朗起來。
“太陽出來了。”她高興地說。
“太陽出來了,可它不屬于我。這好象是《日出》中的臺詞。”陽光并沒有能夠驅散他臉上的陰沉,他的眼睛老是看著空中的某一處,象一尊石膏塑像。“太陽是不會疏遠誰的,永遠不會,除非你拒絕它。”她的聲音很慢,但很堅定。
“太陽出來了。我要結婚了。這不知究竟是一出好戲的開頭,還是結束?”他漠然一笑,臉上的表情很古怪。“噢?”她心里“怦”地一跳,“那女的是誰?”她下意識地問。
“她是我小學時的一個同學。”他很是心不在焉。
“是青梅竹馬?”她低低地問。“不是,是別人介紹的。她說,小學時曾和我同座過,可我不記得有這么回事。”他看了看她,“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是的,有些奇怪。”她老實地承認。
“其實,人生是很簡單很簡單的。”
她的心開始平靜下來,“那你也要走了?”“應該是。但我不知道這有什么意義。我就象一個地道的木偶,聽憑擺布。”他苦笑了一下,“干脆做木偶倒也覺得輕松。”她陌生地看了看他。“萬綠萌芽了。”她說了句無關緊要的話。“是的,萌芽了。”他也感覺到了她的陌生,神情更加凄惋,“但秋葉呢,那腐爛了的枯葉呢,有誰會記得它們嗎?”他將目光全部匯聚在她的身上,隨后邁著重重的步履走下樓梯。
她覺得那目光里,有許許多多的東西,但又象什么也沒有,很虛飄。她依在欄桿上。水杉樹枝間,跳躍著點點的嫩綠。無意中,她的視線移向了那棵棕櫚樹。她驚訝了,她看到那棵棕櫚樹的樹梢上,竟也冒出一點綠色,同她以前夢中見到的一樣。她急忙走下樓梯,奔到棕櫚樹前。實實在在,一點綠色呈現在她眼前。頓時她歡欣起來,“它沒有死,它還活著。”
她相信這是真的。
作者簡介:金陶,原名陶曉躍,29歲。江蘇省南通市第五中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