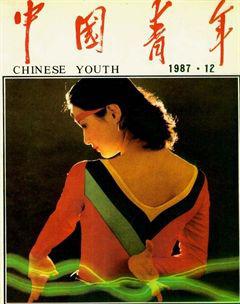中國大學生理論熱
東升 光輝 棟林
謹以本文請教于所有關注理論的大學生們和所有關注大學生的人們。
熱的冷卻與冷的發熱
1987年前后中國一大文化現象
對于中國來說,大學生有著特殊的意義。1919年以來,中國大學生幾度領導思想文化新潮流。他們中出了一批普羅米修斯,馬克思主義得以在中國傳播。他們中更不乏熱血沸騰又清醒冷靜的實干家,喚起民眾變革中國。那么,今日中國大學生又是一種怎樣的思想風采呢?
幾年或者幾個月前,他們還是中學生,他們還在高考的重壓下氣喘吁吁、苦不堪言,多情瓊瑤、浪漫三毛成了他們情感的消遣和撫慰。那么這些小蘿卜頭小馬尾巴進了大學以后看好什么呢?
幾年以至幾十年前,尼采、叔本華、弗洛伊德等等就在中國的大學里熱過,當然也冷過。那么這些藍眼睛高鼻子在今天的中國大學生中境遇又如何呢?
消息一組:
1987年5月27日,首都第三屆社會科學書市隆重開幕有關哲學、思想理論的著作暢銷不衰。購書者以大學生為多。
據《人民日報》報道,今年某日北京大學新華書店上架2504冊《自卑與超越》,當天全部賣完,第二天再進1000冊,天黑前又被一搶而空。
上海、杭州、成都、武漢、沈陽等地也紛紛傳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當代學術思潮譯叢》《拿來叢書》為大學生爭相搶購的熱門書,弗洛伊德、尼采、薩特著作行情看漲。
在復旦大學,知名學者李澤厚和知名度稍低的青年學者張汝倫同時開設哲學講座,這邊走道里都擠滿了人,那邊則把喇叭架到了外面。
在許多院校,學生自發組織了“理論沙龍”“《資本論》研讀小組”“馬克思讀書會”……
對北京、四川、湖北等地幾十所高校學生的調查結果:
——您近年讀得最多的書是哪類?回答是理論書的占37%,超過小說類(34%),居第一位;
——對您最有影響的是哪類書?回答是理論書的達45%,把小說、教科書等遠遠拉在了后面;
——閱讀社會科學方面理論書籍約占您課余讀書時間多少?24%的同學回答在1/2以上,53%的同學回答在1/2至1/5之間,只有22%回答在1/5以下;
——您對理論的興趣如何?回答說沒有興趣的占10%,興趣一般的33%,而興趣濃厚和較濃厚的占53%。
……
弗洛伊德熱,尼采熱,馬克思列寧原著熱……中國大學生理論熱!這是1987年前后中國又一個突出的文化現象。受不了。不過癮。莫名其妙。發熱的人們顯示著種種的興奮與困惑。而面對熱,人們也產生了種種的困惑與興奮。
饑渴·反思·沉悶的打破
一直被視為熱情有余冷靜不足的這批小大學生怎么對深奧的理論有了如此大的興致?一度被看作冷門的理論何以一時間又具有這樣大的熱力?
對大學生的思考:他們大多是60年代來到人世的。他們背上書包不久正好趕上“否定文革”。思想開禁,對外開放,形成一個從未有過的活潑繁雜的文化氛圍。這大角度的轉變,激動了一代青年,有的中學生躍躍欲試,想涉足其中。但他們畢竟為年齡和文化所局限。況且,他們還要準備高考,要把課余時間也用在功課上。他們無暇擠入那個氛圍中心去看個究竟。
考上大學是個轉機。掙脫相對封閉的中學生活和沉重的高考壓力,他們進入了思想活躍的高等學府。長長地噓一口氣,他們開始接觸五花八門的中外文化,開始探究以前未曾探究的課題:人生,自我價值,人際關系,社會變革……原先的一片思想理論空白,這時成了一塊貪婪汲取的海綿。用武漢大學哲學副教授李曉明博士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文化饑渴。
大學生的思考:學潮以后,大學生形象是個問題。社會上有人說我們膚淺,只知道上街,不懂得理論,沒有多少思想。我們也在反思。我們到底是不是膚淺?又甘不甘于膚淺?
舞臺上的輕歌曼舞,舞場上的飛流旋轉,運動場上的龍騰虎躍使我們的課余生活顯得多姿多彩。然而,當我們看到我們的課余生活整個地就是如此這般的時候,不免有一種凡俗平淡之感。我們應當同時有著更高標準更高層次的活動!因為我們的使命在于用理論之力驅動社會之輪,用理論之舵駕馭社會之舟。
對大學生理論熱的思考:1978年以后的中國,被“文革”革了命的一切都在復蘇之中:經濟、文化、社會生活……而過去所堅信不疑的一切又都被擺到了審視的位置:階級斗爭學說、繼續革命理論……中國是在一次大劫難之后,人們痛定思痛,由痛苦而懷疑而重新評估一切,這是自然的。中國又是處在一場大變革之中,變革的現實對理論的單一沉悶提出了挑戰,人們也急切想用理論之光來觀照變革的現實。
前些年的大學生“薩特熱”和時下的大學生理論熱都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產生的。如果說前者更多的是對傷痕的反思,那么后者則偏向于理論和整個文化的重建。如果說前者更多地是在呼喚人性人道上和人本主義思潮取得某種程度的精神吻合,那么后者則更關心人的發展尤其是作為個體的人——自我的實現。而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幾年商品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平等、競爭、多樣化的觀念,竟然也悄悄改變著人們對理論的態度。
疑惑,自我,多元……如此理論熱,是喜?是憂?
60年代,中國也曾有過另一種理論熱。不懷疑,不介入自我,人人都背育那么幾條紅色理論,結果導致了一場極缺乏理性的狂熱“革命”。不輕易相信什么,主體意識的覺醒,多樣化的選擇接受……80年代的大學生理論熱,無論如何有著一種歷史進步的的意味。
十年狂熱的冷卻,凝成了對文化(尤其域外文化)的巨大熱情,于是,被冷落十年的文化和文化研究變為熱門。老三屆大學生便是這文化熱中的活躍分子。
學潮狂熱的冷卻,進一步激發了小大學生們對理論的熱望,給過去冷、當時正熱起來的理論又來了個快速升溫,于是,大文化熱中又生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旋渦——一大學生理論熱。
吞食之勢與消化能力
女式長發與弗氏理論之關系
四川某學院某男生,蓄一頭特長披肩發,從背后看象個女的,從前面看則不男不女——還有一撮黑須。同學問他,你留女式長發為的啥子喲?他反問同學:“你看過弗洛伊德的書沒有?”“看過。”“弗氏說,靈感的產生要聽其自然發展。頭發長在頭上,與靈感有關。我先得叫頭發自然發展。”聽者語塞。
無獨有偶。北京某大學某女生讀了幾本尼采后,如癡如醉,一個人擅自離校出走到敦煌。尼采“重新評價一切”,她則對社會橫豎看不順眼。尼采寫超人,她也寫超人,并且真的超了人,著奇文曰:我是狗。結果被校方勒令退學。
近年來域外文化大量介紹過來,滿足了人們特別是大學生們的文化需求。但同時問題也突出了:長期文化饑渴后的文化大會餐,容易撐死人。西方各種學說,帶著許多的新鮮,也夾雜著不少謬誤進來了。接受它的人們不見得就有審度能力和消化能力。
在這頓文化會餐中,饑不擇食,生吞活剝,對新概念新術語的隨意套用,對西方理論的盲目認同……小齡大學生在文化上的靈敏度高選擇性差又一次充分顯示。至于理論內部的各種歷史的和邏輯的聯系、價值尺度,理論分析的特定背景,各種理論之間的關系等等,不少學生并不了解,也來不及去了解。這就造成了文化接受上的消化不良癥,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有的學生看了兩種觀點截然對立的著作,都覺得挺有道理。
懸在讀書人頭上的問號
讓我們再看大學生理論熱中出現的癥狀三種。
趕時髦癥。“人家有了,我也得去買;人家在看,我也趕緊看。否則,人家吹牛我就啞了。”吹牛、砍大山,這是大學生尤其是低年級男生的一大活動項目。“回到寢室一砍,大家爭得面紅耳赤,實際上不是兩個學生在爭辯,而是這本書和那本書在交鋒。懂點皮毛能吐幾個新詞兒也好,要不顯得我知識老化。”不是為了汲取養料、豐富自己,僅僅為了表白自己知識結構新,看起來和吵起來都不跌份,終究不能份到哪兒去。牛皮吹完以后呢?
借酒消愁癥。在上代人看來,這撥娃娃夠有福氣的了,可這撥娃娃中苦惱、憂愁的卻大有人在。在不少“苦惱人”眼里,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親切得要命。山東大學一位女生寫道:“抽刀斷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這兩年的大學生活該如何度過呢?我只有拼命看書來消散自己的憂愁。”借書消愁,書不也成酒了么?一個苦惱人很難從《愛與生的苦惱》中找到消愁良方,倒有可能消極厭世。
偏狹癥。少數學生讀了一些西方理論書,不看現實情況的差異,也不管書中的觀點是否片面,便與中國實際簡單掛鉤,得出一些偏狹錯誤的結論:“中國是權力社會,日本是技術社會,美國是能力社會。”“技術決定一切,不要研究什么主義不主義了。”顯然,這種“理論聯系實際”法是很難符合實際的。趕時髦、借酒消愁、偏狹以及消化不良,都有一個如何對待域外文化的問題。是本著理性分析的態度,還是聽憑感覺與喜好?是立足現實選擇,還是盲目地套用搬運?這些問號同樣也懸在全國450多家出版社的門口。問卷調查表明,大學生對域外文化的需求還是很高的,56%的學生認為西方學術著作進來得還不夠。是僅僅把文化需求作為發財機會,粗制濫造、胡亂編譯呢,還是審慎負責地向大學生們介紹新知?我們都知道魯迅的拿來主義,然而我們是否都認真思索過“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這幾個字?這可是先生要求拿來者首先具備的素質呵!
關于馬克思不死的一個理論故事
本世紀60年代末,法國出現了一個“新哲學”流派。“新哲學家”站在反對理性、反對一切科學理論的立場上,對馬克思學說竭力攻擊,他們有句口號:“馬克思已經死了”。他們想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價值,又拿不出任何有力的分析,他們的手段只有謾罵和詭辯。
馬克思沒有被罵倒,倒是非理性主義越來越顯出生命力的不足。非理性主義思想家紛紛向馬克思主義“靠攏”,力圖“結合”。新精神分析學派的弗洛姆稱馬克思是一位“更加淵博、更加深刻的思想家”,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則承認,馬克思主義遠遠沒有衰竭,還十分年輕,它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薩特替這個理論故事收了尾:馬克思不死。
對思想和思想家的選擇打勾
記憶猶新的一段不算短的時期,我國曾在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一再失誤,我們的社會科學理論可塑性大、科學性差,這使有的青年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逆反心理。
在讀了點馬克思原著之后,一些學生發現:原來我們對馬克思學說并不了解!
是的,不了解。毋庸諱言,大多數大學生原先接觸的只是教科書上的馬克思主義介紹,而我們的理論課又介紹得不夠成功。不少教科書不是經典作品的精華匯集,而僅僅是抽象教條的精包裝。現狀是一方面精裝真理銷路不好,另一方面學生對樸素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知之不多。
從精裝真理那里,有的大學生得到這么一個印象:馬克思忽視人的問題,不象尼采、叔本華那樣關注人。看了馬克思原著,又有了新的印象:馬克思不是不講人,恰好相反,他是主張改造人生存和發展的環境——社會,從根本上改變人的地位,確立人的價值,實現人的真正解放。
這樣的印象改變不止一次,更不止一個人。——沒讀馬克思的時候,光聽幾十年一貫制的照本宣科,覺著乏味,等看完了《反杜林論》再想,馬克思思想是挺精彩的。我們對低年級同學開玩笑說,先別罵,看完了再說。——比較來比較去,要講真理性,還是馬克思學說最強。前些年,馬列著作一度滯銷,有的書店按斤收費。而現在好多地方馬列著作供不應求!在今年9月的一次大學生問卷調查中有一題:您最推崇的思想家是哪三位?結果,63%的同學投了馬克思的票,大大超過了對其他十幾位“候選人”的“投票”數。另一題:您覺得哪種理論對中國進步最具指導意義?結果,馬克思主義的得票也是第一!
不記名,不會影響入黨和畢業分配,在沒有任何顧慮的情況下表露看法,讓他們在比較后選擇打勾,這是否也開了我們思想工作的第二種思路?
馬克思學說本身就是發展的、開放的,它對任何一個新的科學發現都不會排斥。列寧有句很精辟的話:“在馬克思主義里絕沒有與‘宗派主義相似的東西,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英國學者約翰·斯特拉奇則提出了這樣的“假如”—假如恩格斯再活二十年,他大概不會不研究弗洛伊德的著作。“恩格斯既然不忽略達爾文或摩爾根在生物學或考古學上的發現,也便不會忽略弗洛伊德在心理學上的發現。這老鷹也將猛撲這種新的材料,加以消化、批評和揀選。”
在近十年中國大學里,原先有一種傾向,只要馬克思,排斥非馬克思。后來又冒出種傾向,非馬克思吃香,馬克思不吃香。現在呢?重新選擇馬克思,但不拒絕馬克思以外的思想成果,也成了一種傾向。
對于理論,許多大學生已經或正在發生認識上的變遷與深化。
對馬克思的第二次或第一次認識
在重新認識理論的過程中也重新認識理論家。多年來,人們(包括大學生們)從“左”色濃重的理論宣傳上看到的馬克思,是一個絕對思想權威。宣傳者不允許人們對馬克思學說有絲毫的疑問。
當大學生在宣傳之外翻開厚厚的馬克思原著,包括馬克思寫給燕妮的那些情詩時,他們驚訝了:馬克思的思想并非象宣傳的那么干巴,他的話既深邃也生動,馬克思原來是如此富于感情,他和我們一樣是個血肉豐滿的人!
這才是真正認識馬克思的開始!很長一個時期,不是馬克思僵化了,而是宣傳僵化了。一旦擺脫僵化,一個偉大而親切的馬克思便來到了人們中間。
從絕對思想權威到學者,從作為神的馬克思到作為人的馬克思,這是大學生認識上的又一次變遷和深化,也給我們的宣傳以某種啟示。
解:理論是灰色的
有問題問書,問書也有問題去問誰?
大學生一遇到問題就翻書,尋找答案,我這樣,我所熟悉的同學大多也是這樣。
——摘自西南師大一位學生的談話。
二十歲左右的大學生頭腦里的為什么最多,這不光是因為他們敢想敢懷疑,還因為他們的年齡和經歷都決定他們是單純甚至于單薄的,而社會(包括學校)的矛盾沖突卻是種類繁多。
帶著現實的題目,他們尋找理論,然而理論每每不能給他們以確切的回答。在大學這個文化集散地,種種新的舊的國內的國外的理論流派、社會思潮在匯聚,比較,沖突。他們什么都讀。奇怪的是,不少人“越讀越糊涂,讀得越多,越不知道怎么回事”,反倒多了一個理論的困惑。
問書也有問題去問誰?
生活!
還是學生自己解了題。現實的困惑,到理論中求解;理論的困惑,到現實中求解。從理論熱到社會實踐熱。一切順理成章。
“把自我給找回來了!”
歸來的詩:
我們從自己的小巢走出。
我們象第一次睜開眼睛。
今年暑假,大學生們紛紛打點行裝,走向社會。自發的。有組織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規模空前。
近距離觀察現實。全身心投入生活。在社會實踐中,他們聽到了老教員的肺腑之言:“三中全會解放了我們”,也聽到了企業改革者的呼聲:“大道如青天,吾獨不能出”;看到一位居民為防鹽漲價而儲鹽一萬袋,也看到農民的三個發展動向——純農、半農、出租農……
他們重新思索,思索學潮和理論熱中曾經思索和沒有思索過的問題。
——共產黨為改革和建設付出了艱苦努力,我們關在校園里談“全盤西化”“絕對自由”是不切實際的,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國情。
——一個大學生不懂點馬克思薩特馬斯洛不行。只懂點理論也不行,理論畢竟不是我們的目的。
——以前總覺得自己是社會的棟梁、精英、“夸夸其談一大套”,“關在屋里指江山”,一接觸實際才發現自己的思想、知識、能力與實現需要相距其遠。
——社會實踐告訴我們:需要喚醒的首先不是民眾,倒是我們自己。面對貧窮落后的現實,我們只能按照社會發展的需求來設計自我,才能夠形成有社會價值的個性。
他們在社會實踐中重新發現自己。
“學潮后總覺得人們不理解我們,心里不平得很。”西南政法學院幾位學生到農村講課,正在田里施肥的農民們一聽大學生進村,放下糞桶就來迎接。在熱情和信任的眼睛面前,大學生們找不出合適的話來。
曾在西方思潮中迷失自己的學生,實踐歸來寫小結,落筆便是:“這次活動我把自我給找回來了!”
找回來的又豈止是一個自我?
從第四條路看“熱”的主人公們之走向
在大學生中曾流行這么一個說法:畢業后的主要出路有三條,第一條是考研究生——出國留學——拿博士學位,博士帽是黑的,故稱黑路;第二條是入黨從政,政治上走紅,叫紅路;第三條是搞經濟實業掙大錢,黃路。還有學生對三條路作了比較研究:紅路名利雙收,但不好走;走黃路名聲不如黑、紅;走黑路名聲不錯,競爭太厲害。
社會實踐熱中,很多學生(自然也有聽說過三條路的)提出畢業后要去農村企業搞科技,要回家鄉去執教鞭,甚至于有志愿教小學的。這又算哪種顏色的路呢?沒法說。說無顏色或全顏色大概都可,反正是第四條路。跟前三種路的說法不同在于,它把自我引向社會需要。每條路上都能殺出好漢來,而第四條路的意義在于,別具一格,開闊宏遠,預示著某種方向。
在大學生中有一副對子幾經變更,上聯“風聲雨聲讀書聲”由原來“聲聲入耳”到后來“聲聲不聞”,如今再度“入耳”;下聯“家事國事天下事”由起初“事事關心”到后來“事事不問”,到現在又變為“關心”了。
第一次變更是在學潮剛剛過去的時候,第二個修改稿則脫手于大學生理論熱和社會實踐熱方興未艾的當口。從半頹廢心境走向全方位的思考和實踐,對于中國來說,這代大學生的思想走向有著特殊的意義。
(題圖:盛靈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