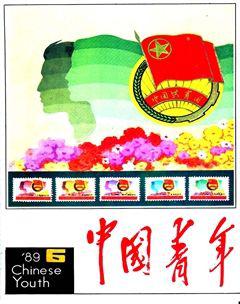不要再“繞”下去了(我的觀點)
許多朋友誤以為我是專門研究現代藝術的,好些畫展的主持人還寄來請柬,希望我能對許多實際上對我來說還相當陌生的現代藝術發表意見。其實,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中人”,我的本意只是想借個話題對自己這些年來紛亂的思考作一點清理——還遠不是認真的清理。
我感到需要“清理”主要源于這樣一種經歷背景:身在此山中,有時卻不知山為何物;一旦置身域外,一只跳出井圍的青蛙驀然被各種新信息的汪洋大海所淹沒,被單一所扭曲的人格心態很快又被龐雜扭曲了。比如,什么叫“現代觀念”就是一個把我攪得糊涂又糊涂的問題。我一度和許多人一樣認為:一些無人說過、讓人費解的玄虛之辭,就是“現代觀念”。只要運用了“意識流”“情節淡化”“無標點符號長句”等新巧手法、形式,作品就有了“現代感”。基于這一類糊涂便派生出另一“檔次”的糊涂:我們在海外求學的文科學生,常因很快學會在自己的讀書報告里堆砌許多新術語而自鳴得意,然而冷不防間卻又被導師或同學的一類評語當頭棒喝:用玄虛高深的理論術語去重復一個實踐中膚淺簡陋的命題。這才發覺,自己的思考仍在原來的思維范式里踏步。漸漸,在許多學術場合也發現,我們中國學生、學者常有意無意地忽略問題的大前提,在大前提遠未論清的情況下便做起“大塊文章”:在一些本來還糊涂的概念上“繞”出許多堂而皇之的“理論成果”。“繞”功雖高,卻是“信息量等于0”。我以為這一類的學術性格、思維習慣所反映的是一種文化心態。記得有一回討論“中國通俗文化”,合作此書的三位美國學者詳細介紹了他們各自對“中國”、“通俗”、“文化”三個基本概念的不同界定和相互整合的過程。我當時很驚訝:“這三個日常的、基本的概念,難道還值得如此費力地去界定么?”按“我們的”慣例一定會作“大而化之”的處理的。答曰:“正因為‘基本,才需要明晰。不同的‘基本理解,可以作不同的立論。‘基本不明,怎么討論呢?‘基本不能討論,后面能做什么文章呢?”
這一席話確使我茅塞頓開。其實,什么是“現代的觀念”?現代藝術的“精神內核”是什么?或者說,它最值得我們珍惜、汲取的是什么?在今天我看來:現代主義藝術的真正價值,不在于它形式的、術語的、技法的意義,而在于“思想”。即對宇宙間普通的、司空見慣的、已成“真理”、“公理”、“慣例”、“基本”的那些東西,在別人說過千萬遍的話題,換個角度重新去看——“現代觀念”者,便是重新面對“基本”問題,在“基本”問題上重新發言。
細細想來便可發覺:今天我們之所以有那么多越攪越糊涂的問題,并不在于缺乏花巧的理論名目和多變的實踐對策,而是我們已習慣于在“基本”不清的情況下大做文章,或在“基本”不能討論的態勢中強做文章。有時并非刻意欺世,而是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直面基本問題”的能力。多年來的政治動亂造成的文字敏感癥和政策多動癥,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在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的同時掌握了一樣萬能的“糊口”法寶——“繞”。繞著說,繞著寫,繞著想,繞著干,形成中國知識分子以“繞”為特征的思維范式和文化心態,以至把繞出來的糊涂帳真誠地看作客觀事實本身、理論“原生態”或真理本身了。
多年來,“繞”的思維積習已經使整個知識界不自覺地陷入一種“怪圈”——“大前提”不清的各種論爭,像打擺子一樣陣發性地困惑著文化思想界;理論批判的出發點常常竟然變成理論完成的歸宿點——這才是一場真正深刻的危機。
從“文化熱”到“《河殤》熱”,再到“新權威主義熱”,就是順手拈來的例子。“文化熱”,本來是一場富于現實感的討論,但卻為了稍稍把思路繞大點,讓沉重的現實話題在文化上“軟著陸”,以避開過于敏感的現實社會、政治話題。一“繞”之下,諸“熱”紛起。知識界忽然眾口一辭,似乎文革以來中國面臨的一切問題,真的成了“文化問題”。“四人幫”與“打砸搶”的前因后果都得歸咎于孔夫子或秦始皇了。《河殤》一熱(《河殤》自有獨特價值,這里不提),便把“文化問題”簡化為“土黃色”與“蔚藍色”的文明光譜問題。“三十年”隱去了,“一百年”淡化了,突現于觀眾眼前的是感傷而玄虛的“五千年”。“五千年”成了“文化熱”祭壇上的羔羊。隨后“新權威主義”、“開明專制”等“理論建樹”又熱熱鬧鬧行動起來。本文無意細加“臧否”,只略略感到“汗顏”:以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為發端的“文化熱”,最終繞出個建立“新權威主義”的“文化實績”。這個圈子實在“繞”出了經典性的悲喜劇水平:彎彎繞的“文化熱”導出了一場精神的“理性倒退”,退回到“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之前。
——不要再繞下去了!與其殫思竭精地用精妙語言為“開明專制”架構“新權威主義”一類的理論營壘,不如還原一點“知識分子”獨立、自尊、批判、理性的屬性,以同樣的聰明去對被自己繞糊涂的眾多“基本”前提作一番認真的清理,問一問:哪些“基本問題”是繞不過去的?該怎樣重新面對“基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