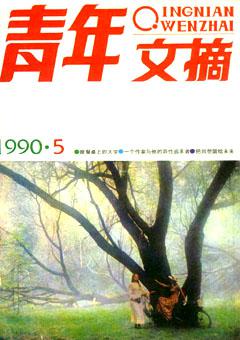三姐妹的命運
徐 然
本文是我的母親,著名女作家楊沫告訴我的一段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有關她和她的小妹、著名電影藝術家白楊、已故的二妹楊成亮的事。
我外祖母是個出身書香門第、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在清朝末年就讀于長沙女子師范學校。
外祖父是個書生,和外祖母結婚后,日子過得極匆忙。在京都大學堂畢業后,他到南洋募捐,名義是置辦校產,實際到手的錢卻用來買地,兼做起收地租的地主,后來竟自顧過紙醉金迷的生活,根本不顧家了。外祖母曾同迷戀于玩樂的外祖父爭吵不休,丈夫惡習難改,她自己只有自嘆命苦,喪失了生活信心。后來,她整天和一些闊太太們打麻將,看戲,以此消磨打發歲月。外祖父和外祖母,誰也沒有心思撫養教育自己的兒女。就是在這樣的精神廢墟上,我的母親楊成業(楊沫)、二姨楊成亮、三姨楊成芳(白楊)出生了,長大了。
母親在三姐妹中最憨,快3歲才吐字說話,這也許是她特別不受外祖父母喜愛的原因。外祖母曾把她送到親戚家寄養,直到8歲上學時,母親才回到自己家。可是在家她仍象個孤兒,冬天,腳上凍瘡流著膿血,下了學,竟常和一些孩子去揀煤渣。
二姨是三姐妹里的美人兒:聰明、能干、潑辣,真正是外祖母神情畢肖的女兒。
童年時代的媽媽和二姨的性格截然不同。在生活極不順心情況下,外祖母的脾氣是極壞的,對孩子更是伸手就打,張口就罵。一次,外祖母出門,來訪的朋友把她心愛的花瓶拿走了,傭人怕擔責任就告訴夜歸的太太,說是大小姐成業讓拿走的。外祖母氣勢洶洶地趕到女兒和下人居住的臥室,不問青紅皂白,就在熟睡的孩子的腿上亂掐亂咬。我母親在睡夢中被劇痛刺醒,這個挨慣了打罵的女孩子,竟是一聲不吭,甚至連淚水也不落。二姨則不然,外祖母把她的胳膊掐青了,她會惡狠狠地告訴人們,這是“狗咬的”!
三姨比二姨小2歲。她在北平小湯山的一個佃戶家寄養。直到9歲了,外祖母才把她接回來讀書。而這時,家已處于沒落境地——那是1931年,外祖父因為破產棄家跑了。
無論家境如何,這個家庭畢竟書多,來往的文人多,母親沒進學校,卻已認得許多字。上學以后,對讀書的興趣越來越濃,把家里給的零花錢大都用在了書攤上。10歲時她就讀了《紅樓夢》。
1931年的母親已是17歲的少女,她就讀于北平西郊的溫泉女中。她有一雙清亮如水的大眼睛,浸潤著聰慧和深沉;她身著一件士林藍布衫,白鞋、白襪如同《青春之歌》中那個可愛的林道靜。
那年春天,風沙彌漫。一天,女中教務長通知說:“楊成業,你母親捎信來了,有急事讓你馬上回家”。
回到家,外祖母臉上竟然綻出對這女兒一向吝嗇的笑容,說出許多動聽的話。母親先是吃驚于自己媽媽少見的柔情,繼而,終于明白了這溫柔的表演只是為了逼她嫁給一個有錢的舊軍官。
中學時代的母親讀了不少文學著作和作品。她早已恨透自己父母的寄生生活,她渴望走上一條有意義的道路,盡管還不知道路究竟在哪里,但她絕不會為生活得舒適而去做舊軍官的玩物的。她的同學于雯曾和她一樣喜歡文學,她倆常一起閱讀世界名著,暢談理想,可惜,這雯姑娘奉父母之命當了軍官的姨太太,終于墮落、毀滅了。這件事對母親刺激很大……于是,這個一向默默無言的女子拒絕了她母親的如意算盤。當時,震怒的外祖母立刻翻臉怒罵,聲言絕不再出錢供不孝女兒讀書。
母親知道外祖母辦事專橫,向來說一不二,便毅然離家出走了。《青春之歌》的開篇中,那個全身素白,帶著一堆樂器,有一雙憂郁眼睛的女孩子,應當算是母親脫離剝削階級家庭,邁向新路的寫照。那時候這個寧折勿彎的少女才17歲!
年輕女人自立的路是極其艱難的。母親的職業時斷時續,肚子時飽時饑。她當過鄉村教員,給日本人學生當過華語教師,也給資本家少爺小姐當過家庭教師。那些年失業后,生活窘迫,甚至把穿在身上的衣服拿到當鋪作押換點伙食費……她曾應朋友介紹,準備去給國民黨的一個小要員家當家庭教師。一進門,便見到那銜著雪茄,坐在沙發上的家伙不懷好意地笑,從上到下地打量,接著說:“可以,年輕的女人,好說,好說!”母親一看那個人那副樣子很生氣,憤怒地走出了那紅漆大門,她寧可餓死,也不能受這些惡人的侮辱。
家庭的破落,使年幼的二姨三姨也不得不考慮生計問題。1931年秋天,漂亮的二姨告訴她的小妹,聯華影業公司要在北京辦電影演員養成所(即訓練班),她要報名。并不經心地掃了一眼呆呆聽她說話的小妹妹,加了一句:“給你也報上吧。”
考試那天,三姨歡歡喜喜穿戴整齊,一心巴望姐姐帶她去,左等右等,出門的姐姐總不回來,年幼的三姨憑依稀記得和姐姐報名時的路線,獨自摸去了。主考官被她那雙透著天使般的單純、潔凈,神采奕奕,黑白分明的眼睛所吸引,三姨由此而踏入了她為之獻身的電影表演事業。
遺憾的是,那天,喜歡唱京劇的二姨被票友拉去“下海”了,早把考試的事兒忘在腦后,多么遺憾。不加約束,過于浪漫的二姨失卻了這一次或許能改變她命運的應試。
還是在1931年。這年年底,外祖母去世了,這個世界上只留下孤單的三姐妹。
時隔2年的大年夜,母親到宣武門頭發胡同三姨住的一所公寓內準備和小妹共度除夕。那里正聚集了一批熱血青年,他們為祖國的命運憂戚,悲忿地低聲唱著:“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那一夜,母親在無望的彷徨迷離中,象是驟然看到了希望之光,由此,她結識了一批共產黨人。
在蘆溝橋炮聲隆隆的時候,母親和三姨已到達上海,一對姐妹面對國家危亡,鄭重地考慮著彼此的責任。為了藝術,三姨到大后方重慶去了,以后主演了反映抗日戰爭的巨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母親在與妹妹作別后,毅然奔赴抗日革命根據地,歷經千辛萬苦,到達冀中安國縣,在那里打游擊,鉆地道,并握筆描摹著中國人民抗擊日寇的壯偉斗爭。直到1949年,這對姐妹才重逢于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至此,萌生在舊中國精神廢墟上的兩株稚弱的小樹才真正成材,靠著她們頑強不息的那種精神。
這兒,讓我們再提及一下那已被人們遺忘了的三姐妹中最美麗的佼佼者吧。這是母親講給我的又一個動聽又悲涼的事情:
1932年,僅僅14歲的二姨已經長成花兒似的大姑娘。她認識了一個姓駱的法官,那人垂涎于二姨的美色。誘惑她隨他赴任職的長春,二姨成了他的姨太太。兩姐妹久久得不到她的音信,直到“七·七”事變前,她才寫了封短信,并附小照一張——照片成了母親、三姨留存的唯一一張二姨的照片。信上說,她生活得很苦,不愿再在長春住下去。那一紙短短的信箋,沒有說清楚苦的內容,然而,小照上那雙凄清如水的眼睛,足以讓兩姐妹品味出她心房的一切悲苦。母親她們等待她的歸來,她們等啊,等啊,卻永遠沒有等到。
直到近年,由一個偶然的信息,母親和三姨才得知,二姨已在1938年去世。這年,距她對姐妹們訴苦僅幾百天光景,她只活了20歲。她死得無聲無息,也沒有留下一句遺言。
母親三姐妹的命運使我不能放下思索:三姐妹乃一母所生,而結局為什么又那么不同?原本,外祖母賦予她們的自身條件,差異并不懸殊,二姨媽則更得天獨厚一些,不是嗎?當初去華聯影業公司報名的本是二姨媽呀……
“沒有神仙皇帝,掌握自己命運的只能是自己!”這就是我聽母親娓娓敘來故事后的唯一想法。在舊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感到祖國前途、個人前途都茫茫一片,在苦悶,彷徨,女青年又多一層婚姻問題。這些人中,有的在失望中掉隊了,然而總有一批人在不屈不撓地英勇斗爭著,奮進的人永遠值得歌頌。也許因為自己是女人,深知做女人的艱難,故此,更偏愛那些自強不息的女性。
(沙中草摘自《中國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