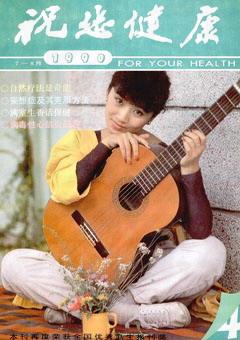面對“猝死”的挑戰
李宗浩
現代急救醫學事業的發展,與人類壽命的增長、生活節奏的加快、現代化程度的發展、交通運輸的多樣化相關,是由于意外災傷事故和各種危重急癥明顯增加而作出的一項重要對策。
“猝死”帶來嚴重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材料說,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約有40~60%因合并癥而在發病最初的幾小時死亡;有70%的發病者因來不及送到醫院而死于現場。在2億人口的美國,每天就有3千人發生急性心肌梗塞,每年因冠心病死亡的約70萬人,而一半是屬于冠心病猝死。莫斯科配備的600輛救護車,分配在22個急救站,有6千名急救員,他們2/3的任務是奔波在搶救心臟病的現場和途中。北京的心腦血管病死亡率竟占到疾病統計死亡總數的一半。
聯邦德國的一份報告指出,有2/3的傷員死于交通事故發生后的25分鐘內。近些年來,關于大型客機的墜毀、火車的相撞出軌、農藥廠的毒物泄漏、大地震的悲劇等屢屢報道,都提及這些災難事故所帶來的嚴重傷害。
“猝死”(sudden death)是徘徊在世界各地的幽靈。許多疾病或條件都可以發生猝死,但以心臟疾病、尤其是冠心病為主要原因。在一些國家的統計中,2/3的猝死為冠心病。
猝死和其它意外災害帶來的嚴重問題,困擾著眾多醫務人員的心神。
編織急救的“天羅地網”
在緊張而突愕的發病現場,人們希望醫生能盡快到達但是,城市中如果只有一個專業急救機構,那末,遠離醫療急救機構的病家等待的時間就長了。在這時間就是生命的情況下,等待越長,意味著病人的生命越危險。
因此,必須縮短急救半徑!我曾在法國南部圖魯茲大學醫學院與該院著名的急救專家拉亨教授熱烈地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的想法竟是如此地一致。他向我介紹,圖魯茲有30多萬人,現有4個急救機構,呼救電話發出后只要4~7分鐘,救護車即可到達病人身邊。
聯邦德國在急救方面有嚴密的組織,能高效率地工作,在當代急救界享有盛譽。慕尼黑的急救中心,確切地講是通訊指揮救護中心,可及時地將收到的呼救信息,指令就近急救人員趕到現場。由于對救護車裝備標準有嚴格的要求,車內有心電監護、除顫器、呼吸器、吸引器,氧氣瓶以及其它搶救裝備和急救藥品,酷似一個濃縮的流動急診室。所以,救護車到達現場,就意味著病人已經“住院”,可立即獲得急需的救治。
在現代化急救事業中,空中救護“異軍突起”。由于在空中“走近路”,所以大犬節省了時間。現在不僅用直升飛機救護,還有輕型噴氣救護機,可以遠涉重洋搶救和轉運危重病人。
急救的“天羅地網”的逐步織成,使得人類的“安全感”日益提高了。
加強民眾的社會急救意識
急救網再怎樣的嚴密,畢竟也有局限。如果在危重患者身邊的人,在醫生到來前能立即給予有效的初步救護,那就可以為下一步的救治奠定良好基礎;一些呼吸及心跳驟停的病人,甚至有可能因而“復生”。
眾所周知,身體里并沒有“氧氣倉庫”;循環一停,氧的供應隨即中斷。心臟的氧只夠它收縮幾次,腦的氧僅夠用10秒鐘。常溫下,人缺氧4分鐘以上,腦細胞就會受到損傷;超過10分鐘,腦損傷幾乎難以恢復,即使被救活,也常會成為“植物人”。所以,當代急救醫學界泰斗、現代心肺復蘇奠基人彼得-沙法教授,將《心肺復蘇》專著的新版改為《心肺腦復蘇》,這一字之增,使復蘇內容和深度大大向前推進了。
急救當然主要靠醫生。但民眾急救知識的普遍提高,則是使急救成功率不斷提高的基礎和保證。因為對一個現場未作初步救護、不進行基礎心肺復蘇的病人,即使由高明的醫生帶著先進的裝備趕到,往往也已無能為力。
民眾急救知識的提高,有賴于社會對急救事業的關注。要把“救死扶傷”的美德不斷地發揚光大,“見死不救”應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民眾的急救技能雖然有限,至少可以及時打電話或叫人呼救。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社會應共享急救資源。不少單位有救護車和急救力量,可以參加城市地區的日常急救值班,應在發生重大災害事故時被統一調動,以在急救工作中發揮作用。
讓我們更加密切地合作
現代文明,使人們的社會交往日益頻繁,地球似乎在迅速“縮小”,這要求各國在急救事業上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我國急救事業起步不晚,現已進入“三十而立”的年華。但受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影響,進展較緩慢。
在現代化的北京、重慶急救中心的建設過程中,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大力支持,該國提供了包括救護車在內的眾多的急救醫療裝備。我作為急救中心的負責人,在與意大利專家的合作過程中,深感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在急救中心建成后,如何真正把力量放在“醫院外的現場”和在現場發揮急救效益,意大利專家們也和我們進行了真誠友好的合作。
世界銀行援華的衛生項目中,對發展我國中等城市、地區的基層急救事業,也有相當作用,我們合作得也很好。這種合作是基于當代世界急救醫學發展前景,又十分重視我國國情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曾一起到浙江金華、江西九江、陜西寶雞等地進行考察,進一步認識到形成和發揮急救網的意義。假若把急救中心完全建成醫院的模式,勢必難以發揮急救效益。在最近召開的第6屆國際急救、災難醫學會議期間,各國專家普遍認為應共同編織好急救網。
情況確是如此。去年3月,日本圣心女子大學一個旅游團在我國四川劍閣縣發生車禍。我受亞洲緊急救援總部(AEA)委托,帶了北京急救中心一個搶救組,與該總部何雪兒女士帶領的法國、美國、香港的醫務人員同往西安,后又經上海到東京。此間,各地急救機構協作配合,使患有心臟病、脊柱骨折等嚴重傷員,在長途“接力”跨國界的轉運中,安全到達了日本,無一例發生意外和截癱。
我想,隨著我國急救網的日益完善,使我國人民和各國來華朋友的“安全感”日益增強,那該多么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