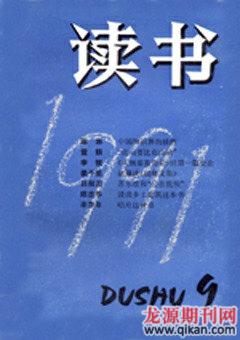站著的皇帝:劉瑾
王念華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這是封建社會孔圣人的話,表明皇帝的獨尊。可是到十六世紀初,在明王朝朱氏的一統天下里,居然同時出現了兩個皇帝,原來是太監劉瑾竊取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權力,他口銜天憲,發號施令,臣民誰敢不遵!當時四川巡撫林俊在劉瑾煊赫時,大膽地寫下一個奏章,他說:
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謂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系皇帝之權。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劉皇帝也。(《見素集》卷四頁1—8)
由此可知,當時京師內外的臣民,已公認劉瑾為站著的皇帝。
出現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并不足怪,也是可以理解的。遠因是在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明太祖朱元璋繼廢除了設在地方的行中書省后,接著又廢除了中央的中書省,罷設丞相,將之紀錄在《皇明祖訓》里,告誡他的子孫要永遠遵守。他的目的是將全國的軍政大權,總攬在皇帝自己手里,以便消除權臣竊國的危險,永葆朱氏家族的天下,萬世罔替。
朱元璋萬沒料到他的子孫,生長宮苑,并不理會他創業艱難和他的苦心焦慮的心機,大都是一些好逸惡勞、享樂唯恐不盡的角色,有幾個心愿去躬攬庶政,關心民間的疾苦呢?
就是在明初盛世,明成祖朱棣就沒有牢記他父親的教導:對“內官(太監們)只可供灑掃,不可使之有功”。對豎立在宮外的鐵牌,上鐫著“內官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禁令也置于腦后。他認為政務叢脞,日理萬機,實在難以勝任,于是在宮中的文淵閣里,設立了一個秘書處,任命幾個翰林院官員,當成筆桿子,草擬誥
宣宗朱瞻基在宣德(一四二六——一四三五)初,在宮中設立了一個“內書堂”,命翰林官員專教小內使書,許多太監因此“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使太監如虎添翼,有批紅、參政的能力了。當時太監金英就曾被親信用事。以后各朝,太監擅權,時有發生。如英宗時的王振,景帝時的曹吉祥,到了孝宗朱
弘治十八年(一五○五年)五月,朱
朱厚照嗣位的次年,改元正德(一五○六至五二一年),正德元年正月,劉瑾被任命為內官監太監,管理京軍“三千營”,漸用事,干預朝政,與其黨七人: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智、谷大用、張永結成一伙,時人稱之為“八虎”。
這位站著的皇帝劉瑾,原姓談,祖籍陜西省興平縣馬嵬鎮,父名榮,母劉氏。幼自宮,在景泰初,投奔劉太監為養子,因冒其姓,得以夤緣入宮。成化中,因領教坊(宮中樂舞)得幸。弘治初,坐法當死,免罪后,擯為茂陵(憲宗陵)司香,很不得意。其后,朱
正德元年二月,顧命三大臣劉健等以皇帝受到“八虎”的誘惑,不理政事,不御經筵,上奏言:“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引領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建白者以為多言,干職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曰再擾,查革弊政,則曰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事涉于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乞特允退”。帝不許。
是年六月,大學士劉健等又奏言:“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增廣,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對于單騎馳騁,輕出宮禁,泛舟海子,鷹犬彈射不離左右,接受內侍進獻等事,希望能留神警省。懇求將劉瑾等八人,盡行摒斥,以絕禍端。可是疏上之后,皇帝未加理睬,卻用內宮監太監劉瑾提督十二團營。
九月,劉健等以南京織造太監崔杲奏乞長蘆剩余鹽萬二千引,上奏說,開中鹽引,本為供邊塞軍用之費,不可濫發。小皇帝藉此聲色俱厲的說:“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朝官中十人里也只有三四個好人,壞事者十常六七。”劉健等據理執奏,皇帝仍許給崔杲所乞鹽引之半。很顯然,皇帝是與內臣站在一邊的。
十月,戶部尚書韓文以皇帝妄費,太倉國庫已空虛,深表憂慮。于是與屬下戶部郎中李夢陽計議,擬聯合科道、六部九卿同時上奏,奏章由李夢陽執筆,韓文叮嚀他奏章“不可文,文恐上不省;不可多,多恐覽勿竟也”。他們征得司禮監太監的同意,由太監范寧、徐智等將奏章直達皇帝。不料受太監支助出任吏部尚書的焦芳,將此情密告劉瑾,使之早籌對策。韓文等的奏里說:
近朝政日非,秋來御朝漸晚,仰觀圣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劉瑾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
朱厚照見奏,“驚泣不食”。劉瑾等八人于是夤夜齊集于帝前,以頭搶地,泣訴委屈,聲言求救,否則將被磔
第二天,圣旨下,劉健等才知事已無可為,如是各上奏辭職,帝允劉健、謝遷致仕,留李東陽仍舊任閣事。這次交鋒的結果,劉瑾等勝利了。焦芳由吏部尚書進入文淵閣,不僅跨入了密忽之地,而且破例地保有吏部尚書的官職,仍舊有對官吏進退之權。內閣至此,幾同虛設,大小政事惟太監劉瑾馬首是瞻了。
從此,劉瑾等排除異己,懲治反對者,首先將王岳,范寧追殺于臨清途中,徐智遭
故事,明廷杖朝臣,到成化時仍容許朝臣厚綿底衣,以重氈疊裹,以免傷動筋骨,撻臣下于朝與眾,原意是示辱而已。劉瑾始主去衣廷杖,故此后經常出現朝臣被撻死之慘狀。劉瑾用這種酷刑以立威。劉瑾還創造立枷,于錦衣衛常用之,枷重一百五十斤,被枷者不數日輒死。依附劉瑾的升官,奏劾他的罷黜鎮壓,因之敢言直諫者日少,奉迎依附者轉多。劉瑾權勢傾中外,公侯勛戚,不敢鉤禮,諸司科道以下,私竭皆相率跪拜。
劉瑾哄騙小皇帝的詭計,每構雜藝于上前,待其玩弄興致高昂時,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省決。帝每曰:吾用爾何為,而乃一一以煩聯耶,宜亟去。自是數次,后瑾不復奏,事無大小惟意裁定,凡百詔旨,上多未嘗知之。劉瑾識字不多,批答章奏,輒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和窩藏在家的松江市儈張文冕等相參決,文字由焦芳代為潤色。當時內外所進章奏,先具紅揭呈劉瑾,號稱“紅本”,然后交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敢稱名。這樣,劉瑾成了實際站著的皇帝。
正德三年八月,劉瑾傳旨:改惜薪司新廠為外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京師統謂之“內行廠”,由劉瑾自己提督,比東、西廠危害臣民更為酷烈。劉瑾下令寡婦盡嫁,停喪沒埋葬的盡焚棄,京師為之哄然!
劉瑾專橫,也引起了內部權力之爭,“八虎”之一的張永,已感到劉瑾對自己有不滿,有遭懲辦的危險,希望情況稍有改變,對使天下臣民皆重足屏息,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的局面,籍江西南康縣民吳登顯三家,因端午節賽龍舟而遭破家之禍,覺得難以維持長久,也思稍稍有所易轍,以免遭到覆巢之禍。
正德五年四月初五,安化王朱
近年以來,主幼國危。好宦用事,舞弄國法,殘害忠良,蔽塞言路,致喪天下之心,幾忘神器之重。予獎率三軍,以誅黨惡,以順人心。(《正德實錄》卷六十二頁1—2)
四月二十三日,
八月十一日,太監張永還自寧夏,擬十五日獻俘,劉瑾欲推遲其期,永慮有變,遂先期入宮,獻俘畢,帝置酒勞永,劉瑾等也在座。及夜,瑾先退,永于是出
劉瑾是惡貫滿盈,喪身的直接原因是納賄深藏,患了“多藏厚亡”之忌,使皇帝見到他所積“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也眼紅起來。不過,他擅權不過五年,何來如此鉅款。正德三年四月,他開鬻武爵贖罪、諸生捐監、廣度僧道,以充邊費,傳者指出,“銀未出京,入瑾之門幾四分之一矣。”正德五年劉瑾被磔后,承運庫太監李時曾指出“自劉瑾括天下之財以歸京師,半入私室,半歸公帑”據歷史記載:萬歷時全國田賦收入每年征銀為一千四百六十萬兩,而劉瑾所藏銀一項多達兩億五千萬兩,是當時朝廷收入十七年以上的總數。這筆錢,并未入太倉國庫,而是全都輦致豹房,供朱厚照做了逸樂揮霍享用之
劉瑾被磔,其親屬十五人并侄孫劉二漢及其黨張文冕等皆論斬。張瘐死獄中,還戮其尸于市。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以及戶部尚書劉璣、兵部侍郎陳震等六十余人,皆降謫。
一部中國封建王朝史,可見宦官幾乎與專制制度相始終。宦禍為烈之時,內豎對天子竟握有生殺予奪之權。“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李商隱《重有感》)但不該發生的事,卻總是屢屢發生。不必說劉瑾以前,即劉瑾之后,終武宗一朝,乃至有明一代,猶宦禍不已。即使對此有痛切之識的崇禎帝,也未能免。這其中的“內因”與“外因”,不值得人們思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