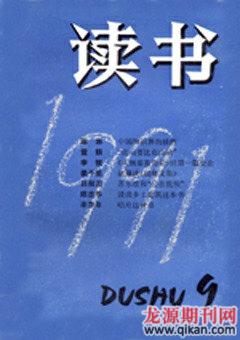蔣竹蓀
《世界文學》一九九○年第二期轉載梁實秋《讀馬譯<世說新語>》一文。梁先生學貫中西,又是翻譯行家,深知譯事甘苦。他說:“(世說)淺鮮易曉者固然不少,但文字簡奧處,牽涉到史實典故處,便相當難懂。”現就使他“困擾了很久”的一句話,作一點粗淺的分析。
梁說:“《言語》第二十六條、‘千里(莼)羹,未下鹽鼓,宋本‘未下為‘末下之誤,已成定論。”宋本是古書較早的版本,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宋本有紹興八年董本,淳熙十五年陸游本,淳熙十六年湘中本之不同,而涵芬樓影印宋刻本并未將“未下”誤為“末下”,《晉書·陸機傳》亦作,“千里羹,未下鹽豉”,可見僅憑某一宋本,尚難征信。
接著梁先生舉唐人例以證成其說:“唐趙《因話錄》早就說過:‘千里莼羹,未聞鹽與鼓相調和,非也。‘末字誤出為‘未;末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按江蘇溧陽有千里湖,“末下”則不見載籍。為弄清語言環境,不妨抄錄《言語》第二十六條全文:“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羹,但未下鹽豉耳。”大意說武子問陸機,你們家鄉有什么美味可以跟羊酪相比?陸機答,有未下鹽鼓的千里羹。其中隱含如下鹽豉將比羊酪更美之意,這是所謂文字簡奧處。
羹能否與鹽鼓調和,是使粱先生“困擾了很久”的問題。他肯定趙二地二物不能調和之說,批評“后人偏偏不改正這一錯誤。又對相反的意見表示疑惑不解:宋黃徹《溪詩話》卷九:‘千里羹,未下鹽鼓,蓋言未受和耳。子美‘鼓化絲熟,圣俞‘剩持鹽豉煮紫,魯直‘鹽鼓欲催菜熟。然則昔賢如杜子美、梅圣俞、黃魯直均是以耳代目,以訛傳訛耶?這真是難以索解的事。”羹自古是美味,迄今蘇杭酒樓尚列為名菜。蘇恭《唐本草》云:“又宜老人,應入上品,故張翰臨秋風思關中之鱸羹也。”在中國最早的農學及食品學名著《齊民要術》卷八曾反復講了羹的燒制法,并引《食經》說:“羹,魚切成二寸長,但菜不切。”“白魚:冷水入,沸入魚與鹽鼓(如是白魚先把菜下在冷水里,等湯開了,再放魚和鹽酸);醴魚:煮三沸,渾下與鼓汁、潰鹽(如是醴魚,把魚煮三開后,將菜放入,再加豉汁和鹽)。”至于梁先生“莼菜若投入鹽鼓,則混濁不可以想象”的顧慮,《齊民要術》還特別強調煮鼓汁的要求:“鼓汁,于別鍋中煮一沸,漉出滓,澄而用之,勿以杓,則羹濁,過不清。煮鼓但作琥珀色而已,勿令過黑,黑則咸苦。”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成書年代上距《世說新語》不到一百年,它的解說自然比較接近于晉代史實。
由“未”與“末”一字之差,影響到一個雙音詞的釋義,進而導致對整個句子的不同理解,這是使梁先生“困擾了很久”的原因所在。倘寫作從“揚長避短”的角度出發,上述這段“志疑”,完全可以省略,并不影響書評《讀馬譯》的完整性,然而梁先生仍舊寫出,做到不嬌飾,不避短,想到啥就寫啥,此種率真態度,求之今日,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