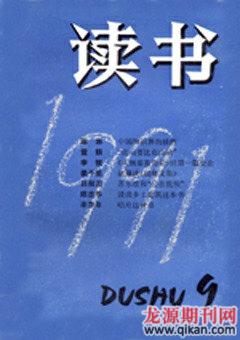社會史的視角
盧暉臨
社會科學對科學方法的要求不是提供完美,而是認識的深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門學科都可以看作一種視角。通過不同的視角,人們看到的不盡相同,但綜合各種視角,人們就會得出比較全面和準確的認識。
海外學人何炳棣所著《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為我們提供的正是這種有益的視角。
何炳棣選取社會流動這一主題作為研究對象,可能是基于這樣的考慮:第一,明清時期有關社會流動方面的資料是最為豐富和完整的;第二,研究社會流動是揭示社會結構的一個非常有效的途徑,它提供了對于中國社會本質的深刻理解。但何炳棣并沒有奢望去研究明清時期社會流動的全部方面,而是將注意力放在了社會學術流動(socio-academic mobility)或者說是精英流動(elite mobility)方面。這一方面是因為明清時期有關社會流動的資料主要只涉及功名階層,而關于職業流動及社會流動其他方面的資料不僅少見且多為印象性的描述,無法量化;另一方面也與何炳棣暗含的一個假設有關:在明清時代,社會學術流動是社會流動的一條主線,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學術流動的趨勢與總體的社會流動趨勢是一致的(這一假設在書末明確提出并得到了證實)。這樣,何炳棣通過對社會學術流動(即進入官場的流動)的研究為我們概括出了明清時期社會流動的主要特征,不僅如此,通過對影響社會學術流動的各種制度(如考試制度、戶籍制度、學校制度等)的研究,何炳棣事實上討論了明清社會的幾乎所有的重要特征,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何炳棣才使用了《明清社會史論》這一書名。讀完此書,我們確實得到了一幅明清社會的清晰圖畫。
為了對進入官場的官僚階層的社會構成進行研究,何炳棣使用了大約包括七十多種進士和舉人,貢生的登錄名單,其中進士名錄四十八個(登錄了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名進士的情況),舉人和貢生名錄二十八個(登錄了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名舉人和貢生的情況),它們基本上可以代表整個明清時期的情況。通過對登錄中的進士的統計分析,何炳棣發現明代有百分之四十七點五的進士出身(指祖上三代,下同)于沒有任何功名的家庭,加上出身于初級功名家庭的進士,比重上升到百分之五十,清代出身于無功名家庭的進士比例雖有所下降,但初級功名家庭出身的進士比例則有所上升,兩者相加占進士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二。對舉人和貢住的統計分析表明對于那些非官員家庭出身(指三代無功名或只有初級功名)的人來說,考中舉人和貢生要比考中進士容易許多,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舉人和貢生中有百分之四十五點一出身于非官員家庭。
為了研究官僚階層內部的流動情況,何炳棣又對官僚家庭出身的進士進行了分類,結果他發現有三分之二的進士出身于老百姓家庭和低級官僚家庭(七品以下),三分之一的進士出身于中高級官僚家庭,對于出身于中高級官僚家庭的這些進士來說,他們的地位變化不大甚至反而下降了(與祖上三代相比)。因此,作者得出結論:中高層官僚家庭存在著一種固有的下降過程,它說明那些位置顯赫的家庭在長期的競爭中,要維持他們優越的地位很困難。
在龐大的功名金字塔中,生員處于最基層。由于“生員”地位的獲得標志著向上流動過程的正式開端,所以它是社會流動過程的關鍵的起步。但有關生員主體社會構成狀況的資料非常缺乏,在浩瀚的史籍中,何炳棣找到了三個記載了生員家世情況的登錄,它們分別包括了長江下游常熟縣,海門縣和南通縣三個縣的生員共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名。統計分析表明南通縣在明朝有百分之七十四點八的生員出身于三代無任何功名的家庭,在清朝雖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三;常熟縣和海門縣在清朝分別有百分之五十四點五,百分之四十八點四五的生員來自無功名家庭。這說明一直到清朝末年,生員的來源仍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考慮到這三個縣都是文明程度較高的地區,出過許多一甲進士和一些對國家有突出貢獻的顯赫家族,而普通百姓仍有一個公平的機會,贏得社會流動的這一關鍵起步,那么可以推測全國的情況與何炳棣的一個陳述非常接近:明朝有幾乎四分之三的生員,清朝有一半以上的生員都出身于沒有任何功名,地位低下的家庭。它表明明清時期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存在著一個廣泛的升遷的社會結構。換句話說,明清的統治階級是建立在一個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上的。
何炳棣的這些研究所導致的結論,與我們的“常識”或以往得到的知識往往相悖。我們總以為讀書應科舉者必出于有產之家,屬于一個不代表平民利益的階級,但我們無法懷疑統計數字的真實性(小的誤差并不影響結論),關鍵在于如何解釋這種情況,能否令人信服地說明:普通百姓的子弟怎么可能從體力勞動的重負下解脫出來,而有余暇和財力進行科舉的準備?
從何炳棣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大致總結出以下一些有利于普通百姓向上流動的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因素。
一公共學校。盡管科舉制度為下層人士提供了一個向上升遷的渠道,但由于國家在一開始只是把它當作官員選拔的一個途徑,而不是為那些希望進入官場上的人提供教育的便利,所以在長達三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普通百姓由于缺少受教育的機會,處于很不利的競爭環境中。宋朝統治者開始注意公共教育的問題,但由于種種原因,一直到宋末,公共學校并沒有廣泛地建立起來。明建立以后,太祖對于學校教育與科舉的邏輯聯系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他頒布了一系列要求各省、州、縣興辦學校的法令,到他離世時(一三九八),全國已經有大約一千二百所學校建立起來了。這以后,公共學校不斷地發展,到一八八六年時,全國共建立了一千八百一十所學校,即使連一些貧困偏僻的邊遠少數民族地區也出現了學校。公共學校的廣泛建立縮小了貧寒人家與富貴家庭在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公共學校都由國家出資,且有一定的津貼),但是由于公共學校只接受已經取得生員功名的人,所以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從童生到生員這一過程中,必須有面向普通民眾的教育機構,不然,貧寒人家仍然難以支付學習的費用。明清社會是怎樣解決這一問題的呢?
二.社學和書院。一三七五年,明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要求全國的鄉村、城市建立社學。在許多地方,社學的建立是與當地政府和官員的努力分不開的,但并不接受國家財政的支持,而是所謂的“自籌資金”。何炳棣參照明末和清朝的地方志說明至少在明朝的前半期,社學已經廣泛地建立起來。通過對大量地方志和政府法令的考察,何炳棣進一步指出,盡管儒家教育機會平等的理想從來沒有得到過完全的實現,但至少在明初的一百五十年中,受教育的機會要比當時歐洲的大部分國家更容易得到。
當社學于明末開始衰落的時候,書院卻以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書院多由地方名流和有聲望的官員捐助,因此,對于一般的學員也是免費的。在明朝,書院主要關心的是哲學問題,只是附帶地為科舉作些準備,到了清朝,為應試作準備則成了書院的最主要目的。
此外,各種形式的義學也為貧寒人家的向上流動提供了一條渠道。義學是由家族建立的學校,為的是教育宗族子弟,但有些義學也接受鄰近地區的非本族窮人。這種情況到了清朝就更加普遍。
三.對應試者的各種各樣的社區幫助。除了正式的教育途徑以外,社區還為應試者提供了各種幫助。最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團體公款制度(the cystem of Cocal Community Chests),團體公款多為當地富戶和官員捐贈,有的是現金,有的是土地,有的甚至是稻米,它們有專門的人員或機構管理。這些團體公款在有的地方叫“貢士莊”,有的地方叫“青云莊”,“進士莊”。根據何炳棣的研究,到十三世紀上半期,團體公款在長江省份諸如湖北、湖南、浙江、江蘇、江西等已經很普遍,它們為生員、舉人獲得更高的功名或者是維持生計提供了一定的幫助,而且有證據表明團體公款是根據應試者的實際需要提供援助的,譬如有許多地方的縣志說明生員從團體公款中得到的津貼要比舉人多。
會館也是地方為應會試的考生提供的幫助,至少從十六世紀開始,全國所有的省,許多州以及一部分大縣在北京都建立了會館。
盡管團體公款制度和會館不是一個地區促進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但它們在明清時期的廣泛存在確實反映了地方社區在追求學術成功和社會的聲望方面是不遺余力的,它連同國家的教育制度(學校)、科舉制度等一起保證了貧寒之士在與富貴家庭競爭向上流動機會時的一定程度的均等。
長期以來,歷史學特別注重對制度史的研究,注重對法律規定的制度結構的研究,盡管這很重要,但容易導致的一個結果是與社會實際情況的脫離。何炳棣的研究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對社會實際情況的關注。何炳棣也研究國家的制度,但他是從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制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這一角度出發的。結果他發現許多制度只是停留在法律條文的層次上,譬如,明朝前期,政府有一套維持特定身份世襲制的嚴厲法規,但明朝的身份仍具有很大的流動性。與法律條文或制度相比,有時候社會小說和當時人的筆記反倒更能反映社會的實際情況。正因為此,像《茶余客話》、《儒林外史》、《定
從小處入手,進行宏觀的考察,是社會史研究的另一特色,它帶來的好處是很明顯的:首先是研究的可行性,從小處入手,無論從研究者的能力還是從資料方面來說,都是最為可取的現實選擇。其次,選取某一個方面進行宏觀的全面的考察,是使研究的意義超出“小處”本身的重要方法。就《明清社會史論》來說,何柄棣著力研究的是精英流動,但他采取了全面的、整體的研究方法,對于影響精英流動的各種因素如考試制度、社會思想、學校制度、戶籍制度等都作了詳盡的分析,因而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已經遠遠地超出了“精英流動”這一概念本身蘊含的意義了,它們對于回答中國傳統社會歷史研究中的某些基本問題是大有裨益的。例如:明清的統治階級是否建立在一個廣泛合理的社會基礎上?中國傳統社會的控制力量是什么?等等。何柄棣的研究甚至對于我們認清中西方社會的差別也有很大的幫助,當然他是從社會流動這一角度看的,但有助于我們認識傳統和現代社會的某些特質,從而理解傳統社會的蛻變。例如,何柄棣認為在西方工業社會里,持續的技術變革和經濟動力共同帶來了收入和職業方面的穩定的向上流動的模式;而在明清社會,由于人口的增殖和技術以及制度的停滯,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長期的向下流動的模式。這種認識巳經具有了很高的理論價值。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