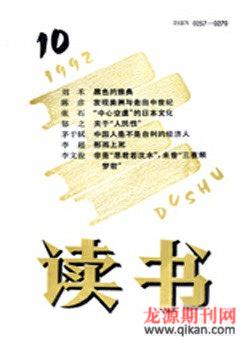漂泊的心
1992-07-15 05:29:58鄭澤華
讀書 1992年10期
鄭澤華
讀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傳記,深為這位身材矮小、表情呆滯、生活刻板、終身未娶的日耳曼人所驚詫,驚詫他在教書、著書、散步的單調循環中提出了星云假說,創立了批判哲學;驚詫他畢生未離開閉塞、沉悶的故鄉小鎮而他的哲學思想卻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思想進程。自他后,許多杰出的文化巨人如歌德、托爾斯泰、愛因斯坦等都榮幸地宣稱受到過康德思想的熏陶。康德曾說過:后來的哲學家都繞不開我康德這座橋。
象康德這樣外表與內心形成強烈反差的例子在思想文化上不勝枚舉,如現代派小說鼻祖卡夫卡終身都是一名保險公司小職員,當代世界級短篇小說大師博爾赫斯做了一輩子圖書管理員。
由康德們我想到了三毛,一位也是因為心靈的漂泊無助而自殘的女人。在三毛作詞的歌曲《橄欖樹》中,我聽懂了她為了愛和不僅僅為了愛而流浪的心聲。無論是浪跡天涯的三毛,還是足不出戶的康德,盡管他們貢獻給人類的的精神財富不可同日而語,但心靈的漂泊使他們壽命的短暫與漫長(康德享年八十,三毛減半)失去了比較的意義,他們的心路旅程在他們肉體寂滅后得以綿延。
古往今來,多少哲人智者,為了抵御惡政時弊,保持心靈的自由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呆滯的外表、鄙俗的舉止、乖
歷史與文化就象一條川流不息的河,放眼回溯,風流人物與庸常之輩泥沙俱下、灰飛煙滅,唯有漂泊的魂靈生生不息。
猜你喜歡
中國德育(2022年12期)2022-08-22 06:16:18
中學生數理化·七年級數學人教版(2022年5期)2022-06-05 07:51:50
華人時刊(2022年7期)2022-06-05 07:33:26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金橋(2022年1期)2022-02-12 01:37:04
當代陜西(2021年13期)2021-08-06 09:24:34
人大建設(2019年4期)2019-07-13 05:43:08
當代陜西(2019年12期)2019-07-12 09:11:50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