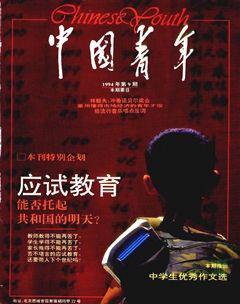教師:飽受煎熬又為啥?
邱四維
看見學生赴湯滔火,
看見家長視死如歸,
再看看領導殷殷的期待,
我不把自己全部投入應考,行嗎?
一黨總支書記說:“上面要求升學率,我們怎么辦?”
北京市安貞里中學是一所建校5年的初級中學,學校的黨總書記蔣瑞琴對我說:
我感覺,應試制度和我們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相悖的。咱們教書是為了育人,講究因材施教,根據學生的特點培養各種各樣的人。每個人能力、水平、特長不同,千軍萬馬都用一個標準,這不符合客觀發展規律吧。上面要求升學率,我們可不千方百計一個勁兒地灌。學校從早上7:30到晚上5:30全都在教書教書,上課上課,背書背書,老師特別反感。可還得這樣干,因為衡量學校的標準,是及格率多少,達標率多少,優秀率多少,一點不看你這個學校究竟培養出了什么樣的人才,那我們也只有用各種方法,去追這些個“率”。
咱們是9年義務教育,上完9年,成績基本能達到及格線就行了。如果要考重點高中,或者職業中專,那你就到報考的學校去考。比如說考外語學校,數學就沒必要非得多少分以上,這對學生來說,教育就有針對性,也便于人才的培養。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講要搞素質教育,可實際上我們做的還是應試教育那一套,當教師的真是不好干。分好了一好百好,分不好就是百好也沒一好。老師當然不會只以學習成績來評價學生,可關鍵時候只有分數管用。我們有一學生,愛集體,愛勞動,尊敬師長,團結同學,有很多長處,可就因為差1分他就不是合格的畢業生,他就升不了學。
每年考完試,成績座次就排下來了。市里排區里的,區里排學校的,學校就得往教師身上壓,要求老師上百分率,老師只好跟學生較勁,可實在上不了的學生又怎么辦?
一地理教師說:我這教
書的也快找不著北了。
現在學生厭學,有很多原因,但我覺得最根本的在于這考試制度。我們總是講經濟要上去,必須提高文化素質,可是我們在培養人才時,只講統一性,忽視了學生的個性發展。而這統一性只是分數上的統一。現在考試大綱是舊的,教材又是新的,教書的特別為難,你不順從上面的不行呀。地理課要上得生動活潑使學生產生興趣并不是件困難的事兒。可我們敢這樣做嗎?地理是副科,現在只有初中和高一學,高考文科理科都不考,但地理課的教學并不能因此就可以隨隨便便呀。對老師來說希望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可老師付出了許多,學生就是不愛學。學生不喜歡滿堂灌,我們老師就喜歡?我們要講那么多課,壓縮著講還不能漏掉可能要考的東西。但考試考到現在,擺在面上的重點都考完了,那就開始考犄角旮旯,你不是知道世界上最高峰和最低洼地嗎?那我考你第二高峰和第二洼地,你還得準確地說出它的高度。這么考,學生能不專揀那些生僻的地方看?這種完全靠死記硬背搜尋偏僻得來的好分數對學生究竟有什么好處?老師除了講重中之重,還要強調重外之重,到頭來自己都犯迷糊。每年我們都為這重點犯難。抱著這樣的心態去教課,我們教得出什么來?再生動的東西還不都成了死八股?我不相信卷子上東南西北考100分,生活里找不著北的學生地理課就算及格,過關了。你說我們這是真正在學習知識呢,還是為了考試而教學呢?
一畢業班優秀教師嘆:“受的煎熬真不知有多少!”
要說現在最跟上形勢,最擅長從細微處見閃光點的是教師。我們當教師的可以從一小句話里找出一大堆考題來。當了10年的重點中學教師,鍛煉得最結實的就是削尖腦袋在課本的字里行間鉆來鉆去。我最羨慕30年代那些名教授行云流水式的課堂教學。那不僅僅是在授業、解惑,而真正是在傳道,傳做人之道。教師不僅有知識,而且有文化,有人格魅力。10年前走出大學校園進入這所全國有名的重點中學時,我曾暗下決心:做一名真正的靈魂工程師。現在看來工程師是當得差不多,但那不是靈魂的,至多只是個外科大夫的水平。從當教師的第二年,校長就把畢業班的重擔放在了我的身上。那是多大的信任啊!當時在全校引起的震動還真是不小。要知道畢業班的水平就是學校的水平,畢業班的牌子砸了學校的牌子也就砸了。可也正是從那時起,我才真正明白自己所渴望的行云流水是沒有了,我所向往的教師形象恐怕也是達不到了。沒有辦法,畢竟你面對的是高考,是千軍萬馬殺向一隅的生死搏斗。對你的學生來說,你是他們的保護神,是教給他們廝殺本領的教官。我是從農村考出來的學生,我最懂得高考意味著什么,我當然會全力以赴幫助我的學生面對戰場。那一年里,可以說是嘔心瀝血,鉆研考題,摸索出題者思路,補充大量教材里沒有的可能會考的材料。從我應考的經驗到學校里老教師的經驗甚至我上大一時同學回憶高考時所講的經驗我全都整理并經驗一回,然后條條款款地教給我的學生們。成績自然是不錯的,當然也是學生爭氣,我教的這科當年高考名列全市第三。榮譽來了,獎金來了,可那沒完沒了的應戰,永遠跟隨的高考再也擺脫不掉了。每年學生考完,就是對我的考試,在高考成績下來前一段時間里,我,甚至我妻子都可以說是過得戰戰兢兢的,直到一個不錯的分數下來后,心里這才放下,暑假這才能過得踏實,一家人一年中才有了喘氣的可能。可也就二三十天,新學期又到了,又一輪考驗來到了。工作10年,參加高考五六次,受的煎熬真不知有多少,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是個盡頭。我是個要強的人,干什么都要做得最好,10年來的成績使我不敢有半點松懈。原來我還有些個人愛好,寫點詩、散文,集郵什么的,現在全放棄了,哪有時間和精力啊!看見學生赴湯蹈火,看見家長視死如歸,再看看領導殷殷的期待,我不把自己全部投入到考試,行嗎?
一教務主任說:“一味指
責考試是不公平的。”
要說“應試教育”有弊病,在我們這個社會里越來越不能全面地培養人才,現在看來的確存在這個問題。尤其《較量》那篇文章出來后,社會上關于高分低能,學生成了考試機器的輿論也越來越多,而且幾乎所有的矛頭都指向考試。平心而論,高考指揮棒的確讓現在的學生學得越來越苦,做老師教得也越來越難,但一味地指責考試是不公平的。選拔人才總要有個標準,國家公務員還要考試,更何況是尚在成長的學生!沒有考試,用什么來檢驗學生掌握知識的程度?如何評價教師的教學水平?如何體現學校的教學質量?說句難聽的話,現在整個社會都失去了標準,如果連考試這唯一還算公平的競爭都要一再被指責的話,我們還要不要標準?
這么多年來我們的考試制度不也培養出一大批人才嗎?每年的奧林匹克競賽,我們不都拿了金牌嗎?
考試對學生來說是檢驗學習效果的有效手段,尤其高考是個大檢閱,對老師對學校同樣是大檢閱。高考成績一下來,學校座次一排定,學校的經濟水平就可以看出來了。升學率高的學校,家長就愿意把孩子送來,交錢多些也沒關系;你升學率不怎么樣,誰愿意白給你錢?學校建設,教師福利,哪樣不需要錢?可國家每年撥的教育經費就那么多,雖說有校辦企業,但現在國營企業都過得艱難,就不用說區區校辦工廠了。升學率高的學校,學生家長有能耐的也多,只要孩子能念書,給校辦工廠謀點便利還不是教師幾句話的事?校辦企業辦得火的肯定是升學率高的。再比如,教師節我們總得給老師發點雞蛋、大米、香油什么的,升學率高的學校很多人搶著送,你升學率不高,誰給你送錢送糧?
一位老校長說:“教育
要面向全體學生。”
位于城市邊緣的清華附中在中學校里卻有著極為中心的地位。走進校園,赫然而陳的是最近一次市高一數學競賽學校獲獎情況:一等獎8人,二等獎4人,三等獎4人。即將離任的老校長楊津光侃侃而談:
要說學校追求升學率,以考試分數論成敗,這是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在短時間內難以扭轉。為什么每年報清華附中的學生那么多?因為我們的升學率是98.7%,去年光考上清華大學的就77個,這些數據在中招會上一公布,大家就看出你這個學校的教學水平如何。要是我們考上清華大學的才20幾個,升學率不是98.7%而是80%,誰愿意考你的學校?兩年前因種種原因,我們的升學率降到90%,不僅我們的教師恨不得有個地縫鉆下去,就是周圍的人都說這下清華附中可砸了。社會輿論就是這樣,只要有高考,就避免不了用升學率作為衡量學校好壞的標準。但誰要說我們是片面追求升學率,我不承認,我們教師也不承認。為什么?因為我們給同學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我們努力從素質上培養學生,學生素質、能力高了,考試也就不難。但關鍵在于怎樣提高學生的素質。我們認為,中學是基礎教育,是一個打坯子的過程,制造一個好的坯子比讓學生考上重點大學還重要。我們不能從一個人能否考上大學來評判他是不是人才。學校有個“馬約翰體育特長班”,我們給這個班的指標就是“合格加特長”,不要求學生門門功課都優秀,但學生體育是特長,那就該充分發揮作用,用體育的特長彌補學習方面的不足。事實上這樣也出了不少人才。有個學生畢業時功課是比別的同學差一點,但他代表中國中學生參加泛太平洋地區中學生運動會拿了金牌,為國爭了光,你能說他不是人才?在學生素質教育方面我們采取了多種措施。多年來我們堅持的一個教育方針就是“你給學生面包,不如給學生獵槍”,從多方面培養他的的學習興趣、學習能力就是給學生獵槍,有了獵槍,那高考這面包也不難取得了。當然,我們學校有許多有利的辦學條件,甚至有人說因為我們的生源好,但我認為,學校教育者管理者的教育指導思想是至關重要的。大環境、高考指揮棒現在沒法改變,但學校作為人才的具體培養者,在對學生進行教育時就應該注意到因材施教。教育要面向全體學生,讓多數人發揮出潛能,激發多數人的創造性來,而不只是面向少數尖子生。因為撐起我們這個社會的,更多的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