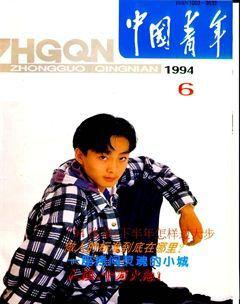文學何時能擺脫困窘?
潘凱雄
曾幾何時,文學何等的輝煌!曾幾何時,文學又如此的困窘!從輝煌跌入困窘,不過彈指一揮間。關于這種變化,世人早已有目共睹:
——全國各種純文學期刊發行量近年來一直趨于跌勢,由過去動輒發行幾十萬份乃至上百萬份跌至萬份乃至數千份(幾萬份或十萬份的文學期刊眼下已是鳳毛鱗角)。這樣的發行量必然與兩個字緊緊聯在一起——賠錢。
——一方面是辦刊賠錢,另一方面卻是辦刊經費的嚴重短缺,有的早巳“斷奶”,有的雖未全斷,卻也是奶水不足。
——文學書籍的出版發行也不例外,這一兩年雖然也有幾本文學讀物被“炒”得紅紅火火,但畢竟不在多數,更多的文學書籍均由于訂數過少而無法開機印刷,文學理論學術著作的出版更是難乎其難。
——文學園地的不景氣不能不對文學隊伍的狀況產生影響,當然也可以說文學隊伍的分化影響了文學園地的繁榮,但無論這種因果關系孰先孰后,文學隊伍的分化則是一個客觀現實:有的“下海”,有的轉向影視,有的身兼多職,總之,那種純粹地鐘情于文學特別是純文學的人大約是越來越少。
當然,這一切或許只是發生在那些被我們稱為純文學的領地之中,至于那些面向市場的通俗文學及大眾文化的消費性讀物其生存則未必如此窘迫。不過,衡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學的基本水準最終還是要看其純文學的狀況如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困窘”二字來描述當下純文學的生存處境倒也并非聳人聽聞之辭。
面對文學的這種生存困窘,我們自然也看到了種種變化和不甘就此沉寂下去的努力,而這一切大致可規納為如下幾類:
一曰矢志不改型。一些文學期刊無論自身的生存如何窘迫,他們寧可在別的方面出主意想辦法,就是不改純文學的初衷。譬如《收獲》迄今就不在刊物上登廣告,也不設種種花哨欄目,而是以扎實的工作和高標準的選稿吸引了眾多的一流稿件,而類似這樣堅持純文學宗旨不變的刊物當然絕非《收獲》一家。期刊如此,作家中也不乏這樣的人在,他們只是孜孜于自己所熱衷的文學事業,根本不為什么“下海”“發財”之類的誘惑所動搖。矢志不改者在旁人看來或許有些愚頑,但這種不為時尚所左右、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推崇的,即使他們最終消亡,其悲壯精神依然長存,更何況迎接矢志不改者的未必就是消亡,誰又敢保證絕不會出現柳暗花明的那一天呢?
二曰以文養文型。一些期刊騰出相當篇幅用來刊登社會熱點類的紀實文學或為企業和企業家立傳的文字,期望以此改變刊物發行量過小的現狀;另外,為企業和企業家立傳也可從他們的口袋里討些銀兩聊補無米之炊;而一些作家也不時寫上一些“廣告文學”和影視一類經濟效益可觀得多的文字,不再死死抱住純文學不放。
三曰橫向聯姻型。一些期刊積極尋找那些經濟效益可觀的企業作為自己的合作者——或直接合作,如《廣州文藝》與深圳中達工貿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或間接合作,如不少刊物的“董事會”“后援會”等形式……
千種變化,萬般掙扎,是耶?非耶?本文無意就此作出評說,更何況最權威的評判官莫過于實踐的最終檢驗。不過,在冷靜觀察的同時,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再追問一下:目前出現的這種文學生存困窘究竟正不正常?
其實,文學今日的“困窘”更多的還是相對于它昔日的“輝煌”而言的,應該說我們今天常常引為自豪的文學昔日“輝煌”更多的屬于那個時代的產物。在一個瘋狂與荒唐的年代剛剛結束不久,人們積聚了多少思考與憤懣需要宣泄,加之當時新聞、言論等其他媒體透明度的不足,致使文學成了一條宣泄情緒與發散思考的主渠道。此外,在當時的特定背景下,文學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精神勞動,同時又成為許多人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途徑,作家夢的實現,不僅使人獲其名,而且使人得其利。這樣一來,投身文學事業的人之多,由一部文學作品所引發的一時洛陽紙貴的現象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了,而我們所說的文學昔日的“輝煌”也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那么,當時代條件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當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逐漸增多,當政治、新聞、言論的透明度日益加強的今天,一部分人從文學隊伍中分流出來,文學作品不再有昔日那種強烈的轟動效應,也未必不是一種正常變化。
在我看來,文學在今日之所以給人以“困窘”的印象,其主要標志不外乎有三,即文學生存環境的艱難、文人心態的失衡和文學社會轟動效應的失落。我并不認為后兩條變化的出現有什么不正常,倒是圍繞著文學生存處境的如此艱難這一條很有再思索的必要,我想說,目前的這種生存困窘除了條件的變化,是否有人為的因素、體制的因素在起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困窘呢?
一本文學期刊、一部文學著作動輒發行數十萬乃至上百萬未必正常,但僅僅只能發行幾千份同樣也是一種不正常,中國畢竟是一個有著近12億人口的巨大市場,雖然其中的文盲半文盲占有相當比例,但偌大一個市場對文學的需求絕不是幾千的數字就能飽和的,稍有一點經濟頭腦的人都不會不看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也有人將文學的困窘歸咎于當下社會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和市場經濟的建立以及社會上物化思潮、拜金主義等因素的綜合作用。此說不無道理,但似乎也不盡然。若論商品經濟的沖擊、市場經濟的程度、拜金主義的嚴重、物化思潮的泛濫,地處西半球的發達國家比我們真是有過之無不及,但這一切似乎并未影響他們文學事業正常運作,也不妨礙一本本被公認的文學經典從那里出現。
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和比較,我們又不能不認為目前出現的文學困窘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至少也不該嚴重到如此程度。如果要探究其成因,簡而言之,我以為不外乎是人們觀念上的、國家體制上的和文化經濟政策上的綜合原因。既然如此,欲尋求擺脫文學困窘的出路也就只有從這三方面綜合治理。
文學創作畢竟是一種極具個性的精神勞動,因此,這就首先要求每一個從事文學創作的個體以一種正常、健康的心態投入到創作中去。那么,什么樣的心態可以稱之為正常和健康的呢?如果套用一句流行歌詞的話,那便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具體點說,也即是要有一顆既開闊又寧靜的平常心,不為一時一地的時尚所左右,不為急功近利的欲望所誘惑。我并不主張作家就一定要貧窮,一定要寂寞,一定要職業化,因此,對文學家的“下海”、兼職以及向影視劇本創作發展等種種“向錢看”的行為,我也并不認為有多少不妥的地方,而是對此持足夠的寬容和理解的態度。與此同時,我又頑固地認為:作家一旦進入純文學的寫作,就不能不淡泊名利、遺世獨立,此時如果又想出經典、又想撈名利,則未必能魚與熊掌兼得。所以,從作家個體而言,擺脫困窘倒不在于他們目前干什么,而恰恰在于他們在從事純文學寫作時以一種什么樣的心態進入,時下所出現的問題也不在于“下海”的人多了,而是存在于許多作家身上的浮躁和虛泛。
如果說文學創作是一種極具個性的精神勞動,那么,整個文學事業則無疑是全社會文明建設的一部分。因此,要擺脫文學事業的生存困境,僅靠作家或是從事文學事業的人的單方面努力顯然是力不從心的,說到底,振興文學事業也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而當務之急就是要改變種種現行的、不合理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經濟政策。現行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經濟政策的不合理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說,國營書店競爭不過個體書商,主渠道的萎縮一方面造成了高雅文學出版發行的困難,一方面又為大量的平庸之作的出籠打開了大門;比如說,幾年甚至十幾年寫不出東西的人可以享受專業作家的待遇,而那些勢頭看漲的作家卻不能不受到所謂名額的限制;比如說,作協機關的高度衙門化和文學期刊的人浮于事;比如說高雅文學的稿酬偏低,等等等等,無不是由現行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經濟政策的不合理所造成。整個文化界的體制問題喊了多年,只是雷聲大雨點小,不見多少真招實招的出臺,不是聞風不動,就是簡單的一刀切。坦率地說,如此玩虛招、擺花架子的改革還不如不改。當然,我并不否認改變一種積習的艱難,但有些明顯不合理的體制和政策的改變也未必就一定是難于上青天,比如以適當的經濟傾斜政策來保護高雅文學的舉措一紙法規就能解決,可這紙法規就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可見,不是不能為,是不為也!而長期不為的結果或許是人們所始料未及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把文化建設放在一定的位置上予以足夠的重視,那么,它的經濟絕不可能持續高速發展,即使在短期內發展不錯,其結果也必然是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