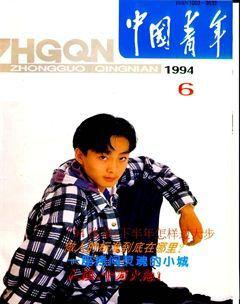朋黨·政黨·革命黨
張耒
朋黨的歷史從遠古一直沿續到清王朝。以康熙皇帝的威嚴和干練,也不能制止朋黨,鰲拜、明珠都是結黨擅權的高手。康熙晚年有儲位之爭,雍正皇帝成為利用朋黨作為政爭手段的行家里手。但即位之后,他卻對朋黨深惡痛絕,頒布《御制朋黨論》,對大小臣工反復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堅決反對北宋以來日漸流行的“君子有黨論”,聲稱歐陽修如果在世,一定治罪殺頭。由此,清代君主御下甚嚴,讀書人已經有陽衰的兆頭,所以朋黨之風不大興盛,但在戊戌維新時期,后黨與帝黨相互斗爭之激烈,也是近人耳熟能詳的故事。
不論朋黨政治發達或衰弱,朋黨只是封建政治的運作形式,并不能演化成為近代意義的政黨。政黨是西方代議政治的產物,始創于17世紀的英國。政黨的含義主要有兩點:一是依據一定的政治見解,組合為相對穩定的成形團體;二是堅持議會道路,運用選舉的方式獲取國家政權。所以政黨與代議制度是近代政治互為表里的兩種運作形式。沒有政黨就無所謂代議制度,沒有代議制度也就無所謂政黨。但在近代中國,政黨和代議制度卻是分別從西方模仿來的,兩者總是貌合神離,從來沒有很好地結合過。
19世紀前期,雖然已經有人注意到西方的議會和政黨,但中國人主要忙于仿制西式船炮。因為議會制度的形式接近古代中國的集眾思廣眾益一類的政治傳統,而政黨跡近朋黨,所以當時的先進分子往往著重介紹議會可以通上下之情,未見有人倡導組織政黨。到19世紀90年代后期的戊戌維新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一批在野的知識分子起而論政,除了運動官僚,還為了必要的聯合行動開始組織政治團體。為了避諱朋黨之嫌,當時的政治團體一律不稱黨,而是稱為會,往往是以學會之名,用做學問為幌子掩護政治目的。
1895年11月,康有為倡導成立了強學會,這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政治團體。梁啟超認為它既是學校又是政黨,由于中國當時還沒有代議制度,強學會也不可能獲取政權,所以只能說是政黨雛型。強學會得到光緒皇帝的贊許和帝黨官僚支持,翁同和曾經批準從戶部定期撥款贊助,這可以說是黨政不分的嚆矢,在西方似乎沒有先例。
當時各種名目的學會有七八十個,大多有政治色彩,但主要活動是辦學校、辦報刊、辦講座,以便傳播新知識,基本沒有掌握國家權力的野心,所以也只能說是政黨雛型。
那時多數中國人還迷信“乾綱獨斷”的帝王統治,因此希望獲取政權的政治團體只能進行非法的地下活動。1894年11月,孫中山在美國創立了興中會,準備造反。興中會是中國形成革命黨的先聲,但嚴格地說也不是西方類型的政黨。
19世紀末,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成立了御用代議機關性質的資政院,各省則成立了咨議局。資政院和咨議局屬于征詢意見的資治機關,不具備橡皮圖章的資格,不過有了一些代議機關的樣式,但活動于其中的政聞社、預備立憲公會、憲友會、辛亥俱樂部、帝國統一黨等,已經更有政黨意味。當時立憲派公開以組織政黨互相號召。這是近代中國政黨醞釀積蓄的一個時期,然而清王朝的當權派愚頑不化,不肯實現立憲政治,終于引發了辛亥革命,共和代議制度于是取代了君主專制制度。
中華民國建立以后,政治結構全盤西化,兩院制國會搬到中國,沿襲了幾千年的黨禁也不存在了。黨的含義由圖謀私利的朋黨一變而為競爭政權的政黨,組黨建黨也由殺頭罪立即變化為一種時髦。有志于政治救國和政治投機的人們紛起奔走,一時小黨林立,據說有300多個。大多數黨沒有政治綱領,面貌混淆,相互界線難以區別,以致跨黨分子大有人在。據說黎元洪這位人緣不錯的政治新星同時是9個黨的理事。
小黨林立可以說是后進國家模仿政黨政治的必經階段,下一步就是大聯合。到1912年第一屆國會選舉時期,有影響的政黨主要是國民黨、民主黨、共和黨等幾個大黨。當時孫中山、宋教仁、梁啟超等一批喝過洋墨水的政治家,都滿腔熱忱地號召在中國實行英美式的兩黨政治,不大了解西方文明的袁世凱也一度目迷五色,打算組織自己的黨或參加民主黨。可見政黨意識的影響確乎曾經深入人心。這是政黨政治在中國曇花一現的時期,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也是“過把癮就死”的時期。
當時的主要政黨在形式上和西方政黨非常相似,有政綱,有領袖,有支部,還有各種會議。國會選舉期間,眾黨派各顯神通,收買選票或脅迫選民,與西方議會選舉也大同小異。但這些都是形式。實際上,民初時期的政黨,在本質上與西方政黨有大不相同的中國特色:一是各政黨一概和社會各階層互相隔膜,老死不相往來;二是各黨派之間互相敵視,形同水火。
辛亥革命結束時,章太炎等人為組織政黨曾經登報募捐,可是沒有多少人響應。當時普通勞苦大眾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顧不上關心國家大事,資本家階級還處在政治啟蒙時期,堅持在商言商,不與聞政治。民初各政黨成員主要是政客文人,各政黨經費一律靠政府撥款,不單支持袁世凱政府的進步黨、公民黨由政府撥款維持,與袁世凱政府作對的國民黨,除在本黨控制的地盤以政費撥充黨費,同時也常常要向袁世凱政府索要經費。這樣的政黨既得不到民眾支持,也不受民眾制約,與西方政黨顯然不同。
各黨派之間的關系也與西方不同。當時孫中山主張政黨彼此相待應如兄弟;梁啟超認為各政黨分別代表國民的一部分,應當互相促進。但是這樣的主張似乎只是一種政治理想,不單普通黨員不大遵守,領袖人物也不能堅持始終。進步黨人稱國民黨是暴民,比腐朽官僚危害更大;國民黨人指進步黨人為專制政府的走狗幫兇,必欲去之而后快。不同黨派互相不承認對方有正當的政治動機,自然不肯妥協,往往求助于政府和軍隊的力量壓制反對黨,當時的立憲派和革命派都有互相仇殺的情況。陶成章是獨立意識較強的革命黨人,創立的光復會加入同盟會后,始終自成一派。辛亥革命時期,他招兵買馬自成勢力,因此招人忌恨,終于被同為革命同志的陳其美派人暗殺。在極端對立的黨派意識籠罩下,各黨派之間,同一黨派不同見解的人們之間,普遍缺乏理解和信任,缺乏妥協意識,意氣之爭和派別利益導致關系惡化,黨同伐異的朋黨錮疾隨處可見,政治暗殺成為多發事件。
1912年8月,黎元洪設計誘騙反對他的張振武、方維到北京,然后密電袁世凱以莫須有的罪名秘密處死。黎元洪向以寬厚被稱為“黎菩薩”,但在利益攸關時,也毫不猶豫地用陰謀手段殺害政敵。同年底貴州省軍務司長派人暗殺了到當地組建黨組織的國民黨特派員。孫中山對此大為憤怒,要求懲辦兇手,政府方面當然是應付了事。不久,袁世凱政府又暗殺了出任總理呼聲甚高的宋教仁,國民黨人極為憤慨。有人懷疑梁啟超與謀其事,梁氏因此著文反對暗殺,但他和進步黨人并沒有對袁世凱政府的卑劣作法采取特別的反對態度。當時多數政治家和黨派主要是反對政敵殺害本黨同志,而不是從維護民主秩序、堅持合法斗爭的一般原則來反對政治暗殺,所以政治暗殺頻繁發生,很少受到各黨派和民眾的普遍抵制。
對于民國初年政黨之間的混亂斗爭,似乎沒有行之有效的救治辦法。孫中山曾經以無可奈何的局外人口吻說:這個,一時是沒法子的;讓他們自己鬧鬧,鬧過幾年,自然明白。事實是,注重實際的政治力量后來都明白了,在中國不可能實行西方那種和平競爭的政黨政治。中國政治不能離開武力,而在近代中國,武力政治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是革命黨,而不是通常意義的政黨。
革命黨在近代中國最初是指同盟會等反清團體。這時的革命黨主要是以起義或造反為宗旨。所以推翻清王朝以后,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以此表示放棄武力,專事和平的政黨競爭。這種和平競爭一度卓有成效,國民黨經由選舉成為國會中第一大黨,也因此引起袁世凱的忌恨。于是,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解散國民黨。這標志著政黨政治在中國不得善終,而革命黨從此再興,取代政黨。如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以后,孫中山于1913年組織中華革命黨,已經有革命成功后由黨人掌握政權而不是與他黨平等競爭的念頭。十月革命以后,孫中山等國民黨人學習蘇俄經驗改組國民黨,逐漸形成了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實行一黨專政的明確思想。在此期間成立的共產黨,則主張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決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也成為最典型的革命黨。
盡管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社會基礎不同,政治理想不同,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但兩黨都走的是以武力奪取政權的路子,都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和系統的意識形態理論,因此都是與一般普通政黨大不相同的革命黨。
革命黨的形成和發展,改變了中國政治近代化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從此走上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