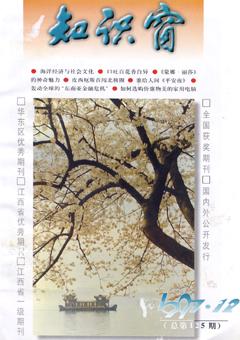口吐百花香自異
晏國琪
人人都有嘴,張嘴都會說話,但說出的話來卻如百花盛開,芳香各異。哲學家說:“世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語言學家斷言:“人問不會有兩個言語相同的人。”
言語的千姿百態是怎樣形成的?
分寸感。是受性格制約的。性格急躁的人說話火力威猛,如炮彈剛剛出膛;沉穩的人說話溫文爾雅,像奏小提琴抒情曲。所以,不同的人對同一事情,態度往往有天壤之別。如河邊有個青年用腳踹斷剛剛栽活的小樹,性格不同的目睹者言辭就大不一樣。老干部模樣的人見了感嘆:“現在的年輕人哪,是該好好教育教育了。”旁邊的年輕老師則說:“教育也不萬能,我看要罰,毀樹一棵,罰款1000元。”性格火爆的管理員接上話茬:“罰輕了,還要像新加坡那樣,加20鞭子,新加坡的文明就是打出來的。”正在植樹的綠化工人更激憤:“要我說啊,毀樹一棵,砍手一只。砍他幾個示眾,就不會有破壞的了。”
如果光從制止毀樹的效果看,綠化工人的做法肯定最有效,但,一項本是文明的事情,怎能搞得如此血淋淋的呢?其他人的意見有不同程度的參考價值。老干部顯然是位慈祥平和的長者,言辭間表現了極大的寬容。年輕教師或許對某些現狀不滿,故提出天文數字的罰款。管理員更急躁一些,他沒注意到,北歐的文明不亞于新加坡,卻主要是靠教化出來的。綠化工人最暴躁,簡直“憤”不擇言,他提出的砍手剁腳的辦法,完全不適合我們這個文明時代和國度。
言語的老練與率真是跟年齡有關的。孩子的話如春日之花,夏天的風,爽朗明快;老年人則慎于思考,往往“話到唇邊留三分”。有一個“老三屆”聚會,昔日同窗現在都五十開外了,教授、工程師、作家、藝術家各行各業都有。晚宴上,氣氛歡洽。有人出了道智力題叫大家搶答:“1+1在什么情況下不等于2?”歡騰的。席面頓時平靜下來,良久無人作答。出題人便點藝術家的名,藝術家連連拱手:“老兄免了,我從小就怕數學。”他悄悄指了指教授。教授微微一笑說:“我這腦瓜子反應越來越慢。——呶,我們的作家從小就有個綽號叫‘機靈鬼兒。”作家倒是笑得爽朗:“我啊,數學老師送我的,全還給他了。哈哈……”打排球似地推了好一陣子,最后大家不約而同將目光射向高三數學老師。這下是“專業對口”,無法推辭了。數學老師頗有幾分尷尬,正準備做玄妙文章,不知是誰帶來的孩子,大聲嚷起來:“這還不容易?1+1加錯了就不等于2。”“妙!妙哇!”大家一起叫起來,一份純真將歡樂氣氛重新點燃了。
言辭有文野之別、雅俗之分,這主要是由文化素養決定的。田野的勞動者,說話質樸,泥土味濃;文人愛咬文嚼字,文質彬彬。同是表達愛情,劉三姐的山歌唱道:“山中只見藤纏樹,世上哪有樹纏藤。”李商隱的《無題》詩卻是這樣寫:“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一個通俗活潑,一個典雅深沉。口語表達差別就更大了,知識分子喜拐彎抹角,或從莫扎特、施特勞斯的名曲談起,或從湯顯祖、曹雪芹的妙文人題,然后感嘆“高山流水,知音難遇”,以此試探對方的心曲。工農大眾要直率得多,要么說“交個朋友吧”,要么更直截了當:“我愛你。”然而阿Q直則直矣,就是太粗俗了,他喜歡吳媽,只會說:我,我……同你困覺。
“文革”中有首歌唱道:“什么樹兒開什么花,什么階級說什么話。”太絕對了一點兒,但也不是全無道理。有個故事頗能說明這個問題。一天大雪,秀才、商人、財主、農夫四人同在亭子中避雪。商人先開口:“大雪紛紛下地。”——顯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心態。秀才立刻接上:“都是皇家瑞氣。”——歌功頌德的媚態露出來了。財主也不甘落后:“如此下他三年。”——反正我有的是錢。最后是農夫說了:“放你娘的狗屁!”——下三年雪老百姓餓死,你也休想活!
與此相關,政治意識也會滲入言語里。國共和談時期,由中蘇友好協會出面邀請國共兩方面的新聞記者參加酒會。酒會有一項猜謎活動,有人出了一個謎面:“日本因此投降”。謎底打一我國古代人名。結果有人猜“屈原”,有人猜“蘇武”。猜“屈原”的是《中央日報》記者,他認為日本投降是屈服于美國的原子彈。猜“蘇武”的是延安《解放日報》記者,他認為日本投降是因為蘇軍擊潰了日軍主力關東軍。謎底不同原是政治見解相左。
實際上,言語的個性化并不只是受單一因素的影響,它往往是多種因素同時作用的結果。前面所舉年輕人毀樹的例子,評論者措辭分寸不同,性格是主要原因,其中也摻和著職業、年齡以及彼時彼地心理情緒等成分。曹雪芹是擅長語言描寫的巨匠,我們隨手采摘《紅樓夢》中一個片斷便可說明這個道理。
第四十回寫賈寶玉和眾姐妹乘棠木舫去蘅蕪院玩賞。水面上有許多敗荷衰葉,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么還不叫人來拔去?”語中透逸出貴族公子的驕氣,口氣是命令式的。寶釵聽了馬上說:“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一閑,天天逛,那里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功夫呢?”這可是典型的溫柔敦厚的閨閣語言,她是從體貼下人的角度說的,難怪上上下下沒有不說她好的。不過,寶釵的話還有弦外之音,一方面看似解釋,實則是安慰寶玉;另一方面是向寶玉表白,你不喜歡的我也不喜歡,順從和取悅之心都在其中。
這些,林黛玉是看得極明白的,心里早已酸酸的。此時她冷冷地說:“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著荷葉了。”林姑娘這話不但顯露了她的性格,而且飛揚著她的文采與聰明靈性。人都說林姑娘“小性兒”(用今天的話說是心胸狹窄、嫉妒)。不過,現代讀者大多能諒解,因為性愛本身是排他的。黛玉這話正是針對寶釵的,你說要拔,我偏主張留,以此掂掂自己在寶玉心中的份量。不出所料,寶玉立即表態:“果然好句,以后咱們別叫拔去了。”黛玉的聰明就聰明在她能將李商隱的詩句恰到好處地摘來。而且先抑一筆:“我最不喜歡”;再高高揚起:“只喜他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之句本有一種幽深的凄清美,經她一賣關子,更覺意味雋永。不由寶玉不贊同她的看法。而且“你們”二字別具匠心,“你”而不帶“們”,就會顯得太尖酸太刻薄太裸露。“你們”實際偏指寶釵,這樣,既發泄了怒氣,又掩藏了鋒芒,真乃是“綿里藏針”之法。林姑娘不愧“心較比干多一竅”。
(責任編輯/豐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