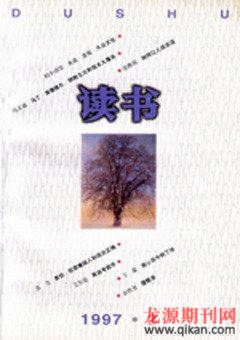關于“亞洲思考”
葉 坦
《讀書》一九九六年第五期、七期分載孫歌對溝口雄三、浜下武志諸氏主編的七卷本系列研究《從亞洲思考》(孫文譯作《在亞洲思考》)叢書的評介文章,我深感喜悅與振奮。不僅文中若干論點使我頗多共鳴,例如指出此叢書“提出問題的方式”,以及“在方法論、思維定勢方面的不一致”等,而且將日本亞洲研究的新動向介紹給我國讀者尤為必要。
拜讀之余,興致與共鳴似乎又深化為某種責任,即應當把一些不同意見講出來,無論對作者抑或讀者,都可以提供一點參考。
第一,孫文將《ァシァかと考ぇゐ》的叢書名譯為《在亞洲思考》恐不妥。無論從語言還是從內容尤其是從叢書的意旨來看,似當譯為《從亞洲思考》(或《從亞洲出發的思考》)。這個問題并非單純的詞匯翻譯,而是涉及到整個系列研究的宏旨。孫文以“亞洲意味著什么?”作為首篇之名,確是把握住了要害,而亞洲在這里意味著出發點、經由點等,即中文的“從”、“由”等意,這也是日文“かと”的本意。此叢書的英文名為“AsianPerspectives”,譯成中文就是“亞洲透視”或“亞洲視點”,這也說明不是“在亞洲思考”。孫文中有一處提到叢書主題為“從亞洲出發思考”,卻不知為什么如此譯書名,并用之于系列評論文章的標題。
第二,孫文引述岸本美緒(她的專業是社會經濟史,不是東亞思想史)的書評,將溝口與浜下分別歸位于“文化本質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范疇,似乎也不準確。我與岸本就孫文專門交換過意見。在岸本的理念中并非是將二者作為對立的概念來使用的,而且在她看來無論溝口或是浜下大抵都是作為“文化相對主義”潮流的推進者來認識的,再則她也并非“更傾向于浜下氏的‘文化相對主義而將溝口視角歸入‘文化本質主義并持有相當的保留態度。”這些在岸本的一貫思想和她對《從亞洲思考》所作書評中可以看出,而提出這些不僅涉及如何認識岸本的評論,更是牽動著孫文立論的一些基點。
第三,孫文講依稀感到“溝口雄三在方法論方面缺少后學們的敏感與潔癖”,認為他“真正關心的卻似乎并不是方法”,這與實際大概也有距離。我以為其學術的重要特征即是重視方法創新,他把自己的重要著作取名為《作為方法的中國》,他的許多著述中都滲透著這樣的學術特征和治學精神。例如其獲得博士學位的論著《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即是建立在對日本權威學者島田虔次《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的發展之上,在研究方法、視角理念諸方面,都體現出方法創新的學術特征。作為思想史的研究者,溝口在日本學者中頗具思想、方法、新見之特色,并在教學體制等方面力倡改革,希圖走出一條中國學的研究新路,這也是他倍受學者關注的緣由。孫歌也曾指出過,“像溝口教授這樣敏銳地意識到中國學應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并為此而提出方法論問題的學者在日本為數并不多”。主編這套叢書和“不要求一致”的“非潔癖”,不正體現了溝口在方法論上的敏感與創新嗎?
最后,此叢書所輯錄的論文是五十八篇,而非一百四十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