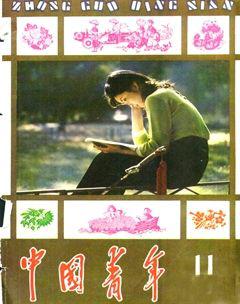想起玉子
金戈
玉子是個矛盾百出的女孩,大學時住我上鋪。
大一時的玉子是我們的“每夜一修”。每次老太太的熄燈“鑼號”一過,我們就央著玉子來一段,于是夜色中玉子的聲音從梁上悠悠飄來。唐宗宋祖兩晉漢,正聞野史大客串。萊克星頓的槍聲也許響在秦始皇夢里,但玉子惟妙惟肖的描述只會讓你對自己的記憶力產生懷疑。無星無月的晚上玉子就講聊齋,直講得屋里鬼影憧憧,我們脊梁骨冷氣直冒;去廁所成群結伴,豎著耳朵提高腳跟還不敢左顧右盼。玉子卻一個人盤坐在上鋪擁著被子樂:“我說勇敢的布爾什維克戰士們,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唯有物質永恒沒有靈魂不滅!”
大二時玉子有了打工的主意,飯桌上一通演說,什么
鍛煉能力,見識社會,也要揭竿而起。卓兒與維怡被她煽忽得動了心,預備一起去應聘一家飯店的服務員。刷完盆描完眉,維怡就斜坐在鋪上望著玉子發呆:“玉子我不想去了,倘若人多,我說不出話來怎么辦?”得,還沒上戰場就先退下一個來。玉子急忙拉著卓兒出門,這情緒就像感冒傳染得快著呢!還沒出北院門呢,卓兒看一眼玉子:“如果我媽知道了該說我不務正業了吧?”沒出中門,卓兒又拉拉玉子:“玉子,到那可別說我也應聘呀。”結果當然是中飯時只少了一個玉子,她去當鐘點工了。中午端著盤子滿場飛,紅塔山15元,叉燒肉10元,還知道了“螞蟻上樹”這個菜。
從此以后,玉子一面忙學習一面忙掙錢,每晚要到熄燈才從圖書館回來。沒了講故事的溫馨,我們都覺得玉子遠了淡了。偶爾有一次“回光返照”,讓姐妹們紀念至今。那天黃昏,圖書館停電,大家都窩在屋里,除了陽臺上等男友的劉湘。我們圍在桌邊談紅燈籠酒店的“三陪”服務,玉子又擼袖子又皺眉:怎么沒讓我碰上這種飯店,也算長長見識,不然馬路上遇著了,披著一樣的人皮戴著一樣的面具,你知道哪個是人哪個是鬼?大伙一時沒了言語。忽然玉子指著陽臺大笑起來:“聽著聽著,我送劉兒一首詩:望夫湖畔望夫丘,望夫丘上望夫樓;望夫樓上望夫女,望夫之夜望夫愁。”念完小鼻子一揚,自以為一步不挪,比曹植七步成詩更勝一籌。
大四時玉子也談朋友了。那個小男生,個兒又低,眼又小,除了專業課時拍片子得了個二等導演(我們玉子還是第一呢)外,簡直看不出有什么好兒來。盡管大張同志又是西瓜又是瓜子地“孝敬”,姐妹們也沒那么容易被堵上嘴。可總歸吃人嘴短,拿人手軟,玉子就這樣被我們拱手相讓了。
大張是山里生山里長的苦孩子出身,據說要遠到了壩上大草原。雖說有一俯身便能拾個鳥雀蛋的誘惑,可誰愿意真做個新時代的“上山下鄉”?所以后半學期的玉子與大張不再做圖書館里的鴛鴦蝴蝶了,他們忙著找單位送禮以期共同留下。大張去拜見主任大人,玉子就坐在樓底下等,還不忘諄諄教導:“你就當過馬路時遇到一條狗,擋了你的路,就喂它一塊肉。”每當有人收了玉子的禮,她就有一種勝利感:雖然看似當官的得了好處,你吃了虧,可實際上你邁過這一步卻有大大的好處在后面等著你。我問她哪里來的這套歪理論?“厚黑學!”她說,“等我當了官再遏制行賄受賄吧……”
大張最終還是回了他的大草 原古戰場。玉子在手絹上寫了一首詩送別:當汽笛鳴響/我低下頭去/我愛/如歌的日子/接踵眼前來//當風煙散盡/我抬起眉來/我愛/草尖上的露珠/隨了冬陽去。玉子分到一家電視臺忙著她的紅綠藍采錄編,她說:“我得先踢響頭三腳。”
我曾在《中國青年》上看到玉子的“20世紀我有一個夢”——“戶口不再限制,沒有兩地分居”。玉子還是玉子,唯物又唯心,虛幻又現實。
作者通聯:050000石家莊市第一職業中專學校電教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