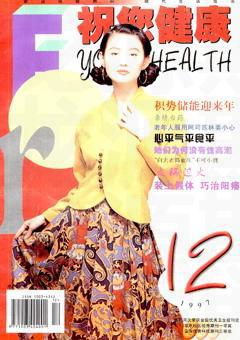并非心理醫(yī)生的敘述——
傅巖山
朋友,你所訴說的而立之年的困惑,也正是我近來所思考的問題之一。根據(jù)我對你數(shù)年來的觀察,并根據(jù)來自同道們的一些意見,我想說你是一個充滿敬業(yè)精神的人,一個朝氣蓬勃干事業(yè)的人。基于這樣的判斷,你的一些尷尬,你的一些困惑,也就有了論說的必要。作為而立之年的你,你的既有業(yè)績是不錯的,可以說已經(jīng)超過了同齡人所能為。如果要說而立尷尬與困惑的起因的話,這也是起因之一。公平地說,人的弱點在這里起了很大的阻力。沒有一個人是愿意居于下游的,沒有一個人是愿意空耗一生的,但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起點,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生存環(huán)境,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機遇,所以便有了形形色色的人生狀態(tài),便有了各種不同的社會地位。你的單位,我的部門,或多或少的人中,都可以找到各式人的代表,于是這個世界便熱鬧起來,酸甜苦辣也就盡在其中了。要想事業(yè)有成,只有埋頭苦干,默默奉獻一條路。投機取巧的事決不是年輕人的依恃。
有了這樣一個基本的態(tài)度。我想你還要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你所從事的是富有開拓性的事業(yè),是合于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要求的事業(yè),你能比較稱心地干這么幾年,已經(jīng)是很不容易的事。這種狀況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你的眼光,你的努力及朋友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你所供職的單位或多或少的贊成。在這種情形下,你只要對你所從事的事業(yè)保持必要的信心,而不要過多地將目光盯在那些不如意的事上。干,就是了。沒有時間的積累,再偉大的事業(yè)也不會有成。
其次,任何一個單位,任何一個部門,其合理的事情與不合理的事情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妥協(xié)的,發(fā)展,才是真理。所以,不合理的事兒,其地盤一天天在縮小,但換個方式它又會冒出來,斗爭,又得從頭開始。如果我們把眼睛只盯在這些不合理的事情上,遲早會被這些事情纏繞得透不過氣來,到了我們撤手人寰的那一天,我們便會后悔——假如,我們自身更堅強些的話,某某時期我們還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哲學(xué)家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哲學(xué),可資憑證。他同樣經(jīng)歷過西南聯(lián)大時期的困難。教授的日子其時肯定不如一個小公務(wù)員,但先生認(rèn)為,人生有比衣食生活更重要的事情,本著這一想法,并得到夫人任梓坤的襄助,他安心地在別人下海之際穩(wěn)坐書室,潛心著述。其他教授夫人做生意。任梓坤不能說對自己的生活沒有一點幾埋怨,教授本人也不可能無動于衷,但他們堅持下來了,生活便在新的時期對他們投以微笑與鮮花。岳麓書社的唐浩明先生,他投身出版這十來年,正是出版業(yè)風(fēng)起云涌、熱潮翻滾的時候。且不說那一波又一波的書市熱浪對從事古籍整理的他的沖擊,單是那形形色色的協(xié)作出版之風(fēng),不知不覺的發(fā)財之道,便足以撼動古籍堆里的唐先生。事實是,他潛心故紙堆,學(xué)習(xí)、鉆研、寫作,勞作不輟,用他的話便是。日子過得很單調(diào),沒有別人那樣的五彩紛呈。忽一日,先生捧出了數(shù)十卷<曾國藩文集),又一日。他拿出了數(shù)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他早年的夢都在這些白紙黑字中實現(xiàn)了——他何憾之有?
引發(fā)我們今天心緒浮躁的根由無外乎一些外來的肯定方式,其最終的表征,都是物的占有。其實多年前的人們同樣會遇到此類問題。在這一點上,如果你還要做一些事的話,我勸你還是想得寬一點,多一點兒精神自足。如果你連精神上的自足都做不到的話,我就要懷疑你能否干好一項有價值的事業(yè)?這有價值三字當(dāng)然還是看重其精神文化價值,而非折合成銀兩的價值。貝多芬如果去學(xué)習(xí)烤面包的話,他不會有那樣的潦倒。所有想不開的事情要著力去想開他,真正從事精神創(chuàng)造的人,似乎并不太在乎對其身外之物的占有。我曾笑對人講,居住30平米不人道,60平米就正好,百平米以上呢,那就是奢侈。胡適老先生曾對人說,少時讀書如饑似渴,但是沒有書可讀;中年無閑暇無精神,人家卻送來許多書給你讀;老來怎樣呢?有閑暇有書籍卻沒有了好眼神。這人生就是在重重矛盾中曲折前行,每一個階段你只能重點解決一個問題,否則,忙亂一通,什么結(jié)局也不會有。尤其對于從事精神事業(yè)的人來講,你于一般的生活之外,想登上人生的另一重境界,你自然需暫時放棄一些人生的世俗。我有一位較熟悉的朋友,號稱才子,他說他都不想放棄,于是他多多少少都得到了——然而我在他的文章中看到了較多的虛浮與矯情。以他的水準(zhǔn),以他的勤奮,以他的才干,他本來是可以有更大的收獲的。事實是,貪多求全的虛榮。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他的事業(yè).因為他完全有能力達到更高的境地而非目下的處境。
拉雜如許,難以言說你三十而立的種種困惑。好在還有那么多的歲月,還有那么多的機會,你只要靜下心來,是可以干出一番事業(yè)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