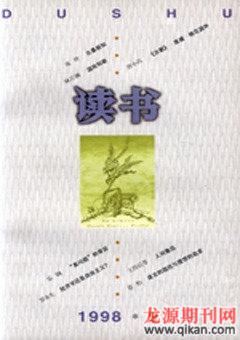經濟學還是自由主義?
羅永生
英國政治學家貝拉米(RichardBellamy)在他的著作《自由主義與現代社會》中,追索了自由主義在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等幾個歐洲國家的發展的變形的歷程。他的基本命題是:十七世紀從英國興起的自由主義,是一種“道德性自由主義”;但往后的自由主義,特別是經過意大利和德國在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發生的變化,其道德訴求已日漸萎縮,讓位于一種沒有道德承諾的“經濟性自由主義”。
所謂“道德性自由主義”,源起于亞當·斯密、斯賓賽、密爾等英國啟蒙哲學家,以及歐陸一些受康德和黑格爾所啟發的理論。這套早期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有它的哲學前提和社會命題。在哲學層面上,他們不約而同地高揚個體自由的重要性。雖然對自由該落實到哪一種類型的社會活動,哪一種自由更具優先地位的問題,他們未完全達成一致意見,但都相信一套完整的自由理論,可以同時兼顧社會成員不斷擴大追求的自由,以及自由個體之間能夠和諧共存的社會秩序。可見,道德自由主義者不是要放棄道德評價,而是力求避免對不同的社會活動作出實質的道德評價。這種自由主義,其實是為自由本身,給定了一種比其他社會價值更為優越的道德價值。所以,宣稱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這行為本身,并非遠離道德的承諾,而是明確宣示對“自由”這一種道德價值的委身。而且,這種自由主義不單要在價值和理念的層次上高度重視道德,更要為自由這價值奠定實現的具體基礎。而這項工作就要依賴提出一項與自由主義哲學前提相對應的社會命題。
道德性自由主義的社會命題認為,自由的發展不僅不會帶來道德上的空無、相對,挑動社會成員之間有害社會團結的價值沖突,反而會帶來更和諧的社會生活。特別是洛克和(很大程度上的)亞當·斯密,都試圖為這種關于新社會的發展方向和未來的和諧秩序,提供一個神學的基礎。而亞當·斯密的突出貢獻,就在于試圖說明一種理想化的市場關系,如何能為新型的社會道德奠定基礎。他的整個理論體系,是以一套關于人性發展和世俗社會演化的說法,來承接洛克的神學/道德前設。他認為,自立、有責任感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都是通過在市場社會中,人們相互接觸、交往,才能真正培養出來的。市場關系的道德意義,在于它所促成的各種體現在個人、社會和道德不同層面上的改進。于是,自由、理性、道德和進步,都在這套關乎道德的自然哲學命題和關于社會的演化命題互相結合之下被等同起來。對這些啟蒙者來說,國家是不道德的追逐權力之地,而市場社會卻是道德反抗的前線。所以市場社會存在的合法性,恰好是其道德上的承諾。
可見,早期自由主義者的問題意識,完全是一種道德關懷。這套道德自由主義立論的關鍵之處,是它假設了一個完全的競爭性市場,在其中,所有經濟活動的參與者,都是各自獨立、地位相若的。不過,十九世紀中后期的發展,雖然證明了這種假設與現實有很大出入。市場并非在各獨立、平等而自由的布爾喬亞個體之間設立,而是在互不平等的利益集團之間形成的。然而,重要的問題不僅在于,市場關系背后存在多大程度上的(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沖突,更在于:縱使歷史上存在過這種理想中的人格、道德和社會狀態,市場機制的自身調節,是否真能把它們維持下去?反過來說,當市場中各參與者的關系,原來就是處身于資源、資訊等各方面的不平等狀態的話,市場機制又能否把這些道德和社會條件營造出來?十九世紀后期的自由主義者所普遍擔心的就是,在攫取性的個人主義日益泛濫的歷史事實面前,自由主義是否要放棄其原初的道德承諾?而放棄了道德承諾的自由主義思想,又會是怎樣的一套思想?不少自由主義者開始不再單單信賴人類道德情操的自然演化,反而漸漸寄希望于由國家和知識分子去充當公共精神和社會道德的守護者。也就是說,自由主義的道德承諾,已無法單純依靠構想中的市場社會/公民社會去使其兌現,相反地,國家體制的道德訓導角色,就日漸突顯出來。國家和市場體制的道德地位,又再一次倒轉過來。
如果說英國的自由主義者(例如密爾),還是深信個體的自我發展能力的話,法國的道德自由主義者(如杜爾凱姆),就愈益感到需要強調這套道德理想的社會基礎。而且,在意大利和德國,自由道德情操和現實的落差就更大。意、德的后進工業化,使這兩個國家的工業經濟發展,為強大的由土地貴族轉化過來的集團利益和國家主義者所主導,逼使得自由主義在思想和政治立場上產生了巨大而實質的變化,從其道德性的形態向經濟性的形態過渡。而這種過渡所引起的緊張和沖突,在發明著名的所謂帕雷托最優定理的經濟學家和社會思想家帕雷托身上,表現得極為明顯。
帕雷托早年深信英國自由主義者,例如密爾所持的道德信念,也就是說,民主和自由的根本目的不在其他,而是人格的改進和建立自由人的公民責任。他反對社會主義者所支持的社會立法,并非因為他不認同其人道主義目的,而是為了反對一切不是靠自力贏取的特權,無論這些特權是對富人還是窮人有利。帕雷托認為,這種依賴國家力量去維持的利益,是意大利政治腐敗的原因。針對這些腐敗,自由主義者應具備一種“自由的情操”去站穩立場,反對一切違背自由、公義的事。他認為自由主義者一定要遠離政客的蠱惑,抱持正直不阿、誠摯勇敢的道德人格。可惜,這些都是當時意大利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所缺乏的,也是他對意大利新冒起的布爾喬亞階層最感失望和沮喪的原因。他悲觀地感受到,如果連自由主義者都缺乏了這些素質,公義的大旗只會被社會主義者奪去。
陷于這兩面作戰的處境,帕雷托一方面想推動自由主義的道德大業,反抗權威政治,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的自由主義,建立在一種有別于社會主義的藍圖之上。他要證明市場體制存在的最終理據,是在于科學論證上勝過社會主義者。在調和道德考慮和科學體系的系統性這雙重要求下,他求助于功利主義的倫理學來整理他的經濟學,試圖說明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與所有人都能得到最大快樂的狀況,是緊密地互相關聯的。所謂帕雷托最優狀態,就是指一種一個人的進一步增益已到了不能不以另外一個人的損失為代價的狀態,也就是說一種剛好不需要以剝奪任何人來使每個人都有最大利益的狀態。這套所謂帕雷托最優狀態的定理,成為日后新古典經濟學強行在預測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之間作出學科區分的轉折點。它帶來的后果就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哲學教授森(AmartyaSen)所云的在經濟學中日益強烈的反道德主義。也就是說,市場的存在不再建基于社會在道德、人格方面的進步,而是很簡單的一種功利和效率上的原因。這條以功利和效率為標準所引伸出來的對市場制度的支持,并沒有顧及資源和財富分配的情況,而且是一種相當簡化的,以功利單位來計量的推演。
正如森等經濟學家所指出,人際之間效用的可比性是簡單的功利主義倫理學的致命弱點,可是當今的經濟學主流,為了反道德主義,極少對此有足夠的研究和重視。在簡單的帕雷托模型中,也沒有妥善地處理外部性的問題,例如在涉及公共決策時極為重要的關乎原初擁有權和資源配置方面的訊息,就并非一個簡單的市場機制可以解決。不過,更嚴重的缺陷還在于以個體追求自利為最后動機的帕雷托定理,并沒有說明在集體獲致最優選擇前,怎樣形成需要首先存在的那些可以讓個人選擇能朝最優狀態進行的自由權利,以及關于這些權利的規則,除非這些關于尊重這些權利的價值,已經先于尋求最優狀態的體系運作而存在。但如果這樣的話,這套定理想要努力排除的道德問題,便又重新出現了。
當然,對于在早年充滿自由主義道德熱情的帕雷托來說,這些尊重權利的社會價值,理論上是隨社會演化而自然發展出來的,但大失其所望的政治社會現實,最后促使他本人放棄了那套以追求自利來達成社會最大快樂的,所謂“看不見的手”的機制。十九世紀末年的政治轉變,使他已不像過去那樣將這個理想化的市場機制,看成真能憑藉自身就能保證社會達到最優狀態,而是把它視為一個純粹存在紙上的經濟理想。世紀之交后,他的關注點反而轉向了指引人們行為的非理性動機,而這也令他將研究轉向社會學。他將早年建立經濟學系統的科學主義企圖,和關于人的功利主義動機論,推演成一種非常冷酷和犬儒的政治和心理文化分析。他提出有名的“精英循環論”,把各種以道德熱情推動的改革和革命運動,都視為只不過是由新的精英去取代舊的精英,新的特權取代舊的特權。他又提出“余緒”(residues)的概念,去發掘人在邏輯思維底下的各種心理動機。他的政治社會學,描述了一個由強力支持的獅子型人物和狡猾的狐貍型人物相互交替的世界。貫通他前期的經濟學和后期的政治社會學的,是人的自利主義行為的分析,所不同的,是他的社會學已失去了關乎道德、幸福和最大快樂的執著和承諾。
與此同時,帕雷托的政治取向也日益從自由主義向右傾,犬儒的歷史觀使他日漸成為一個以權術為先的馬基雅維尼派。自由主義者原來支持的各種措施,變成僅是一些管治上可用的手腕,而他也漸漸變成為一名新興的法西斯主義同情者。他雖未全面肯定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但他贊許墨索里尼的狐貍智慧,肯定他為意大利的第一流政治家。他認為法西斯的暴力傾向,只是一個過去長期的“紅色暴政”的恰當反動。而墨索里尼,也贊許地說在帕雷托的課堂上受益不菲。
如不少道德自由主義者一樣,帕雷托也堅持創業精神,反對國家干預。但由于在他的理念當中,衡量一個政權的標準,已非自由、道德,而是效率。于是,當他們發覺人們在掌握自由的時候,并不一定“懂得”以對社會有用的方式來運用,那么國家的指導、帶領和介入,取代原先促成道德上不斷完善進步的市民社會,就變得理所當然。因為個人的追求自利的動機,已不足以保證達到最優狀態,余下的就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和“道德”責任,去保證一個自由經濟體制的運作。這樣的話,去除了道德面向的自由主義,在使自由變成一種經濟體制教條的同時,也使自己顯得軟弱無力。面對赤裸裸的權術追求,也只有一種犬儒的回應。原本反專制、反國家的自由主義,變成另一種的國家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也只余下一步之遙。帕雷托一生的思想轉變,足為一個深刻的見證。
纏結在帕雷托身上的,并不是他個人在道德立場上的退縮和軟弱,而是一種被學科規范建立過程所淹沒了的思維上和道德上的矛盾和陷阱。當帕雷托以一個完整而論證嚴明的經濟學模型,去為自由主義的道德價值奠定一個“科學”基礎的時候,他可能沒有想到的是,近一個世紀之后,人們談論的竟是要道德還是要經濟學。但正如森在他的《道德與經濟學》一書中所講,帕雷托以來主導經濟學界的那套簡化的功利主義邏輯,已經同時危及以描述或預測為務的經濟學和以福利評價為務的經濟學。森所正確談到的,是經濟學內部的學科分隔危機。但他已很明白地指出的,而且更重要的還是,今天經濟學已日漸失去了為自由、選擇和權利此等自由主義價值,提供有力的說明。看來,對所有曾經為自由價值所鼓舞和感召的人來說,問題不是要道德還是要經濟學,而是要經濟學還是要自由主義?是哪一種的自由主義?
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維園涼亭